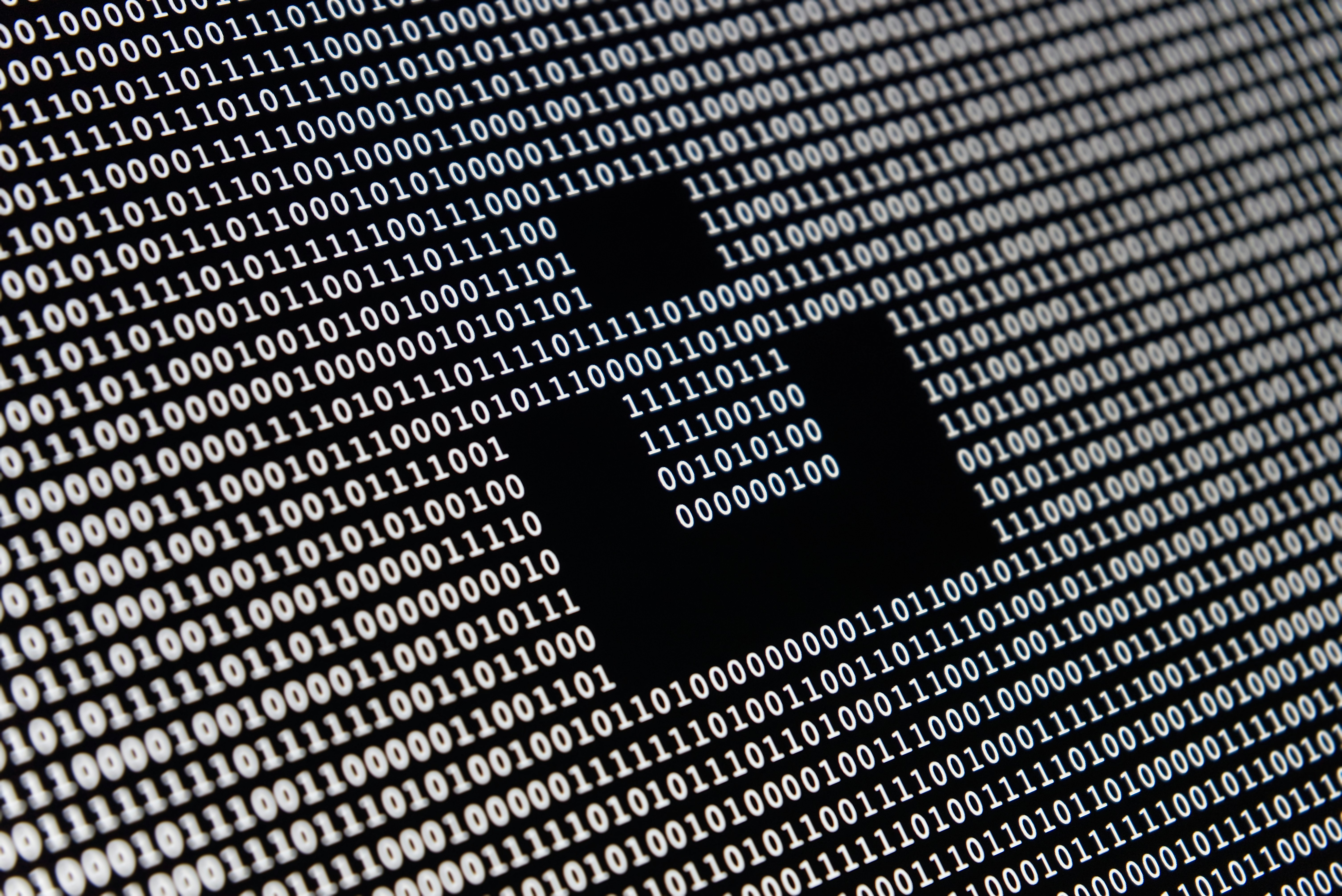粽,和所述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我記得我在嘉義第一次吃到南部粽的感受。
嘉義總是這樣的,在炎夏也不悶熱,在山腳的小小鄉鎮終日享有不帶水氣的日曬,炎熱而從不蒸溽。每逢夏季,鐵軌載送著一波波的遊子,朝向山腰上的自由空氣而去。再載送著興奮與忐忑而回。
在嘉義的日照彷彿比較長。我總會更早醒來,騎著腳踏車在村莊裡晃晃。那裡是陳厝寮,路邊大樹下總有賣自家鳳梨的攤販,舜泰柑仔店以及大樹下便當。在我還不認識系上同學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了這些村民。我往往停下單車,跟村民買顆削好的鳳梨,回宿舍半躺著吃。鳳梨咬舌是我很難避免的痛。我總會在選購鳳梨前做垂死掙扎,最後屈服於牛奶鳳梨的香甜。比起金鑽,果肉顯得更加白皙細軟的牛奶鳳梨生津止渴、奶香清甜。一口接一口地吃完一顆後便唇舌刺痛,仿佛石礫磨過,白水亦變得苦味難當。我曾經感嘆過,鳳梨是我遇見最霸道的水果,往往咬它數口,它便要占領人的味覺好幾日。
我跟村民之間是買賣,銀貨兩訖。但是我們之間總會多聊幾句,往往要聽他們親切地招呼、對自產自銷鳳梨的介紹;以及後來我每年回去看煙火時的熱絡:
「欸,你回來啦?」
「對啊!校慶一年一次,剛好來看老師朋友啊!」
我在嘉義時也想家,在風裡長大的孩子,到哪都希望風時時刻刻吹拂過面孔。年復一年,在霧白的晨光中甦醒,而在寧靜湖中倒映著銀白星光的夜中入睡。最後一年我沒課,鎮日晃盪,認識了洪雅書房跟其他。離校的焦慮一直在我身上燎燒。我那時每天早起,想知道我在嘉義能不能有事做、是不是要一個人留下來。成天在城鎮中遊蕩,日日騎好幾公里的路程去找尋我的方向。我的同學,幾乎都選擇離開嘉義,我問過他們,他們說:「在這裡找不到發展。」這也成為我最後離開嘉義時的心病,我也覺得,在嘉義我可能真的找不到發展。
我一個人晃來晃去,用另一種心情去跟村民聊天,第一次在豐收村五穀王廟那裡遇到了早餐時段的攤販。比起我相對熟稔的陳厝寮,豐收村是另一番風景。陳厝寮的紅土上佈滿著被黑紗網覆蓋的鳳梨,而豐收村處處可見鮮綠的稻田。我不認識他們,豐收村的人們對我是陌生的。我當時隱隱約約注意到,村民對於「大學生」的複雜感受。我也不確定我是否延續異鄉人的身份留在嘉義。於是開始有一份尷尬出現在我跟嘉義之間。
那個早晨,我面對五穀王廟第一次坐下來,在簡單的桌子上點了一份肉粽。老闆打開蒸籠,將肉粽剝葉後盛在碗中遞給我,還說了:「你噯搵這。」手指其中一瓶我看不出來是什麼的醬。身為北部人,承載著過往的吃食記憶,我從來不聽南部人在飲食上的建議。我固執的在眼前的選項中找尋最可能合乎意料的口味。
我自己拿了他有的醬料,每種都擠一點點出來在盤子上,然後將肉粽分為一小塊一小塊,每口一種醬料蘸著吃。肉粽是糊的,花生是軟的。軟糯的米飯黏著筷子跟碗盤,就是不黏我的唇舌。我第一次看到糊糊爛爛的肉粽,我心裡想著,這老闆手藝不行啊!肉粽蒸太久了吧!不過蒸太久會變這樣嗎?我家的不會啊!我還是吃了,畢竟是肉粽,畢竟是早餐裡單點項目最貴的那個。
第一口,沒味道太軟爛,有粽葉的清香,我還沒沾任何醬料。
第二口,太鹹,醬油跟肉粽不合。
第三口,太辣,只加辣椒不配烏醋的醬沒有靈魂。
第四口,好吧,是這個醬的味道,但是不合啊。不合,不符合我的期待,也沒覺得特別美味。
我想了想,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吃這邊的肉粽必須得像小籠包一樣。每一口都配著幾根薑絲,蘸上他們很愛的那種的紅紅的醬,這樣既有清爽的口感,也有了美味的甜辣。我吃完那顆肉粽,心裡想著,以後來這邊吃還是點豆漿跟飯糰就可以了——這邊的飯糰也和北部的不一樣。
老闆一邊做生意一邊看著我的舉動,他最後在我付帳時說:「啊你甘嘎都幾種卡合?」
我笑了笑,知道自己舉動怪異,不好意思說什麼:「沒啦,我頭一次吃,想說都試試看。」
「頭一次吃肉粽喔?!」老闆很驚訝。
「不是啦,是頭一次吃你家的,想說試試看。」
「啊捏喔。」老闆像是有話想講,但是忍著不講出口。
我騎上單車,直接離去。想說,還是找找看不會蒸太久的肉粽好了。後來的某一年,南北粽之爭正式開打,即使總在異鄉飄零,我也從不猶豫,年年選粒粒分明的北部粽。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4會員
33內容數
作為一位對人文學深感興趣的學生,我深知討論對概念釐清的重要。身為一個推動審議式民主的成員,也作為一位對教育深感興趣的助教。我嘗試將各種議題用淺顯的語言寫成一篇篇故事,我很希望大家不只是看文章,也透過討論來理解公民社會的運行。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