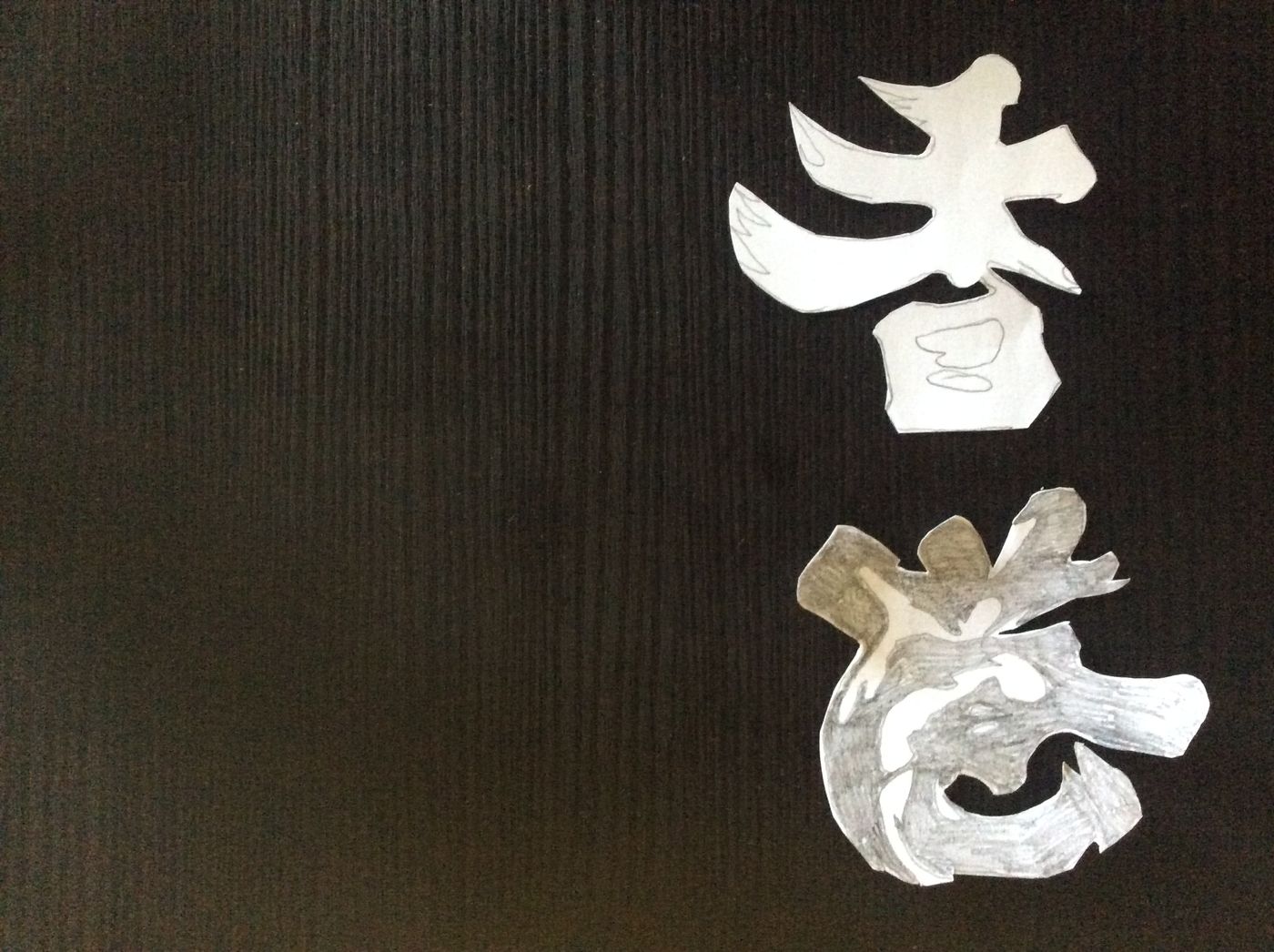現代台灣讀者對於魯迅(1881~1936)作品的印象或許會停留在高中課本選入的「孔乙己」,對於那個出口成章的破落書生的所做所為覺得荒謬可笑,不過如果知道魯迅本人在還沒寫白話小說前也做過一陣子古碑文的研究,或許會對於作者的自嘲再加上一絲同情。朱宥勳先生的導讀「《魯迅小說全集》朱宥勳導讀:如果世界真是一個鐵屋,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是很棒的導讀,介紹了魯迅與台灣小說的關聯,建議一讀。
今天要介紹的是魯迅半自傳散文集「朝華夕拾」,裏面談到他的童年、求學、一直到學校工作為止的所見所聞。對於魯迅來說,舊中國是他大部分作品的靈感來源,他用「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來完成這些小說、雜文,而這些不假辭色的批判,或許都來自於他對於這個古老大國的孺慕之情。我們先來看序文中的自述: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序)接著,他用各式各樣的中國古老事物來貫穿全書,八戒招贅、老鼠娶親、山海經、二十四孝圖、迎神賽會、城隍、東嶽大帝、鬼卒、鬼王、活無常、西遊記、封神榜、關帝廟…都是他童年難以磨滅的意象。直到他生命中出現了重要的轉折、開始出外求學之後,就開始有天演論、地學(今地質學)、金石學(今礦物學)、華盛頓、蘇格拉底、柏拉圖、斯多噶、東京、上野的櫻花、日本老師藤野先生、骨學、血管學、神經學、解剖學、黴菌學、生物學、革命烈士徐錫麟與秋瑾…對於從舊時代過渡到新時代的少年魯迅來說,這本「朝華夕拾」所描述的種種,可說是他生命的啟蒙。
講到「生命中出現的重要轉折」,就是這篇「父親的病」,描述魯迅父親晚年生重病,請名中醫看病所經歷的光怪陸離的過程。其中一位名中醫開的藥引令人嘆為觀止: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
隨著病越來越重,最後醫生開始建議要看前世的因果:
…「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是前世的事…」
最後藥石罔效之後,在長輩的命令下,開始五子哭墓式的呼天搶地: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父親!父親」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什麼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切地喘著氣,好一會,這纔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我覺得這卻是我對于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父親的病讓魯迅對中醫的信心崩盤,後來去日本留學後,更讓他對中國人的無知與麻木感到悲哀:(接下來引自本書的「藤野先生」)
…但我接著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補獲,要鎗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藤野先生)
對於這些看到同胞被鎗斃都還歡呼的悲哀中國人,魯迅最後決定棄醫從文,因為這些人最需要醫治的不是身體,而是病態的思想。魯迅窮極一生,都在跟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落伍思想奮戰,而這些反傳統、尋求現代化的主張,也深深影響了一整代的中國作家以及台灣作家。
我們可以把這本「朝華夕拾」視為魯迅寫給舊中國的訣別書,就算鄉愁再濃,但是不揮別舊中國,就沒有新中國的誔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用他無所畏的健筆,揮向舊中國的魑魅魍魎,而這場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戰爭,似乎還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