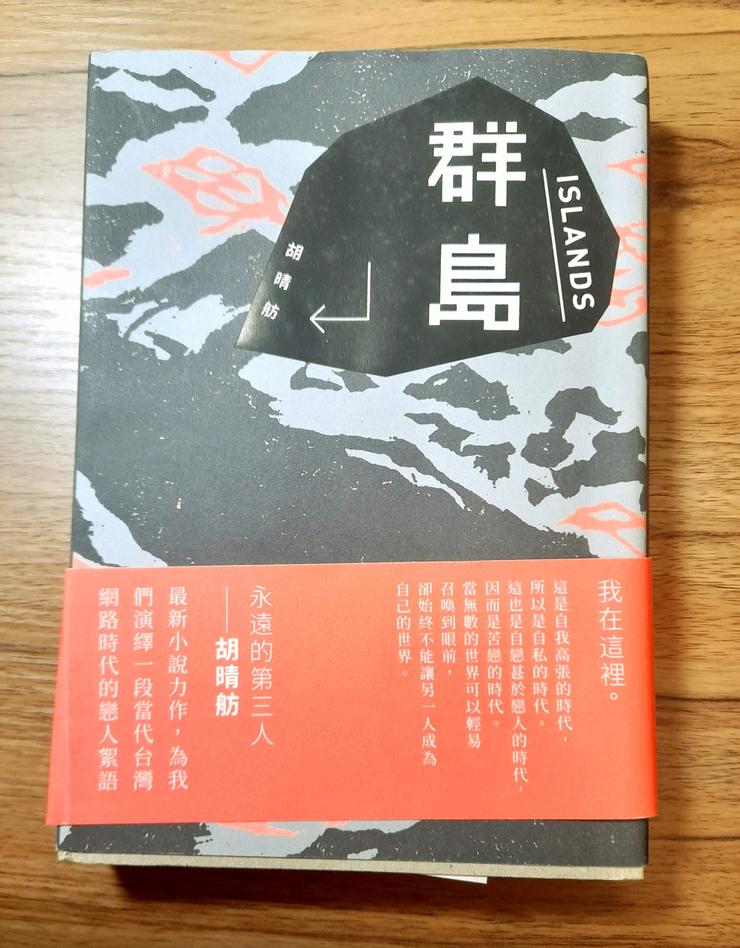刊登於《幼獅文藝》2021年7月號
我選擇相信,死去的肉身和靈魂,埋在泥土深處,為城市提供著繼續運行的養分。這些年來,城市一直經歷著暴猛而頻繁的大死和小死。(p.433)
讀韓麗珠新作《半蝕》,心中浮現的是一片密林,痛苦與平靜並生。今日香港,H城,天空中散布著各種死亡的碎片,飄蕩如遊魂,最終落地,成林,包覆著整座城市,也有些會以空缺的形式繼續存在著。
小說家韓麗珠過去多以隔離與異化為母題,採取陌生化技法「虛構」H城,表現人們的壓抑,為了生存保持疏離是常態。而近年來自由的崩解,迫使港人更直接地思考城市命運,韓麗珠書寫遂轉向「當下」,那是從她眼中看出去的一塊香港碎片。2020年日記體散文《黑日》近距離凝視抗爭現場,寫黑洞般的恐懼,卻信光亮仍在。2021年新作《半蝕》延續這個體例,紀錄此時,此身,此城。最初一篇是〈城影〉,威權迫近,照見城市的暗面。〈穴居時期〉寫瘟疫時期的家居日子,以內在能量孕育森林般的平靜。〈心裡有蛇〉、〈吃人的家〉和〈帶罪者〉寫人們的恨、傷痛與罪咎,從根本處受到背棄。一切收束於〈中陰生活〉,「中陰」是人死後到前往下一期生命前的中間存在狀態,貼近此刻香港,欲過渡到自由彼世,卻尚未完成的一種狀態。有什麼死去了,又有什麼將要新生,這是書名《半蝕》由來。
無所不在的執法者,是權威的具象。香港特區政府頒布禁蒙面法,警方卻被允許以黑布蒙臉,揮舞著警棍,對手無寸鐵的人投擲胡椒霧和催淚彈。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香港即已處在「非常」狀態:在流血的街道,警方射爆抗爭者的眼球、跨坐在人們脆弱的頸椎上、執法者趁虛強暴與輪姦、製造無辜者自殺假象……,當生命自由受到剝奪,每個人都帶著相似的傷痕與負罪感。離開,或者留下?成為隱隱作痛的問題。
安全感的匱乏,注定了「家」成為核心意象。韓麗珠作品多次談及家族血緣相連的束縛,《半蝕》則自言,自己是很早就決定離家的人,自此「家」一直以空缺的形式存在她體內。這個隱喻是如今的H城。許多人離開了,而沒有離開的人也成了意義上的離家者,要在不斷離開的過程中,想像家的樣子。書中巫言般喃喃追溯祖母與母親的話,彷彿從靈魂深處,承繼她們對此地的執念。曾經想逃離「家」,如今因為想念,以及看清人與人命運相連的本質,決心不離開。詛咒也是愛。
如何不只有「恨」,是為這本傷痛之書的基調。這亦是香港人面對暴力時的自問。或許是為了喚醒、不忘記安全無虞的感受,在秩序遭瘟疫中斷了的穴居時期,韓麗珠在一個安靜空間裡,想念著點點溫暖的日常:母親的烹煮、中藥和瑜珈、白果貓與動物們……,筆調暖而軟,靜好,不受攪擾的呼吸節奏,自成一片原始森林。傷害多巨大,溫柔竟有多麼巨大。世界崩頹時,她以自身為一顆行星固定轉速下思考,書寫,重建生活秩序。
那麼,延續韓麗珠長期以來對H城的探討,《半蝕》所揭示的此刻,如何連繫到未來?
沒有人會相信,這是個可以自主的城市,因為它一直沒有根莖,只是依附在更巨大的權力之上。然而,這個城市真正的主幹,其實是反覆的消逝和變形──在虛無中創造。當它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壓和攻擊,就意味著人們漸漸看到自主的雛形。(p.435)
離開,或者留下。愛,與恨。生,以及死。H城是矛盾的,卻在疼痛之中強烈地感受到存在──正是此時,人們與土地前所未有地緊密。「當下」的意義顯現:《黑日》寫2019年反送中抗爭時,即有意識地組織、穿插2014年雨傘運動,時空交映,威權幽靈從未遠去,且有封存當下,與時間相抗的意味;《半蝕》更進一步揭示此時/此身/此城命運相連,互為因果的狀態。面對所有的大死、小死,以及新生,處理傷痛,即為正視歷史,那是最貼近個人的真實,而非包納在更巨大的群體(國族)聲音之中。《半蝕》給出信念:直面脆弱,凝視發燙的傷口,此時,此身,此城,不在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