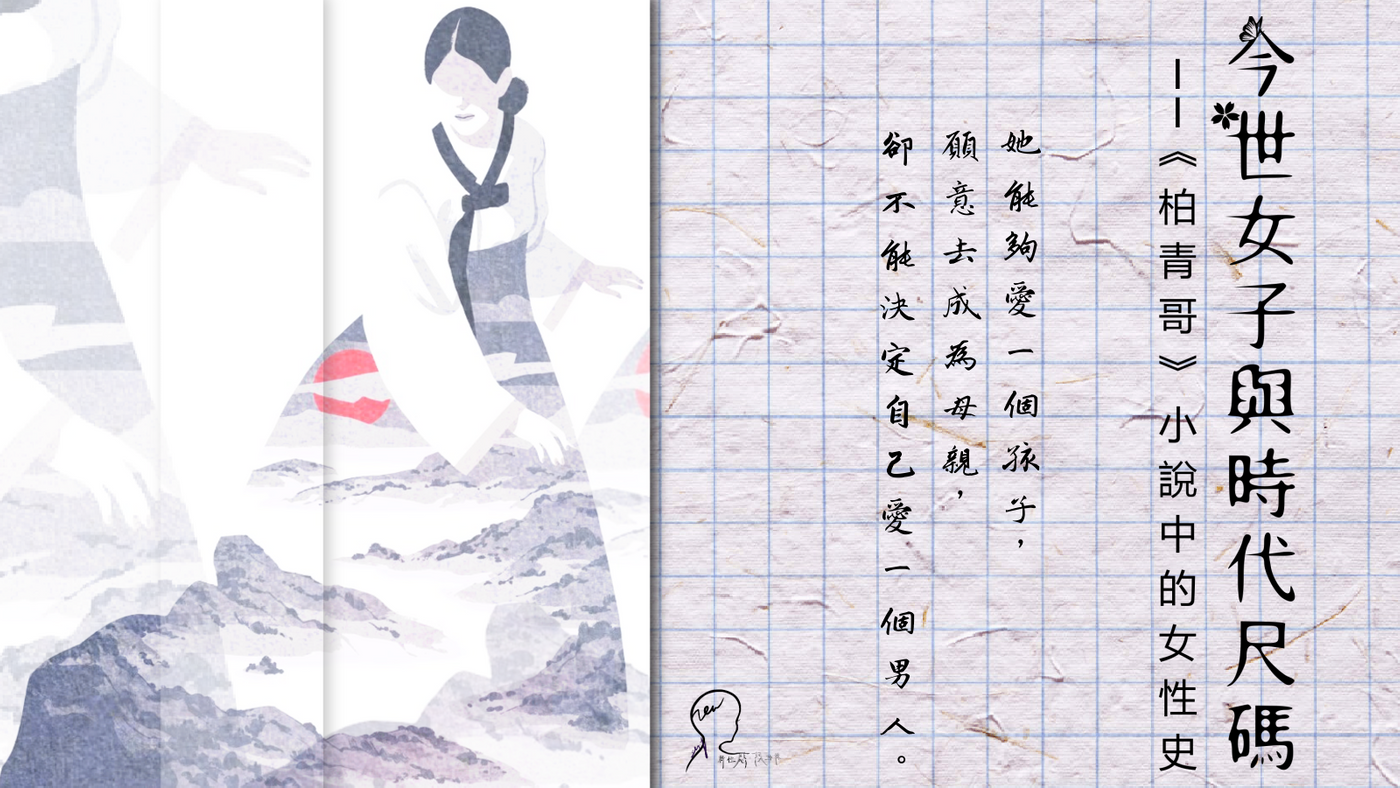女性在文学中的位置,不管是创造文学的、还是被文学创造出来的,都有一点类似于灵媒的角色。

我对一切“恐怖”“惊悚”感兴趣,但一方面又觉得它们实在太过于露骨(或是面对它们时的“兴奋”露骨),一旦承认了自己喜欢,就很容易被人看穿。仿佛这是一个肮脏的令人不齿的癖好,大多数时候都算不上是“美”,即便有种难以捉摸的玄妙,也经不住片刻的凝视。因为它很快就会导向死亡和毁灭,消失不见,只留下满地狼藉,血淋淋的、不堪的、脏污的,以及仅仅留在躯体上的害怕和恶心。
我很喜欢看恐怖片,甚至于到了成瘾的地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平白无故地发作一次。当我一口气看很多恐怖片的时候,心里有个声音在说:白痴,看个够吧!眼前只剩下一些充满了暗杀、血淋淋的骨头、或者是一个惨白如纸的形象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的东西,于是那份羞耻感又迅速升了起来,它讽刺地提醒我,我所感兴趣的不过是这样一些怪东西,世俗所谓的令人恶心的一切。
但我坚信,在这些参差不齐的作品中(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垃圾),一定有真正的“恐怖”逃走了,那才是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它是不可名状的、未知的,而那些肉眼可见的邪恶,只是它微不足道的征兆和暗示。关于恐怖,还能想起来什么。耳熟能详的爱伦·坡,曾经看过的恐怖电影留下的破碎画面,小时候在书店看犯罪和恐怖小说不敢回家的傍晚,好奇但没来得及打开的一个个魔盒……它是无穷无尽的,关系着古老的过去和一个崭新的未来,那是一片兴趣盎然的天地,我们的视野在不断扩大,障碍被打破,它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和联想。
大部分描写黑暗主题的作品,在降世时都受到了批评。即便到了今天,一部恐怖电影、恐怖漫画的名声,往往伴随着观众的恐惧和逃避,只有少部分化为赞赏,使作品与其创造者获得应有的尊重。
但是像我一样的爱好者肯定不在少数,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在生命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抱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羞耻心,不便与亲密的人分享,只好躲起来观看更多的恐怖作品,默默吞下所有故事,不愿开口?我想找到这样的同伴,不是在兴趣天地里赤裸地表达自己就是爱好一切血腥、谋杀、尸体和鬼魂的那帮家伙,我希望他们是“恐怖”的创造者。
一直以来岌岌无名的洛夫克拉夫特出现在我面前,但对于那些早就意识到要找到这类同伴的人来说,他的名字或许如雷贯耳。洛夫克拉夫特是一位著名的哥特小说家,写作小说之余还撰写了一篇关于恐怖文学的论文《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正是这本书,帮我找到了更多的“同伴”,向我开启了这个世界的大门。
我对“恐怖”感到兴奋,并且发现它几乎串联了所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死亡、女人、疯子……而且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由一个女人写出来的。女性在文学中的位置,不管是创造文学的、还是被文学创造出来的,都有一点类似于灵媒的角色。
洛夫克拉夫特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似乎还有些轻视第一个写作恐怖小说的女性,认为《弗兰肯斯坦》“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归功于其丈夫雪莱”,但他还是给了这部小说应有的赞誉,“是所参赛对手中唯一精心完成的一部完整的小说。”
透过洛夫克拉夫特梳理的这部恐怖文学简史,我们看到了大量熟悉的女性作家的名字,玛丽·雪莱、简·奥斯丁以及勃朗特姐妹,她们都创造了出色的哥特小说。而这几位,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前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女性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也正是自由的女性主义意识开始启蒙的时候。她们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小说里创造如此恐怖的意象?弗兰肯斯坦、呼啸山庄里的鬼影幢幢……这些女性作家仿佛是在被包裹的时代找到了一些缝隙,在这些艰难的缝隙中才得以生长出更加有力量的东西。
但即便故事得到广泛传播,其中这些恐怖的幽灵终于穿透森严壁垒的父权机制,为世人所熟知,但它们的创造者却迟迟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很遗憾,那个时代忽略了这类女性写作者。
《弗兰肯斯坦》最开始的1818年版本并没有玛丽·雪莱的署名,直到1831年的第三版,玛丽·雪莱的名字才出现在书中。就连恐怖文学的爱好者都认为,她这部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归功于其丈夫雪莱。
现在终于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天才的艾米莉·勃朗特,她的《呼啸山庄》在出版后也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甚至被评论界的某些人斥责为““一部骇人听闻、荒谬绝伦、毫无意义的作品”,“一部恐怖的、令人作呕的小说”,“小说充满阴森恐怖、病态心理和异教思想”。即便后来终于承认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奇特”作品,也宁愿相信它是出自其兄勃兰威尔之手或兄妹俩合作写成。人们怀疑的是:“一个蜗居山乡、从不接触异性的二十多岁未婚女子,怎么能写出爱得这么深、恨得这么透的爱情和复仇小说呢?她的体验从何而来?”
写作《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的洛夫克拉夫特一生创作恐怖小说,与艾米莉·勃朗特的遭遇相似,其创作无法养家糊口,生前贫困潦倒,默默无闻。也许是出于感同身受,他在这本书中对艾米莉·勃朗特的评价非常客气,他认为“作为恐怖小说和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堪称杰作”、“勃朗特小姐的故事不但恐怖,而且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强烈的反应”、“《呼啸山庄》是一个文学转型的象征性作品,标志着一个新的更加健康的流派的发展”。
这种感情最终还是导向了对恐怖文学的怜惜,洛夫克拉夫特在本书的尾声中说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恐怖文学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它是人类基本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尽管显得狭隘有限。但对那些为数不多而思想特别敏感的读者来说,它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明天的杰作无论诞生于幻想或者恐惧,都将会因其艺术技巧而不是因其值得同情的主题思想而得到人们的接受。然而,谁会公然声称:黑暗主题是文学王国里的一位正派的但是又是地位卑贱的三等公民?难道它不正如托密勒的玛瑙杯那样——美轮美奂!”
恐怖小说位于文学王国的边缘,女性则更是处于其边缘的边缘,为恐怖文学的正名,也可以为女性写作的文学带来一丝丝光辉吗。但至少,他们因相同的命运而被裹缠在一起,互相映衬,直至发出托密勒的玛瑙杯那样美轮美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