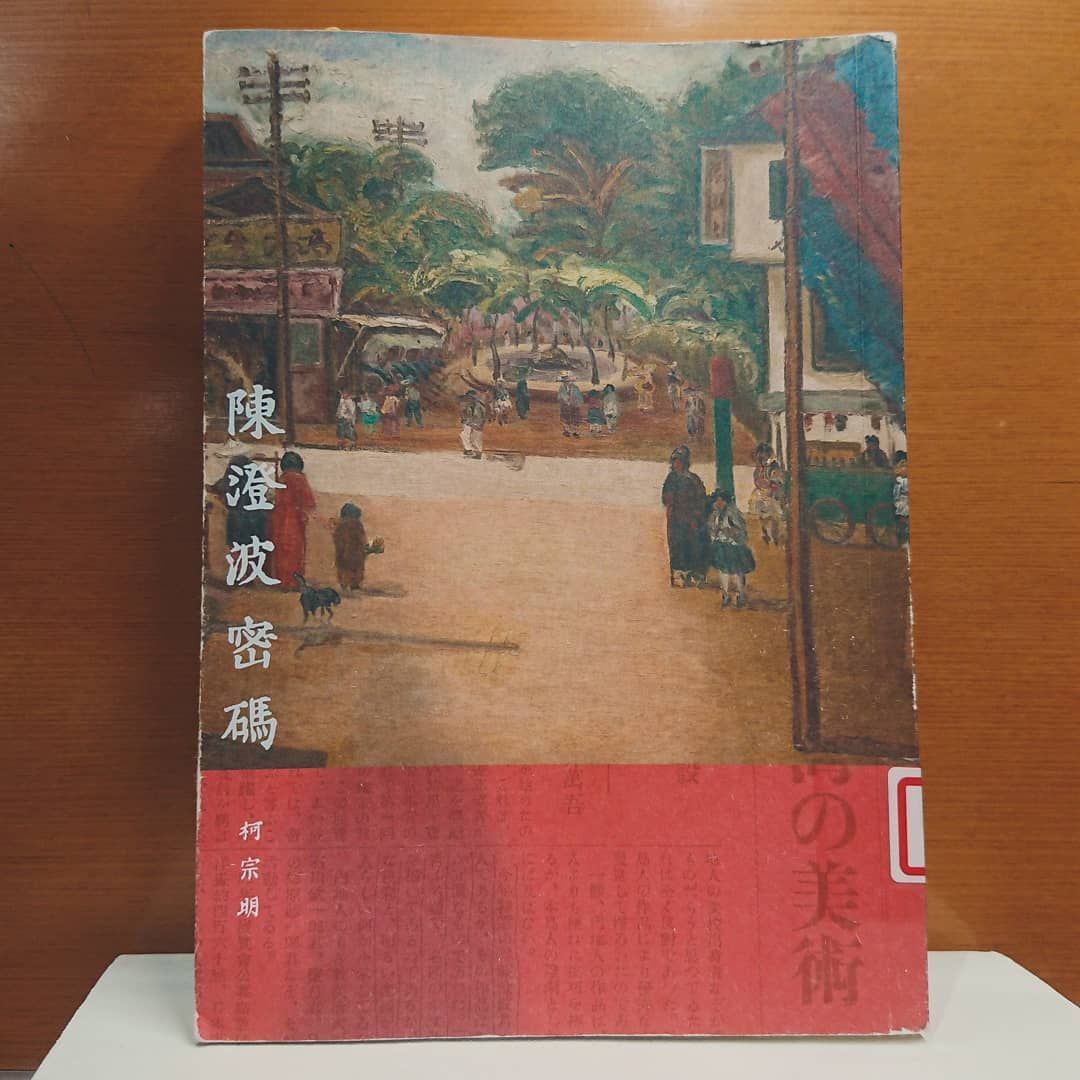【如果在臺灣,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中國人】
1994年,剛出版《打狗歲時記稿》的高雄文史工作者林曙光,接到他在《台灣新生報》副刊工作時期主編史習枚的逝世消息,感念之餘,他洋洋灑灑寫了36張稿紙的篇幅,來悼念這位他心中「首倡建設臺灣文學的先驅者」。
史習枚是誰?或許有些人對他的筆名「歌雷」更熟悉一點,他從學生時期就對文學編採有興趣,隨後渡海來臺,創辦「橋」副刊、為臺灣文學與作家開拓一方空間,卻也不斷面對來自黨和政府的壓迫。
他是中國人,但自詡自由主義者。他還不了解臺灣,但想建設一個臺灣文學的空間。
他是《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他有一個建築夢。
【他信奉的是理念,不是黨】
史習枚在學生時期就展現了對刊物的編輯興趣,出生江西九江縣的他,1940年代初考上了因中日戰爭遷校至重慶的復旦大學新聞系,當時復旦大學有濃厚的文藝氣息,200多個社團中無論文藝或非文藝類,皆在發行刊物上闢有文藝園地,壁報形式的刊物也超過50種。
或許是浸淫在這樣的氛圍下,史習枚於1943年創立了「新血輪社」,發行刊物《新血輪》。有趣的是,這個社團的社址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青年館中,青年團由國民黨設立,招收16到30歲的青年,以培養抗戰建國的新血為主,回看在中國語境下與新血同義的「新血輪」,不難想像社團背後隱含的政治性。

史習枚與其中幾位同學正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員,但思想上是較為溫和的中間派,他們對《新血輪》的想像是:「一份不偏不倚、不受人唾罵、也不擔風險的中間報紙。」上面有學生關心的話題、時事,偶爾也有一些不受校方喜愛的言論,其中闢了《文藝》和《時與地》兩個文藝副刊,也收到許多來稿,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的副刊主編經驗。
只是若因黨政而生,也有很大機率因黨政而亡。
《新血輪》後期內容被青年團認為有左傾傾向,因而直接出手將「新血輪社」改組,史習枚等五位編輯成員決定在發行完第一百期《新血輪》後集體辭職,像是對組織的消極抵抗。
但史習枚沒有因此離開編採,1945年他邀請了同寢室的新聞系學弟馬克任與魏端共同創辦壁報,名字正好就叫做「橋」,站在親國民黨反共產黨的立場,張貼在五十多份壁報中忒有份量。不過他大概沒想到,「橋」這個名稱會一路跟隨他往後的人生。
學生時期的史習枚雖然加入國民黨下的組織,但他信奉的不是黨,是三民主義所說的民主自由,是對於社會與人民的關懷,這也讓史習枚一再因此受難。第一次國民黨直接瓦解他發行將近一百期刊物的社團,第二次則是他張貼了一張批評國民黨的壁報。
這次,黨要抓他。
剛從新聞系畢業以助教身分留在校園的史習枚決定逃跑,他想起已經去臺灣的表哥鈕先鍾在《台灣新生報》擔任主編,或許能夠投靠對方。
1947年夏天,史習枚來到臺灣這座在二二八剛流過血的島嶼,他沒想到,這場血其實還沒流完。
【「橋」上風景】
同年8月,他成為戰後第一份官營報紙《台灣新生報》的副刊主編,以歌雷為筆名展開文學活動。在為副刊取名字的時候,史習枚沿用了大學時用過的「橋」:
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誼,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
這段話被刊在第一期作為刊前絮語,他藉由「橋」讓當時的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相遇、讓中國文學與臺灣文學相遇、這座橋也讓史習枚自己從對臺灣文學一無所知,到後來說出想出版《臺灣作家集》介紹臺灣文學。
他知道生於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在1945年後,一時跨越語言到中文書寫有一定難度,因此請了後來寫下這份悼念手稿、精通日中兩種語言的林曙光擔任臺灣作家文章的翻譯工作。林曙光當時還只有20歲,而承接副刊主編大任的史習枚也不過是個大學剛畢業的20出頭青年,林曙光在手稿中形容初見時史習枚是一位「年輕白皙留有鬢毛的美男子」。
當時年輕有活力的史習枚常請副刊的作家們吃飯座談,林曙光也常被招待上館子,史習枚讓所有人一起討論這塊由自已開闢的園地,他樂觀浪漫、闊綽大方,也向橋副刊投稿的孫達人就回憶:
他看我抱著幾本舊書竟對我說:「達人,你又去花錢買書,把錢花完了吧?喏……」他伸手從口袋掏出三百元塞進我手中:「這算你的預支稿費好啦!」我大笑起來:「哪能這樣,你知道我要寫什麼?」他笑著說:「沒關係,別客氣,以後沒錢花時儘管向我預支好啦!」
在有了發聲空間後,本省作家開始討論起「臺灣文學」該是什麼樣子,外省作家也提出想法加入,成了後來有名的「橋副刊論爭」。作為主編的史習枚將這些想法一概整理發表,他自己也多次提出認為臺灣文學應該要更加反映現實、打破傷感氣氛等。
在戰後因為從日文到中文的語言轉換,一度消沉的臺灣文學在過程中似乎要長出新的形貌,史習枚搭起橋的一端,邀請原先互不相識的本省與外省作家們上橋,一起決定橋的另一端該往哪裡走。他們在橋上大聲吆喝、偶爾大笑、偶爾吵架,整座橋的樣貌正逐漸清晰完整。
當時史習枚也許曾想過另一端的風景,卻沒想過橋有一天會垮。

【那一天,文學橋樑垮了】
1949年4月6日清晨,史習枚位於懷寧街大樓二樓的新生報員工宿舍大門被敲響,他前去應門,見到的是將自己上銬逮捕的便衣警察。他一時沒能搞清楚狀況,直到看見常在橋副刊投稿的楊逵也在,才想起前陣子拒絕刊登但出現在上海《大公報》上的〈和平宣言〉惹怒了省主席陳誠。
囚車緩緩開動,史習枚坐在其中,「橋」副刊在幾天後被迫停刊,結束了為期兩年多一點的223期生命。政府粗暴折斷他的橋,那些曾經想像過關於臺灣文學的未來,全都成了往後幾年牢房中的死灰牆面。
林曙光並不完全清楚史習枚的狀況,就讀他就讀她師大史地系的他也面臨學生宿舍被警察包圍臨檢,他只知道史習枚與楊逵一同被捕、橋副刊也停了,而等他與史習枚重逢,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後。
★作家小傳
史習枚(1922-1987),筆名歌雷。江西九江人,重慶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1947年來臺擔任《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於1949年四六事件中被捕,輾轉關押至1954年保釋。出獄後開過廣告公司,任職《聯合報》與《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病逝於臺北榮總。
林曙光(1926-2000),本名林身長。戰後返國在台北就學、擔任記者,先後經歷二二八、六四等重大事件,也曾參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協助本土作家翻譯日文作品。後因北部局勢動盪回到高雄,轉向鄉土文學和地方文史研究,後期為高雄保留下大量珍貴的在地民俗、諺語和民間故事,著有《打狗滄桑》、《打狗瑣譚》、《高雄人物述評》等書。
★團員簡介
高于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在學中,喜歡書寫,也喜歡學術研究。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北市文學獎等,入選九歌109年度小說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