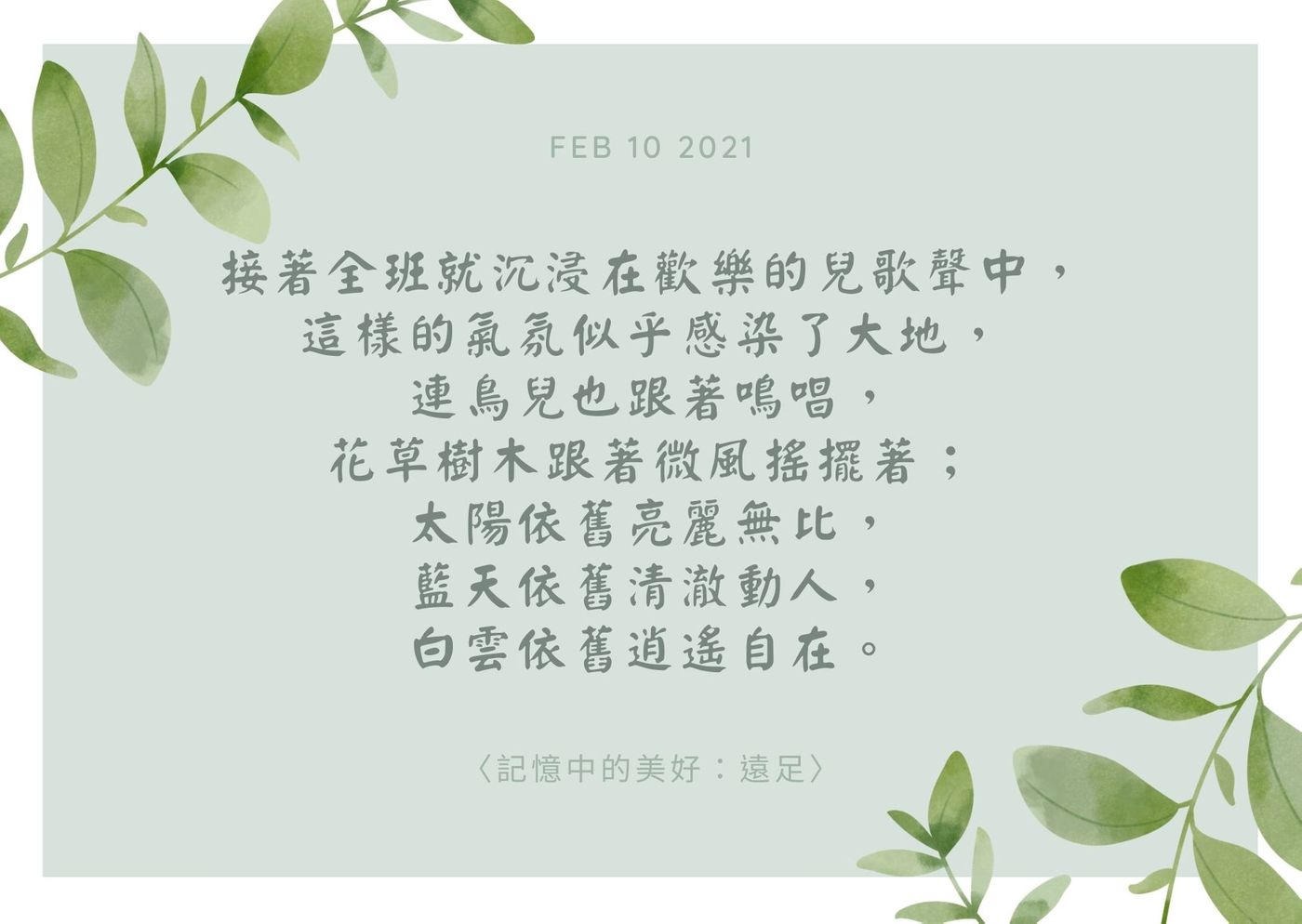走進小坡,他曾經是那樣的熟悉,沿路往上,毛茸茸的狗尾巴草、割人的長草、一碰就嬌羞起來的含羞草、看起來有點刺刺能黏住衣服的種子球,這些曾經的玩伴已經成了一棟棟不可褻玩的屋,回憶的風是蔓延的,隨著熟悉又不熟悉的路徑,纏繞入心駐紮了下來。
我們這群小瘋子自然不到晚餐時間是不會回家的,阿嬤的晚餐時間很早,大約是下午五點,夏季夕陽西下的晚,這條橫在斜坡上的巷子,陽光並不熾熱,這時候阿嬤會走出家門,和鄰居們聊天,而潑猴們自然在他們眼皮子底下繼續撒野,當然遊戲區域不僅僅是這條巷兒,還包含了坡底下的那間雜貨店呢!呈現一個口字,騎著腳踏車溜下去,又將腳踏車拉回來,不騎嗎?騎不動啊!往往一半就得推著車往上。那怎麼就不超出這個範圍呢?
小坡第一個巔峰是司馬中原的家,拐個彎上去住在我家上坡的鄰居種著一塊兒三角形的地,上面阡陌分明的一攏攏的蔬菜排列其上,那些鄰居們經常會互相送著幾把菜,偶而也會集體帶著剪刀,上去隨便剪幾把地瓜葉。當晚就會有鮮嫩的地瓜葉可吃,地瓜葉老了,就算咬了百來下,還是會在嚥下去的那一刻卡住喉嚨,讓人抓心撓肺,費了老勁兒,才能將他們吐出來。
那時候的我們晚上經常聽著司馬中原說故事,殭屍們深入到我們的腦海,總覺得往上挺恐怖的,明明司馬爺爺也是個可親的人,偏偏我們見著他除了招呼打了聲,也不敢靠得太近。還有小坡往邊兒還住著幾戶人家,他們往往都有一個小樓梯,才會進到房子內部,那個門並不高,總愛用著像籬笆的鐵矮門,裏頭都養著德國狼犬。
那狗兒遠遠看很可愛,帶著點傻氣,然而靠得近了,他們就開始狂吠,那個吠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的跳躍能力,他們跑上樓梯奮力跳出籬笆門,那個瞬間我們彼此之間玩得就是心跳,幾個小毛孩心跳加速的看著他,計算著距離是否能夠跳出來?就在他們跳出來那一瞬間,一夥人不約而同地往家的方向衝去。
汪汪叫的狗、驚聲尖叫的孩子們,喧嘩在這個無人的午後,我們衝進家門,關上了那個籬笆鐵門,以為進入安全區域,門外的狗依然不死心的狂吠,我們驚魂未定的跟他對峙著,想著他們應該進不來,所以放下了心,對著他們挑釁著,你問孩子們怎麼挑釁狗?ㄜ~~就是做鬼臉啊!狗好像感覺到我們的鄙視,開始續力追擊,跳進了籬笆們,我們又一次火速衝回屋內,鎖緊了門,任他們在外喊叫,但這個午後外出時刻也被他們報廢了,只剩下屋內的躲貓貓可玩了!
另外一邊的小坡往上,直上死路,轉角有一個安靜的角落,往下就是朱天心朱天文他們的家,但是我們與他們從未照面,也就是知道鄰居有這麼些名人的存在,那一個區塊因為又安靜、又沒樂子,只有想探險的時候,才去那邊開發新的領域。這些以為早已隨風而逝,卻又隨著自己腳步越走越遠,讓風盪了回來,那些暖洋洋的午後時刻,在心裡歡騰著,然而隨著腳步走遠,攀爬而上的竟是說不盡的想念。
風起了,吹散了人兒,也吹散了那時的景兒,留下的就是那些片片段段,是棉花糖的甜,嘴一抿也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