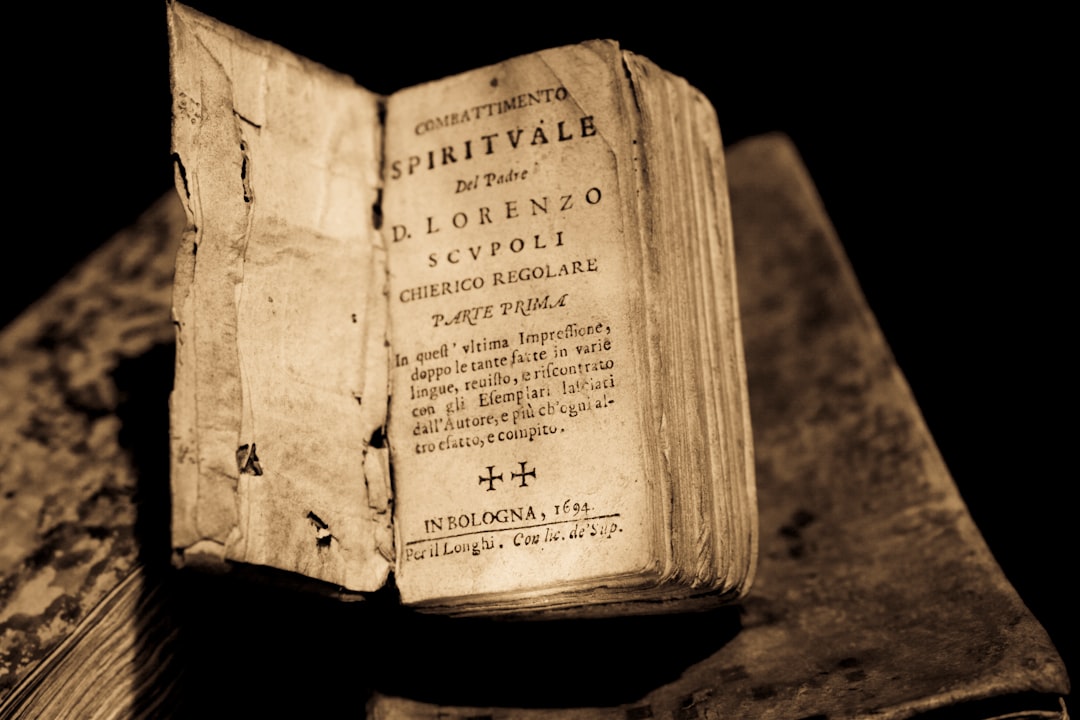——《想死的愚人》導讀序 撰文|馬千惠
像是童話,也像詩,像繪本,也像口傳的故事。也許詩人從來甚麼都是,畢竟世界上最早的史詩既是報導文學也是神話,成就了偉大悲劇的出現。也許詩人什麼也都不是,他們只是將遠方的故事帶回來,如水一般,流過一個村莊一個地方,語言是他們的刀筆,在人心裡留下刻痕。
「想死」,
就像戀愛的心情一般
踮著腳尖到來了
就像細雨一般
潤物無聲地到來了 ──孫得欽《想死的愚人》
小時候學塔羅牌,0號牌是愚人。那時抽牌總不解:為何是愚人?看起來聽起來都不是個讓人愉悅的角色,畢竟這世界,誰想當愚笨的那一個?可到現在,人過四十,身邊的疾病與死亡像土壤累積,聽到誰生病而誰又在應當壯碩豐美的時期離開。死神的鐮刀不問老少男女,也不看壯志未酬,一下揮來,無人可擋。
也是到了四十歲,憂鬱再也不像一條黑狗,而是個不太友善的朋友,出現時總伴隨陰影。年輕時關於愛與明亮的那些事情,到了這個時間點,如同得欽筆下的愚人,想死的念頭顯得那麼溫柔旖旎。
念研究所時,得欽是學長。那時都知道二年級有寫詩寫得非常好的學長,但當時的我不懂詩,只知道詩句高貴。可是年輕時的自己,越是那些高不可攀的事物,越是膽怯。我一邊讀詩,一邊想詩是什麼。至今我仍讀詩,仍在想詩是什麼,只是隨時間過去,好像逐漸靠近一點點,卻仍然不懂。
但我喜歡這次讀到的這本書。
像是童話,也像詩,像繪本,也像口傳的故事。也許詩人從來甚麼都是,畢竟世界上最早的史詩既是報導文學也是神話,成就了偉大悲劇的出現。也許詩人什麼也都不是,他們只是將遠方的故事帶回來,如水一般,流過一個村莊一個地方,語言是他們的刀筆,在人心裡留下刻痕。
有段時間努力想理解詩是甚麼,但都撲了個徒勞,詩從來甚麼都「是」,高高在上的睥睨所有文類。沒有一個文類這麼靠近語言的本質,也許這便是詩高貴之處。可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一開始在這個過程裡打轉,轉到最後只能繼續讀。讀詩也許也像愚人一樣,一邊痛恨著,一邊愛著。像這本書裡的愚人想死,但惡魔愚人不許他死。惡魔愚人的出現像個嘲笑,帶點愉悅,有點開心。哎呀哎呀,幹嘛呢要烤肉也不找我呢?讀到愚人想方設法的去死,而惡魔愚人快樂的破壞,那瞬間生死與成功失敗的倒轉,那麼有趣而輕快。
如果討論這本書,彷彿又與塔羅牌緊密相關。那些關於成為一個人的追尋(愚人),與那些對於慾望的渴望(惡魔),我以為一個是生的旅程,而一個是死的控制。但相反過來,不也說得通嗎?帶點戲謔的惡意,生活有時宛如嘲笑一樣:想死嗎?那就破壞你,叫你好好的活著。
(而壁虎那段,誰會忘記研究所時真的有一位學長很怕壁虎呢?看著看著幾乎笑出聲來。)
(那瞬間,我感覺我帶上了惡魔愚人的面具,帶點惡意與嘲弄的……)
然而想死是什麼呢?活,又該怎麼活?
我們都來到四十歲,照理來說應該要成熟,卻好像還很年輕,二十歲的時日還不遠,眼前已經是五十、六十歲大關,死亡本來就不遠,現在更近了一些。愚人,我想與其說想死,不如說更是想活吧。只是活著該怎麼活,如聰明愚人所說的那般。如今現代人,誰不聰明呢?誰沒有一點心理諮商的經驗?誰又沒找過算命師?死這個經驗太大,從未有一人歸返來敘述死亡的彼岸到底長甚麼樣子。讀著讀著,我感覺自己是那個想死的愚人,在追尋死的旅程裡活著,思考著何謂死,而甚麼又是生活的滋味。
原來成熟的想死是這樣的
原來成熟的活著是這樣的
我不禁又帶上了惡魔愚人的面具,想著:也許這是詩人的潛台詞。
只是誰知道呢?
所以,隨著書頁,我與愚人並肩,開始漫長的散步。
讓我們從詩的討論中離開一下,來說一下漫畫。
看過《致不滅的你》嗎?那是一個未知生命,從祂自遠古誕生起,經過一段段生命歷程,總是一次次相遇,又一遍遍分離。這首詩讓我想起這部漫畫,也讓我想到我們身體裡那不滅的靈魂。也許我們都該相信轉世,相信靈魂不滅。因為這樣所有吃過的苦,在過去在未來,都有了意義。因為你必經疼痛,而下一世轉化為甜美。也許因為這樣的旅程,物質世界裡那些悲哀的傷害,都有了救贖。與其說是在讀詩,不如說在觀看一場靈魂的旅行,或是某個悠長祈禱中的禱詞,在那流轉的畫面中,牽引前往向一次一次的轉世裡。
至今我仍不明白詩是什麼,但仍喜歡讀,喜歡詩人們運用語言的方式,喜歡那近乎神話般的敘述。我好奇愚人接下來會走去哪裡,他仍會想死嗎?他仍會散步嗎?他會往回看嗎?在所有的轉世中,他將去哪一世?
最幸運的工作莫過於此了吧,創造出一個世界,引人無法自拔。像愚人花園裡盛開的花朵一樣,每一樣事物都可以成為花朵。但不幸可能也源於此,因為自己也深陷其中。如想死的愚人、惡魔愚人與聰明愚人的三位一體,凡事皆是,凡事皆否。詩是這樣,創作亦然。
期待得欽未來的詩作。
馬千惠/台灣埔里人,自由工作者,寫字調油調香占卜維生。喜歡讀書看星星,與愛人同處一室一言不發且長長久久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