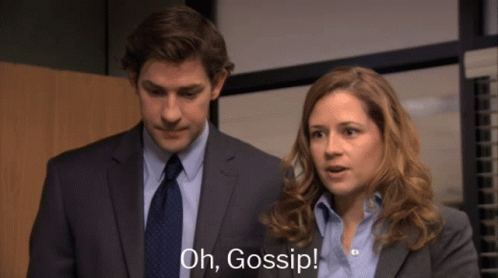最近幾個月都會固定從圖書館借一部宮部美幸的作品。從《落櫻繽紛》開始,陸續讀了《繼父》、《相思成災》及《模仿犯》。(題外話:覺得宮部的簽名好可愛。)
推理之外,是一種活著的方式
目前讀來,作品吸引我的地方在情節裡的層層推理,讓人欲罷不能,很想趕緊知道發生什麼事。事件展開時呈現出來的人情味及傳遞出對社會現象或人生哲學的觀察與反思,讓作品更有深度。
如《相思成災》中說的:「然而,十七、八歲的小鬼頭,就是不明白人生的漫長。只看得見此時此刻,不非黑即白地劃分對錯就過不去,才叫年輕。」感受到歲月帶給宮部的洗鍊,卻不覺得是以上對下地說教。有趣的是,小說中的要角基本都不是主流定義上的「完美」,但都很有個人特色。例如《落櫻繽紛》的古橋笙之介,出生在武士之家,但握筆卻比握劍還行。被母親和哥哥視為懦弱的父親,他的度量及溫柔卻深深影響著笙之介。
又如《相思成災》中長相抱歉的井筒平四郎,起初覺得他是「出一張嘴」的官員。但藉由井筒的視角一步步剖析事件,會被他細膩的觀察力折服。而其外甥弓之助,家中富足、擁有天使般的臉龐、聰明機伶,卻還會尿床。這些反差讓人覺得角色立體,容易產生共鳴。
或是《模仿犯》裡愛護孫女鞠子,一身勁骨的爺爺 有馬義男,與直覺敏銳的刑警武上悅郎,在書中都是禿頭矮胖的設定,卻不減他們的人物魅力。
之前覺得喜歡宮部美幸江戶時代的小說更甚現代,雖然人物名字很多,我經常會搞混。大家的名字真的太像了...例如○兵衛、○之助、○衛門、○○郎。
我很喜歡故事中的長屋場景,總有俠義、率真的鄰居,如《落櫻繽紛》的阿秀或《相思成災》的阿德。且因為他們的接地氣的個性,更能感受到人情味與生活的煙火氣息。
從《模仿犯》讀出人性的裂縫
直到讀到《模仿犯》,發現自己愛到不行,除了吃飯睡覺外都在看小說。劇中的兇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壞,而是使出人性上真正的「惡」。不把其他人當人,將被害者玩弄於指掌之間,剝光她們的自尊,甚至捉弄和精神折磨受害者親屬。
栗橋和兇手X擁有許多人稱羨的特質:外型亮眼、知性、頭腦聰明,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但諷刺在自以為高明的步調卻是被他們口中的「低等人物」—溫吞沒存在感的和明、休學的高中生塚田真一、豆腐店老闆有馬義男打亂。讀來心情緊張的同時又覺得大快人心。
小說中除主線劇情外,還有大大小小的支線劇情。讀來不覺冗長,反而讓故事更加飽滿。我認為在於作者沒有偏頗某個角色,她可以感性的描述人物對事件的衝擊及心境變化,但又是理性、與角色拉開點距離的敘述故事。
輿論對女性角色的雙重標準
情節中也不乏對受害者及社會輿論的探討。受害者接二連三地被報導出來後,民眾除了同情外,心中也忍不住有「受害者本身的行為是不是有問題」的想法出現。或是小孩差點被誘拐,妻子卻被丈夫和婆婆責難,認為都是「媽媽不夠盡責」。以及遇到騷擾不敢報警,就怕被說閒話。
讀者是以上帝全知的視角來閱讀,知道事實並沒有那麼單純。不過,當切換到現實世界時,我們還能這麼理性和包容嗎?
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模糊地帶
小說中對於如何報導重大事件的切口也令我印象深刻。通常事件發生後,我們習慣於揣摩行兇動機、分析兇手作案心理,與如何防範再次發生,往往忽略受害者及其親屬的聲音。
當我們是外人時,了解動機出自「八卦心態」多於同情,報導方向自然也偏向大眾預期心理。可假設當我們變成相關受害者及其親屬呢?加上沒有相關的機構及法條提供被害者親屬,導致有心人士趁虛而入,這樣無疑又加深了他們傷口之痛。
拿塚田真一和樋口惠來說,正常來看會認為塚田真一是可憐的受害者,但樋口惠卻認為自己安穩的家庭和生活被打亂了,她才是受害者。相較於塚田,除了要忍受失去至親的傷痛、無止境的自責,還要接收樋口轉嫁給他的痛苦。樋口可以肆意妄為的宣洩,但塚田呢?
讀到塚田真一和有馬義男,因同病相憐發展出跨世代、跨血緣的情誼讓人感動之外又很心痛。我很難想像如果是我,是否能像塚田那般超出年齡的智慧和理性,或是有有馬千分之一的骨氣。
我很喜歡宮部美幸的小說沒有「造英雄」的情節,無論是兇手、警察、受害者、記者…等,都會流露出人性上的缺點。也因為如此讀來會令人忍不住反思——如果是我會怎麼做。
接下來迫不及待想要讀《樂園》。是本作的續集,發生於模仿犯後9年,描述記者前畑滋子的內心世界。(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我好奇前畑滋子在這些經歷之後,內心會有什麼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