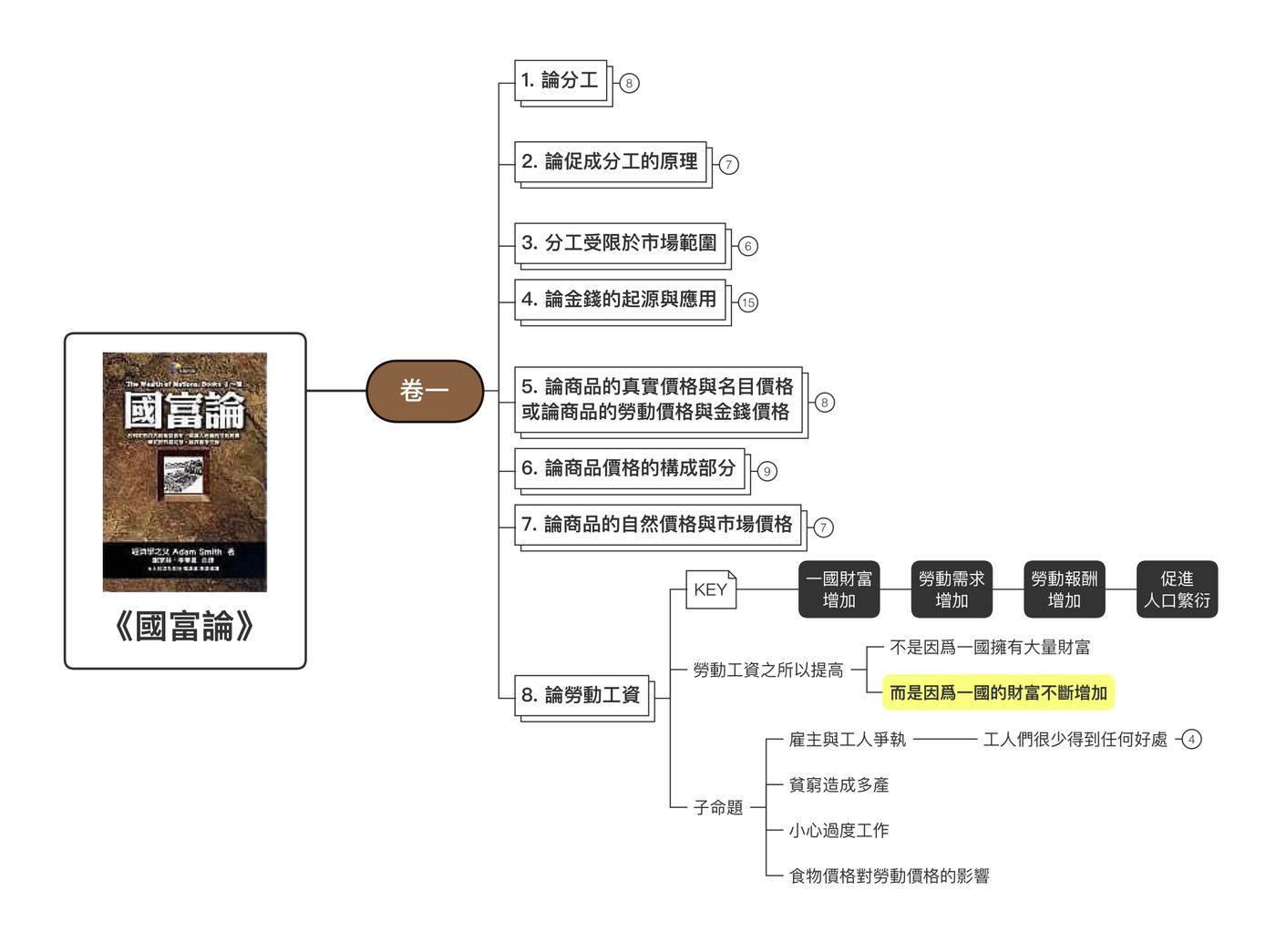強調薄利多銷的傳統代工思維與產業結構
過去20多年台灣人實質薪資不斷倒退,有分析認為與產業結構性有關。
1980年代台灣經濟以出口代工的製造業為主,當時工業與服務業的受僱人員過半來自製造業,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1990年台灣政府准許台商赴大陸投資,大量台資企業帶著資金和技術遷移,這波「去工業化」導致本土流失大量職位。
2001年中國和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後,國際貿易的分工結構改變,變成是用台灣的資本和技術,結合中國的密集勞動力,把產品外銷,得到好處的是台灣資方和大陸勞工,台灣的勞工就大受打擊。至於留在台灣的企業大多沒有產業升級,仍沒擺脫傳統代工思維,即成本導向、用廉價勞力賺取微薄利潤,這樣難以投資研發與創新,企業競爭力低,員工薪資自然難以上調。
另一方面,台灣大部分企業為中小企業及家族企業,不少還是由第一代把持,他們沒有永續經營動機,也不願把獲利蛋糕分給員工。
以數據來看,2021年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佔GDP的比重降至43%的歷史新低,反而「企業盈餘」佔比攀升到36.5%的十年新高,意味著經濟果實被資本家吃掉,受薪階層分到的不斷萎縮。
高薪的科技業與低薪的服務業的薪資差距擴大
2018年被視為台灣經濟的轉折點,中美貿易戰促使大量台商回流,部分將高附加價值產線移回台灣,台灣進入「再工業化」時代。
據經濟部資料,政府推出的「台商專案」截至2023年9月共吸引297家台商回台投資約1.2萬億元,創造超過8萬個職位。然而這些高薪職位只集中在科技業和少數製造業,台灣社會因此面對更嚴重的分配不均。
據104人力銀行的報告,台灣前五大高薪產業首位是「電腦及消費性電子製造業」,平均月薪5.8萬元;「半導體業」居次,平均月薪5.6萬元;其餘包括「軟體及網路業」、「鞋類/紡織製造業」、「投資理財業」,平均月薪都高於5萬元。最新數據顯示,台灣最高薪10%與最低薪10%的薪資差距擴大為4.12倍,創下五年來新高。
台灣自2018年起低薪勞工每年減少,但是結構不變,低薪勞工當中每年都約有35%為30歲以下人士,他們的行業分佈有六成是從事服務業,其中28%在住宿及餐飲業,25%在批發及零售業,這兩大行業都是台灣最低薪的產業。
因為入行門檻較低,大學生畢業生有高達七成半的人會進入服務業,之後就難以擺脫低薪魔咒。
勞權低落
除了國際貿易和產業結構因素,台灣人低薪的另一原因被認為是勞資實力太懸殊,勞工沒有議價能力,權益長期被壓抑。全台共有130多萬間企業,工會卻少於一千個,組織率僅7.6%,遠低OECD國家平均的16%。
這是因為《工會法》規定,要有30名勞工連署才能成立企業工會,但台灣有98%企業僱員不足30人,這些企業僱用了約43%的勞工,即有超過340萬人因該項規定無法籌組工會。反觀,鄰近國家及地區,日本、韓國、香港都是不到10人可組工會。
首先,分析背後歷史因素,日治時期職業工會非常活躍,但國民黨來台後實施戒嚴令,在1953年公布把工會屬性功能,變成只能辦勞健保的工會。國民黨丟掉大陸是因為勞工、農民運動,他們怕有社會運動,也會丟掉台灣。
即使1987年解嚴後,台灣逐漸民主化,但工會還是很少。有新的、年輕人成立的工會,但力量太小,只有機師、空服員的職業工會才是真的團結勞工爭取權益。其他就出現畸形現象,比如工會家族化,被老闆把持。
台灣龍頭產業科技界的老闆都信奉「無工會主義」,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對《天下雜誌》表示「好的企業,可以要求不要有工會」。大家覺得他是台灣代表人物,沒有人敢批評他,但其實阻止工會成立是違法的。連台積電都沒辦法組工會,其他企業更加不可能。
其次,在台灣的政治結構,無論什麼政黨都要靠資方捐款才有選舉資源,使得資方對政治和立法擁有極大影響力,可以阻止勞工權益的相關立法及改革。
如果台灣勞資力量持續失衡,低薪問題無法解決,短期會對選舉構成壓力,長遠會削弱年輕人對民主政治的信心,甚至助長民粹主義興起。
然而,只有制度性改變才能處理資方的過度影響,這要靠民主動員,也需要修改立法,包括適當調整資本在政治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但這一步相當難,因為各政黨未必有足夠動機和意願改變現狀。畢竟,他們也是受益的一方。
少子化和人才流失
青年低薪問題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台灣的未來,包括加劇少子化問題。目前台灣生育率全球最低,人口已經連續三年負成長。
又窮又忙的前景讓不少台灣青年失望而去,勞動部最新調查發現,有23%台灣青年想赴海外工作,首選美加,其次是紐澳,學歷越高的年輕人越想出國。
據主計總處統計,2022年下半年才放開疫情封鎖,台灣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數就達47.3萬人。疫情前的2019年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數是73.9萬人,其中30歲以下佔了20%,2012年以來持續增加。
根據官方調查,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回流台灣的海外工作者未來動向,有三分之一表示還會再出去,原因是海外工作更有前景以及薪酬更高,另外三分之二人當中,只有約略過半人表示會長期留台。
台灣人才流失,加上少子化嚴重,2021年已經開始進入「大缺工時代」,未來的執政者必須更積極解決低薪問題,包括完善法律及加快中小企業產業升級。
然而,這些措施喊了30年,在台灣都只是說說而已,不管哪個政黨都做不到。台灣的當局者唯有更務實的面對這些社會問題,不再說空話,台灣的低薪現象才會有解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