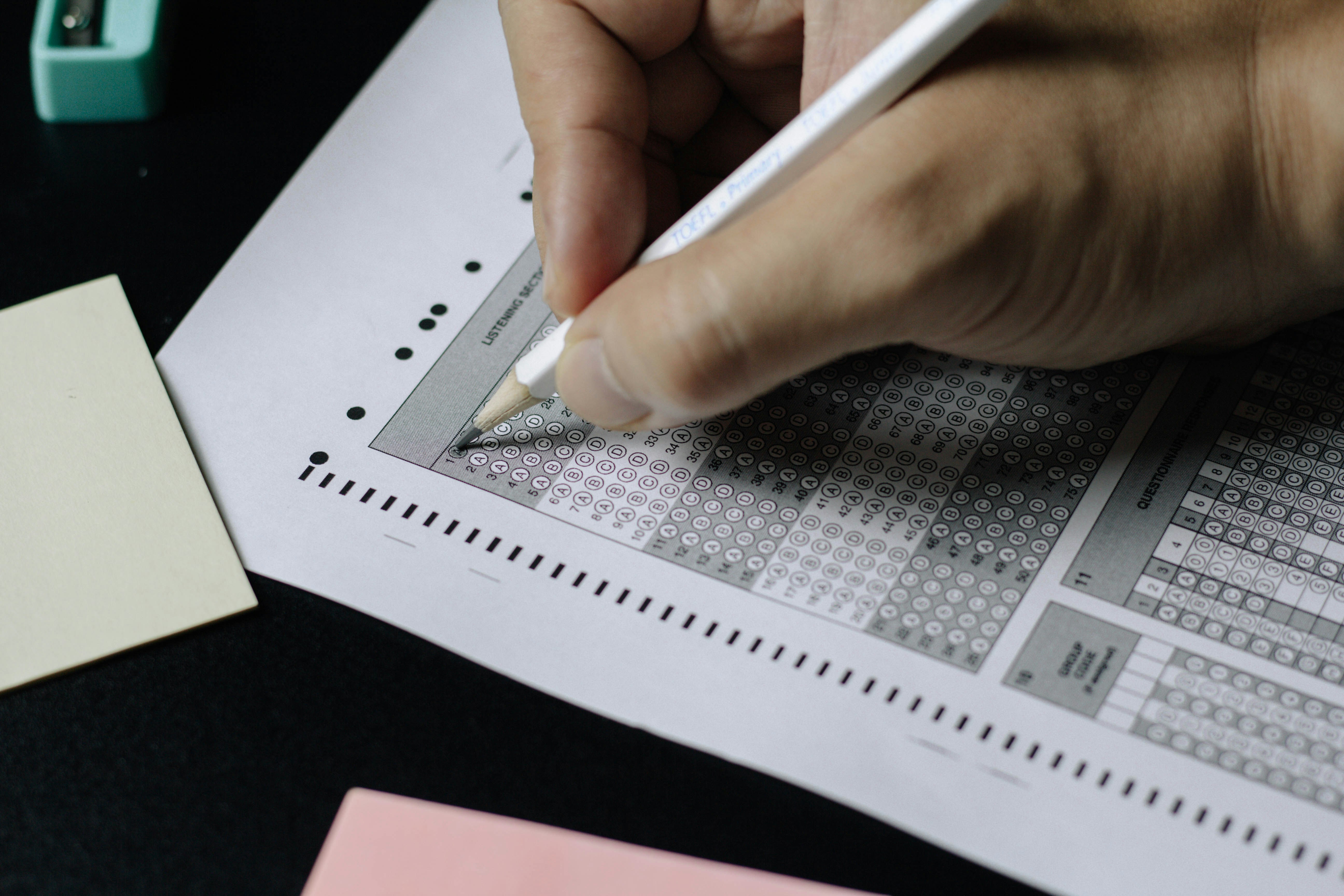民意長久以來被視為民主正當性的基石。
從選票制度、民調指數,到社交媒體的輿論聲浪,政治領袖、政策制定者乃至媒體普遍相信:「人民的聲音就是天意」。這套共識在幾乎所有政治體制中都能成立,無論是選舉制的民主國家,還是聲稱「代表人民利益」的威權政權。
某種程度上,民意就是政治世界的「顧客至上」——另一種版本的Customer is King。但這種信仰,真的經得起考驗嗎?
所謂「民意」,本質上是眾多個體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基於有限知識、強烈情緒、短期焦慮與群體心理所形成的集體判斷。
換句話說,它確實代表「大多數人此時此刻的聲音」,但這樣的聲音,能否作為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
我個人淺見認為:民意並非無瑕的道德指南針,而是人性限制下的情緒回聲。
我們將以中國的三峽水壩建設與其他民主國家的案例,來探討民意如何在不同政治體制中,展現出相同的人性局限:情緒化、短視、簡化傾向與群體暴力——以及,為何這些局限無可避免。
民意的四大局限性
A. 情緒主導,理性難持
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曾指出,人類大腦傾向於「快思」模式(System 1),這種依賴直覺與情緒的運作方式雖然高效,卻也高度脆弱。
當民意被激發時,往往並不是出於深入理解與邏輯推理,而是來自於憤怒、恐懼、焦慮或群體焦躁。
在三峽水壩案中,支持者普遍受到「民族自豪」與「現代化進程」的情緒驅動,視其為中國崛起的象徵;而反對者則充滿對家園被毀、環境破壞的憤怒。
兩種立場都呈現強烈情緒化色彩,且都難以建立在公開、透明、充分資訊的討論之上。
英國脫歐(Brexit)亦是典型例證。
回望當年,一句簡單的『take back control』把那些多年以來,針對移民與國家主權的焦慮,那些被遺忘的中下階層深藏的不滿一夕間爆發出來,迅速成為主導論述。
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事情並沒有像預期般變好,經濟反而陷入泥潭。當集體的情緒多巴胺退去後,大量選民後來才承認「自己當初其實沒想太多」,純粹是情緒表態。
時任總統卡梅倫,也因為過分高估『民意的理智性』,輸掉了公投,賠上了政治生涯。
B. 短視逐利,忽視長遠
新手父母在查閱育兒經的時候,幾乎都聽過一個對寶寶未來發展有利的東西——延遲滿足。
所謂延遲滿足,是指甘願為更有價值、更長遠的目標,而放棄眼前的即時滿足。
這是一種自我控制的能力,涉及到延遲享受,並在等待的過程中展現自制力。 這種能力對於個體完成任務、協調人際關係和適應社會都至關重要。
而民意,恰恰反映出人類對延遲滿足的忍耐力有多薄弱。
這正是三峽工程受到廣泛支持的原因之一。
短期內,三峽水壩在防洪與發電效益極具吸引力,這個好處讓人『自願性』的忽略,水壩帶來的長期生態系統崩壞、水土流失、地質災害與140萬移民的社會成本。
同樣的,近期美國國會剛剛通過的“Mega Spending Bill”,是一個高達數兆美元的支出案,涵蓋國防、基礎設施、社福與補貼政策。
儘管學者與財政部門強烈警告其對赤字與通膨的長期威脅,但民調顯示:多數選民支持「花錢救經濟」,而不關心國債問題。
結果顯而易見:政治人物為了不失選票而妥協,財政紀律在選票面前潰散。這是一種以未來代價換取當下滿足的制度性集體失控。
C. 複雜問題,二元簡化
人類天生對複雜性感到排斥。
你不相信?那麼想像你在餐廳時,服務生給你遞上來厚厚的一疊菜單時,你的煩躁和無助就是最好的答案。
同理,面對政策選項,民意往往只願接受簡單對立式的敘事,例如「挺還是反」、「是進步還是保守」、「有利人民還是有利財團」。
這些過度簡化,正是人往往不能看清事情的全貌的主因——我們的基因趨向讓我們往更安全的方向走,即便那意味著我們需要放棄思考。
於是,我們下意識的選擇了簡單的道路,選擇了多人走的道路,毫無保留的接受二元簡化的選項——就好像在看完餐廳厚厚的菜單後,你最終選擇很可能是餐廳最早提供你的A餐B餐配套。
三峽水壩的爭議,被簡化為「愛國者支持建設/反對者阻礙國家進步」,讓涉及技術、生態、地理、社會學的複雜議題被粗暴歸類——對普通人而言,這些議題知識內容太複雜了,而人們也沒有耐心去一個個認真查閱。
在美國,類似邏輯支配著如墮胎、槍枝、能源等議題的公共辯論空間。政策設計的細節與條件反而無人問津,留下的只有簡化口號與敵我意識。
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莫過於美國防疫政策的民意撕裂。
2020–2022年間,美國在是否封城、是否強制戴口罩、是否打疫苗等議題上出現激烈對立。明明是公共衛生的高度複雜問題,卻被民意極端簡化為:「自由 vs. 控制」、「民主黨搞陰謀 vs. 科學專業理性」、「口罩等於奴役」或「不戴口罩等於殺人」。
這麼一來,原本屬於流行病學的複雜討論,被民意輿論轉化為忠誠度測試——你戴不戴口罩,成了你是哪一黨的政治表態。
D. 多數暴政,少數犧牲
托克維爾早已警告「多數暴政」的風險。當民意凌駕於個體權益與倫理原則之上時,極易演變為對少數群體的壓迫。
三峽工程中的140萬移民,大多為農村弱勢社群。
他們的生活、文化、土地與歷史記憶被輕易抹除,只為成全「全國人民的利益」。這種犧牲被包裝為「必要代價」,但從未真正獲得社會討論與尊重。
然而,當我們試圖冷靜地問一句:「這些代價是否值得?」往往不需等國家動手,群體就已率先發動攻擊,指責你「不識時務」、「挑撥對立」。如此一來,真正的反思空間就被情緒輾壓成了道德勒索的戰場。
美國亦然。
在疫情補貼分配、基建資源分布、稅收改革中,政策傾向於「滿足最多人的需求」,而非保障最弱勢群體的永續生存。
比方說2000年代初期,許多州進行「公投決定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結果多數都表決反對。也就是說,多數人投票決定少數人是否擁有基本婚姻權利。
這是「多數決」壓迫少數權益的經典情境。同性戀者作為人口中的少數,被迫接受不屬於他們自己建構的「公共道德」裁決。
這些例子都一再證明,當民意的被誤當成正義,就會輕易的淪為強者的代言。
制度差異,困不住人性的相似
三峽與美國的這些案例,在政治體制上迥然不同:前者是集權威權決策,後者是民主制度下的選票協商。但它們都揭示同一個核心:民意作為決策基礎,並未逃脫人性的局限,而是在人性中被放大與扭曲。
中國的政治菁英藉由「民族偉業」操作情緒,掩蓋反對聲音;民族國家如美國則在「人民想要更多福利」的壓力下失守財政紀律。
前者是情緒壓制,後者是情緒投降。制度的差異掩不住人性本質的相似——都是情緒導向的短期自利行為。
但是請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民意絕對值得被傾聽,卻不該被奉為決策的絕對依據。
民意揭示了社會的情緒與焦慮,卻未必具備處理複雜性與倫理權衡的能力。真正的公共治理,不是迎合民意,而是在尊重它的同時,建立能抵禦其脆弱性的制度與價值觀。
這不是對民主的否定,而是對人性深處的誠實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