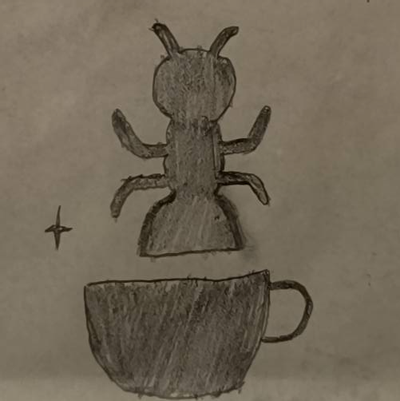-談七等生「我愛黑眼珠」與太宰治「人間失格」
以個人對抗集體主義
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發表於1967年,蔣中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對抗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於是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這種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文化動員,不僅僅是一種高度政治力的展現,對於民間社會的壓抑,同時企圖灌輸一套僵化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以便遂行有效社會控制。
這套官方意識形態下展現的意識形態控制,深入學校,甚至包括家庭,譬如1971年實施的家庭計畫,控制生育,亦即國家機器直接控制身體,同時控制了慾望以及慾望的表現形式。
在那樣的時空脈絡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做為一個對抗集體主義文化思潮與意識形態的文本,所具備的個人主義敘事風格,其背後隱含的權力運作,個人主義是一種對抗集體主義的形式,個人主義彰顯了敘事者的主體性,敘事者企圖透過自我理性的運作脫離國家機器的掌控,用一種敗壞社會集體價值的方式來訴諸解構的力量,同時將個人從這種集體的束縛之中解放出來。
七等生的敘事策略凸顯了個人的主體性,並訴諸個人理性思考的模式來解構社會集體價值,並企圖揭露此種集體價值的非理性,具有榮格集體潛意識控制的國家意識形態,透過此進路,個人將獲得自由,儘管此種自由帶有虛無主義的色彩,因為解構集體價值後,個人獲得獨立思考自我價值的空間,但卻無力建構一種集體價值,以致於此種個人價值因為無法得到集體認同而具有虛無的傾向。
此一個人主體性的辯證發展過程,恰恰好就是現代性的困境,前現代的集體主義提供了個人主義掙脫束縛的論述場域,個人主義得以用自我的理性對抗集體的意識形態,然而具備理性的個人也在解放後面臨缺乏社會認同基礎的虛無性格。
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也具有同樣的特徵。
歷經昭和法西斯的日本社會,籠罩在集體主義價值的氛圍中,國家集體意識形態的力量無遠弗屆的深入社會中,讓人無所遁形。
太宰治的「人間失格」做為一種個人主義的敘事,不崇尚與歌頌任何集體價值,反而刻意地貶抑生命存在的價值,以自我的否定來否定整個時代精神。
日本的軍國主義在昭和時期發展到達顛峰,軍國主義精神已經貫徹整個日本社會,其最具體的展現為發動二次世界大戰及東亞侵略戰爭。
在此集體價值下的太宰治並沒有個人屈從於時代精神與國家意識形態之下,而是透過個人的虛無傾向來反諷軍國主義的虛無,透過個人價值的迷失來凸顯國家集體價值的迷失。
七等生與太宰治透過個人主義敘事來對抗集體主義價值的結果,是慾望主體的重設,七等生以敘事者與黑眼珠外遇來顛覆集體價值所設定的倫理關係,以及這種倫理關係下所設定的慾望主體的樣貌。
太宰治則以捨棄生命來取代為國犧牲,以否定生命來否定個人生命服務於集體價值,譬如自殺特攻隊,以便重設慾望主體的展現方式。
但是這兩種個人主義敘事所展現的現代性,最終都不免出現價值失落的樣貌,因為個人生命從集體價值解脫後,對抗集體價值的慾望主體並無法提出一種具有社群性質集體認同的慾望形式,而是有賴每一個慾望主體的解放,重新建構或者重設自己的慾望主體,然後才能在相互肯認中使得慾望主體之間獲得一種相互認可、肯認的過程。
換言之,現代性的超越必然要經過後現代理論的批判,最終才能從現代性的困境中出發,從而超越了現代性。
個人主義敘事風格的論述分析
論述分析原本是語言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後來被廣泛運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Michel Foucault可謂是其中的翹楚,他特別著重語言使用過程中的權力現象,並試圖剖析此權力形塑了何種社會關係。論述分析透過Michel Foucault的研究開展了更開闊的空間,但其對權力整體論式的觀點在方法論上不免流於獨斷,而其影響卻仍然深遠。(Fairclough,1992:p.37-61)
論述分析延續Michel Foucault的思想脈絡,仍試圖對於論述所隱含的權力運用來加以分析,透過論述分析來解釋其如何建構(construct)或重構(re-construct)社會關係。但對於論述本身做為一個論題(statement),既不純粹把它看作是一個科學上客觀存在的或有待驗證的命題(proposition),但也避免如Michel Foucault那樣把論述直接等同於權力,而推論出社會關係已被形塑,此種在邏輯上已建立因果關係的結論。
論述是種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Norman Fairclough將論述視為是一種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Fairclough,2001:p.14-35),本研究在分析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或者太宰治的「人間失格」時將其文本視為是一種政治行動,此種政治行動面對當時的集體主義價值體系,可以被視為具有一種解構的企圖存在,此種解構的政治行動企圖在論述中去重塑社會關係。
在論述分析的方法中,理念被轉變成為論述,其行動的目的最終在於重構社會關係的價值取向與倫理意涵。因而,論述不但具有理念,而且是一種透過理念的敘述企圖取得權力的政治行動,在此政治行動中理念被轉譯成為論述,並且在文本所處的脈絡中產生社會影響力,進而對於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產生一定的破壞力,來呈現與象徵解構行動的開展,此種權力的開展透過閱讀社群的詮釋,最終超越了作者論的範疇,甚至可以蔚為一種政治行動。
要談現代性,首先得定義何謂現代性,現代性的問題從上世紀討論迄今,雖然很難找到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卻有一個很清楚的哲學思想及方向,那就是主體性哲學及其批判,關於現代性的問題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德國唯心論傳統的主體性哲學而展開。
黑格爾可以說是主體性哲學的集大成者,換言之也就是西方哲學關於現代性討論的集大成者,主要有三點構成了黑格爾的主體性哲學,第一、人的主體性因何而存在?因為有理性,康德在何謂啟蒙一文中明確地揭櫫了啟蒙的意義在於開啟人類的理性之光,康德的三大批判為理性找到了可能性條件,奠立了主體性哲學知識論的基礎。
第二、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精神的發展,也就是人類理性的開展。第三、人類歷史既然是理性不斷地開展的歷史,那麼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在辯證中發展的歷史,亦即辯證理性的發展導致了人類歷史的進步。
這個由黑格爾所奠立的現代性遭到三個著名思想家的顛覆與否定,第一個是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他發現了潛意識對於人類的行為所起的作用,證實人類行為未必只有意識,潛意識的作用可能是更為基本的。(Habermas,1972:p.214-p.245)
第二個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在精神,而在於物質,或者應該說是由人類改造過的物質,因此他否定了黑格爾意識決定存在的命題,而將其修正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了其社會意識。(Habermas,1972:p.25-p.63)
第三個則是尼采,尼采分析指出黑格爾現代性的繆誤在於相信一個進步的時間觀,歷史發展在達爾文主義的烘托下,變成不斷進步的規律,尼采以希臘神話來比喻人類社會的發展,只是一種永劫回歸,也就是歷史循環論。(Habermas,1972:p.274-p.300)
在這三個挑戰下,現代性的矛盾蔚為上個世紀的文藝思潮,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從尋求主體性的現代主義一直到否定主體性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交織成為一場繽紛的變奏曲,讓文藝理論與創作不斷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進行一種雙軌的詮釋循環,現代主義既沒有完全被否定,但後現代主義提出的質疑卻仍然有效。
這裡面有三種路徑是值得關注與討論的,第一個是哈伯瑪斯的路徑,他相信溝通理性仍然可以解決主體性的困境,也就是透過主體溝通理性之間的對話可以達成主體之間的互相理解,進而克服主體性本身的缺陷。
第二個是詮釋學的途徑,以Charles Taylor為例,他主張透過人的自我詮釋來解決現代性的困境。
第三個便是傅柯的論述分析途徑,透過不斷解構與重構社會的權力關係來解決現代性的困境。
我將著重於第三個途徑來理解七等生與太宰治文學作品中的現代性,做為對抗集體主義的一種文本,現代性要彰顯的主體性,在七等生的論述脈絡裡面透過自我的理性以覺察個人的道德自律與應該遵循的倫理規範,而集體主義的倫理框架雖然沒有具體地被強調或者彰顯,但在文本的脈絡中卻可以處處感覺到其存在,做為一個集體主義下主流的價值體系,它幾乎是無所不在,如同傅柯在描述一個如同監獄一般的全視景的社會控制體系一樣,個人的行為在這樣的倫理體系中無所遁形,處處受到檢視,以致於個人理性必須時時刻刻保持覺醒,以便與之對抗。
當代社會學理論大師紀登斯在討論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時,讓我們理解到現代性論題的出現伴隨著自我認同危機,自我認同其實是現代性的產物,當主體性越加彰顯時,個人的自我認識便越加深刻且廣泛,從而產生更多的疑惑需要解決。(紀登斯,1991:p.71-p.77)
透過詮釋學大師高達美的詮釋循環概念的釐清,我們可以發現自我認同具有兩個面向,這兩個面向的交互辯證構成了詮釋的循環,其中一個是面向未來的時間向度,另外一個是面向歷史的時間向度,個體透過歷史的自我認識以便決定未來自我行動的方針。
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Charles Taylor則以人是自我詮釋的動物此一哲學人類學的命題來開展其論述。
放置到本論文的架構中,可以如此綜合以上理論的論述,而證成關於人在歷史中的理解如何形成自我認同,此一課題乃是現代性的核心論題。
在東方社會的威權體制轉型中,個體面臨的是傳統的權威主義的瓦解,以及個人主體性的建立,這往往成為東方社會面臨殖民與後殖民處境時一個共同的脈絡,個人的主體性陷溺在一個必須透過前現代的國族認同以便對抗壓迫的殖民主義,一旦殖民主義瓦解後,國族認同卻又成為個人主體性的枷鎖,蔚為現代性的另一個困境。
個人主義在威權統治的獨白
七等生(1939年7月23日-2020年10月24日)的童年面臨一個歷史上政權的交替與置換的轉折期,他的青年時期又面臨新政權企圖用新文化運動來對抗國共內戰中的勝利者。
由新政權提出的新文化運動形塑新的國族認同,一方面企圖由國家機器發動一場由上而下的集體價值革命,充分地把過去的殖民文化革除,代之以新的殖民文化。
一個以中華文化的道統為根基的價值革命,內在卻是承襲自儒家思想做為官方統治意識形態的倫理規範,一個外在於這個社會卻有企圖覆蓋在社會上的集體價值,由此誕生,並變成七等生企圖對抗,以便保有個人主體性的國家文本。
因此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是敗德的,敗的是國家高舉的道德大纛,敗的是國家機器強加於人民的意識形態,敗的是國家企圖建構的集體價值,在形態上,這個新文化運動與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並無不同,都是國家建構的一部分,都是歷史發展的上層建築,也都是一種殖民論述。
從企圖超越殖民論述來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是一種後殖民論述。
對抗集體價值,以便保護及建立個體的自主性,這是一種現代性的表現方式,是現代主義的工程。
七等生透過李龍第在一場洪水中的道德實踐展演了一場關於道德自主性的論述,非常典型康德式的論述,道德是不證自明的,他在面臨此岸俗世的救贖命題時,刻不容緩的,必須符應內心的道德召喚而援救這個已經在他懷中的妓女,至於她的妻子晴子則在這場洪水裡面,處於彼岸他無法援救的對象,他非常理性的做出道德判斷來援救當下的這位妓女。
當晴子因為這樣的舉動處於不能理解的狀態時,七等生所塑造的男主李龍第堅定地以自己的道德信念決定援救這位妓女到底,以至於妻子晴子竟因而發狂,企圖到達此岸但慘遭落水而不知去向,這其中的道德兩難困境,是作者七等生一開始的敘事結構就設定的,直到末了。
李龍第的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體現了其主體性,尤其是相對於七等生企圖透過文本的論述對抗的國家機器集體價值而言,他充分尊重了內在不證自明的道德判斷,基於理性的道德判斷。
當李龍第完成了這場在緊急危難中的道德實踐後,他回到了家,並企圖向晴子的母親訴說其道德實踐的正當性,其主體性宣告完成,他未曾屈從於任何權威而保有正當性。
李龍第的道德正當性建立在自己不證自明的理性上,這個理性主體同時也是道德主體透過自我肯認獲得主體性與正當性。但是,他卻充分地將晴子與妓女客體化了,李龍第既無能也無法對於這樣的道德處境與其妻子晴子進行對話,也沒有企圖對妓女說明事實,其存在處境的荒繆性似乎隱隱約約在諷刺當時當道的道德教條主義,但同時他彰顯的也是個體的主體性,而無法與晴子或妓女透過對話來進行意義的交換及詮釋,使對方來重新理解這樣看似荒繆的道德處境。
這樣的主體性建構是以犧牲其他主體,如晴子或妓女的話語權,來成就其自身,換言之,他是個人主義式的主體建構,同時帶有性別歧異色彩的主體建構。
太宰治置身於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換言之,置身於日本建立現代性的過程中,明治維新的成功,大正民主的稍縱即逝,昭和的法西斯象徵威權的復辟,戰後,象徵大東亞共榮圈及大日本帝國榮光的集體價值崩解了,天皇宣告人間宣言,集體價值的崩解往往也等同於個人價值的崩解,「生まれて、すみません」,帝國的失敗同時也意謂著個人的失敗,個人離開國家後,飄盪無所底乎。
法蘭克福學派的心理學家佛洛姆曾經用逃避自由來形容二戰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集體價值的崩解往往需要一個新的價值來代替,日本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在大正民主時期提出的天皇機關說在二戰結束後,才由聯軍統帥司令部的元帥麥克阿瑟來加以實現,一部由統帥司令部制定的憲法,成為日本的憲法架構至今。
日本戰後的現代性,無疑地,是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統治當時日本的就是戰勝國的聯軍統帥司令部。日本的現代化是由新的帝國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強加於日本社會。
生活於這樣時代的太宰治,面臨集體價值的喪失與崩解,其個人生命面臨同樣的命運,蔚為當時日本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而存在著,其主體性的建構脫胎於過去的主體性完全被否定的前提,儘管過去的主體性帶著集體主義的性質,始終沒有脫離帝王專制的政治體制,但是這個毀棄過去主體性的過程是痛苦的,是戰勝帝國透過手術刀式的方式來加以切割的,以致於對日本多數國民而言,都像是一次換腦或換心的外科手術一樣,甚至由於排斥作用太過劇烈,而難以繼續生存下去。
太宰治面臨戰後日本社會關於帝國美夢瓦解所帶來的集體價值崩解(吳叡人,2019),過去作為國民信仰中心的天皇被迫發表人間宣言,其個人生命的否定是集體潛意識的表徵。主體的自我否定是揚棄過去遭到君主專制傳統束縛的主體性,進而開展出個人理性自覺的主體性,還是重新掉入另一個權威象徵所建構的主體虛擬實境之中,太宰治並沒有給出最後的答案,人間失格後主體性留下了一個空白,可以自由填寫答案。主體可以昂揚,但也有可能如同法蘭克福學派心理學家佛洛姆所言的逃避自由,個人重新去尋求一個集體主義所安排與建構的價值與秩序。
近代的超克對東亞國家而言是宿命,是日本的宿命,也是中國的宿命,最後台灣也被捲入這場對抗來自歐美殖民主義的浪潮中。
比較七等生與太宰治的文本「我愛黑眼珠」與「人間失格」,企圖探討殖民社會中主體性在對抗集體主義,尋求一種現代性過程中,如何進行論述及建構文本,以彰顯其自覺,主體性的建構在重塑權力關係時,隱身在理性主體後慾望主體如何成為預設,此一慾望主體在七等生的論述脈絡而言,仍然未能顛覆日本父權社會裡的性別權力關係,從而彰顯的只是特定性別的主體性,而非互相肯認。
在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中,生命的自我否定為主體性的建立開展無限可能,但也留下一個集體主義與權威人格可能復辟的空間,近代的超克始終是日本恢復為正常國家的文化硬核,遺留父權體制支配關係的日本社會如何完成近代的超克而不會淪為威權的懷舊與復辟仍是一個嚴肅的課題,對於台灣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參考書目
七等生,(2020),我愛黑眼珠,台北:印刻。
太宰治,(2017),人間失格,台北:前景。
太宰治,(2019),人間失格日文版,香港:中和出版。
吳叡人,(2019),文學的自殺與日本近現代精神史:太宰治-體現戰後的廢墟與病徵,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676。
陳芳明,(2021),評論》清癯靈魂裂變的惡之華:陳芳明談七等生,openbook,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4475
廖淑芳,(2017),《天使與橋者: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台北: 遠景, 2017.2 (科技部計畫成果推廣叢書)。
廖淑芳,(1990),《七等生文體研究》,台南:成功大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未刊行)。
廖淑芳,(1994 ),〈七等生短篇小說〈大榕樹〉的啟悟主題〉,《光武學報》,第十九期,台北: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舊:北台科技學院), 1994。
廖淑芳,(1992), 〈七等生作品中的個人觀、群體觀及其形成〉,《文學台灣》第三期,高雄: 文學台灣雜誌社,1992.6。
廖淑芳,(1990 ),〈諷刺浪漫或感傷寫實──七等生短篇小說〈結婚〉探討〉 ,《新地文學》,台北: 新地出版社,第五期,1990.12。
廖淑芳,(1993), 〈七等生作品中的個人觀、群體觀及其形成〉,張恆豪編,《認識七等生》, 苗栗: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 月,p.5。
廖淑芳,(2015),〈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以天使與橋者的形象為核心〉,台北: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主辦,「七等生作品研討會」。
廖淑芳,(2012),〈愛、犧牲與沉默──七等生〈我愛黑眼珠〉與陳映真〈山路〉中人物倫理行動比較閱讀〉,中壢: 東華大學﹑中原大學聯合主辦,「兩岸華文文學會議」, 2012.4.28~29。
廖淑芳,(2009 ),〈文學敘事的在地演繹──由七等生小說〈散步去黑橋〉的「在地性」談起〉,苗栗: 聯合大學台灣語文傳播系主辦,教育部台灣文史藝術計畫辦公室協辦,「文化自主與台灣文史再現」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9.25。
廖淑芳,(2009) ,〈人媒到鬼媒──由七等生小說〈結婚〉的媒婆角色論婚姻的傳統與現代〉,台北: 創意出版社主辦、國家文藝基金會協辦,「媒情研討會」,2009.2.21。
廖淑芳,(2010),〈在一個沒人注意或有意疏忽的角落,固執地種植我的花朵──七等生〉,《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得獎專刊》,台北:國家藝術基金會出版,2010.10。
廖淑芳,(1998 ),〈自我鞭撻的文學偏執者──七等生論〉,自由時報第41版,七等生專輯,1998.10.8 。
蕭義玲,(2016),〈亞茲別的宣言與選擇──〈我愛黑眼珠〉的詮釋及其在七等生寫作歷程的位置〉,《文與哲》29,p.317-354
蕭義玲,(2016),〈愛與戰鬥的雙向命題—七等生《耶穌的藝術》的理想藝術之追求〉,《東華漢學》23,p.207-248
蕭義玲,(2009),〈獻給永恆女神的禱詞─從七等生《譚郎的書信論藝術實踐與自我完成》〉,《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五期,p.85-123
蕭義玲,(2009),〈自我追尋與他人認同─從「自律作家」論七等生的寫作風格及評價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三十七期,p.105-162
蕭義玲,(2008),〈走在一條建造家屋之路─論七等生《重回沙河》中的時間光影與生命家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第十二期,p.201-240。
蕭義玲,(2008),〈愛、疏離與暴力─論七等生<精神病患>中的疾病與醫療之路〉,《文與哲》,第十三期,p.299-339。
蕭義玲,(2008),〈觀看與身分認同──七等生小說的「局外人」形象塑造及其意義〉,《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二期,p.121-160。
蕭義玲,(2007),〈面向存在之思──從七等生小說論愛慾、自然與個體化歷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第十期,p.151-190。
蕭義玲,(2007),〈內在甦醒的地方,才是吹奏開始的地方--從七等生《沙河悲歌》論生命藝術性的追求〉,《東華漢學》,第5期,p.173-212。
蕭義玲,(2010),《七等生及其作品詮釋:藝術•家園•自我認同》,台北:里仁書局出版。
崔末順,(2006),韓國的現代性經驗與全球化時代的課題,當代, No.226,p.90-107。
安東尼、紀登斯,趙旭東、方文譯,黃瑞祺審定,(1991),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
Fairclough, Norman.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orman.2001. Language and Power (2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
J O H N W. M . K RU M M E L. 2021. The Symposium on Overcoming Modernity and Discourse in Wartime Japan,HISTORICKÁ SOCIOLOGIE,2/2021
Jurgen Habermas.1990.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he MIT Press
Jurgen Habermas.1972.Knowledge & Human Interests,Beacon Press
Timothy Unverzagt Goddard .2013.Teito Tokyo: Empire, Modernity, and the Metropolitan Imagin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Richard J. Bernstein .1985.Habermas and Modernity ,Mit Pr; 1st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