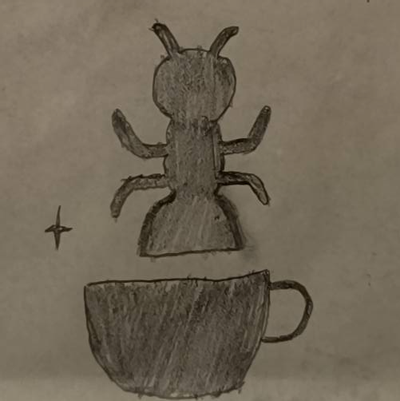在科幻電影中,「時間終結」(The End of Times)或「末日」啟示(Apocalypse)不僅僅是「災難」場景的展現。更是一種透過複雜的「時間」結構,來探討人類「生存焦慮」、歷史記憶與存在意義的手段。
一、 科幻電影中「末日」的四大奠基作品有四部電影被認為足以建立科幻電影的分支,或成為「時間終結」主題的參考標竿:
1. 《大都會》(Metropolis, 1927):
導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在片中構想了一種高度「層級化」的組織結構,並將其災難性的結局,歸咎於支撐該組織的巨大「機械裝置」。這部作品被視為社會預測的先驅,其影響延伸至後來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

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 1927)
2. 《堤》(La Jetée, 1962):
法國導演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利用靜止照片攝影蒙太奇的形式,探討了「原子末日」。該影片通過對時間的玩味,展示了科學如何介入日常生活。並成為導演特里·吉列姆的電影《未來總動員(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5)的靈感來源。

《堤》(La Jetée, 1962)
3. 《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作品超越了傳統的太空歌劇。它描述的不僅是穿越時空的長途跋涉,更像荷馬史詩般,提出了一個回歸生命誕生前「起點」的循環過程。
4. 《超世紀諜殺案(綠色食品)》(Soylent Green, 1973):
理查德·弗萊徹(Richard Fleischer)展現了當人類僅面對自身「慾望」求生時,人性如何縮減至純粹的暴力。這部影片並非純粹的生態預言,其靈感其實源自死亡集中營,探討人類處於極度脆弱狀態下的生存境遇。

電影《超世紀諜殺案(綠色食品)》(Soylent Green, 1973),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演。
二、 「作者論」視角:末日作為「個人恐懼」的投射
探索科幻電影中的時間終結,本質上是一種「作者」的行為。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與高達(Jean-Luc Godard)等導演,都將「末日」視為對當下不安與個人死亡焦慮的夢境投射:
法國導演高達在《二十一世紀的起源(De l'origine du XXIe siècle)》中,從個人回顧的角度尋找「新世紀」的意義。
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在日記中,表達了對未來災難和末日瘟疫的恐懼。他的電影《犧牲》(The Sacrifice, 1986)探討了在世界性災難背景下,個人如何逃避死亡。

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犧牲》(The Sacrifice, 1986)。
科幻電影利用對人類整體終結的恐懼,試圖通過「奇觀化」(spectacularization)的手段來驅魔,將個人死亡的焦慮,轉化為大銀幕上的「壯觀」視覺體驗。
三、 末日「時間」的四種敘事結構
桑迪·托雷斯(Sandy Torres)的研究,將科幻電影中的「時間」構造分為四種情況:
1. 末日之前(Before the Apocalypse):
劇情沿著「線性」時間發展直至末日爆發,「終結」通常與影片結束重合。這類作品(如《末日預言》Knowing, 2009)充滿了緊張感與末日預兆,空間的壓縮往往成為「時間緊迫」的隱喻。

電影《末日預言》(Knowing, 2009)尼可拉斯·凱吉主演。
2. 末日的後果(Suites of the Apocalypse):
此類電影關注災難後的生存樣態,「災難」通常發生在影片開頭。表現手法可分為兩極:一是誇張手法,如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宏大災難規模;二是微言大義,如電影《末路浩劫》(The Road, 2009)中僅透過細微的光線變化,來暗示災難的爆發,和災難後的死寂。

電影《末路浩劫》(The Road, 2009)
3. 末日之後(Beyond the Apocalypse):
故事設定在末日之後「很久」的時空,主角通常經歷了時空跳躍。例如1968年舊版的電影《人猿星球(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主角在未來發現了「文明毀滅」的痕跡,這種結構帶來的是一種「事後揭示」的震撼。

1968年舊版的《人猿星球(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演。故事講述了一支太空人小隊,經過兩千年的冬眠後,在遙遠的未來,迫降在一個陌生的星球上。發現了一個猿類社會,這些猿類已經進化成,擁有類似人類的智慧和語言能力的生物。猿類成為了這個星球上的統治物種,而人類則變成了穿著獸皮、無法言語的原始人。最終,他們發現了自由女神像的殘骸,這才意識到這顆原本被認為是外星的星球,其實是核戰之後的地球。主角絕望地跪倒在地,痛恨人類毀滅了世界。
在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人類消失」兩千年後,高科技機器人試圖重建過往的片段,展現了一種與死亡和孤獨對抗的親密經驗。
4. 接近末日(Approaching the Apocalypse):
末日尚未發生,但「徵兆」已現,如「戰爭」頻發或人類面臨絕育(如《人類之子》)。這種生存的脆弱性,讓敘事時間變得極其緊湊。這類結構強調緊張感與預兆,時間被「壓縮」了,敘事節奏如同驚悚片般急促。在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 2006)中,末日表現為人類絕育導致的物種滅絕威脅,生存的脆弱性讓每一秒都顯得極其珍貴。

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 2006)
四、 「非線性」與循環的時間實驗
除了線性敘事,科幻電影也利用更複雜的「時間」構造,來深化末日主題:
「循環」與回歸:
在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時間結構超越了單純的探險,提出了一個回歸「起點」的循環過程,暗示末日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誕生」。
架空歷史與時間組合(Uchronia):
以電影《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系列為代表,影片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進行複雜的組合遊戲。「未來機器」試圖改變「過去」以重塑未來,這種結構讓「人類終結」的必然性與「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不斷拉扯。

電影《魔鬼終結者2》(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 1991年),詹姆斯·卡麥隆導演。
記憶與「重建」:
在《堤》(La Jetée)及其重拍版電影《未來總動員(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5)中,末日後的倖存者試圖重建「末日之前」的時間。這種結構探討了「影像」如何作為時間的載體,即使在死亡與虛無之上,也能架起通往「記憶」的橋樑。
《未來總動員》利用「過時」的裝飾、服裝與機器,創造出一個與預期不同的未來感。末日後的世界,看起來像是一堆現狀與近期過去的「廢料」堆積而成的舊貨。這種刻意營造的「庸俗」(kitsch)風格,讓「未來」看起來像是在「過去」之中,產生了一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

電影《未來總動員(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5)。
五、 末日樣貌背後的深層意涵
這些時間結構的設計,是為了探討更核心的議題:
個人與集體「死亡」的對接:
導演常將個人的死亡焦慮,投影到「整個人類」的末日中。例如在《綠色食品》(Soylent Green,又譯《超世紀諜殺案》)中,一位老人的臨終時刻,與整個人類文明的墮落與終結,產生了深刻的共鳴。
末日與「重生」的共生:
在許多末日敘事中,「孩子」(如《魔鬼終結者》的約翰·康納(John Connor)或《人類之子》中的嬰兒)的出現,是關鍵的時間轉折點。這象徵著在毀滅性的時間終結中,依然保留著「重新」開始的希望。
對不可捉摸之歷史的捕捉:
科幻電影中的末日奇觀,往往是為了反映當下社會難以言說的「悲劇」,如種族滅絕(genocides)或「大規模死亡」的恐懼。透過虛構的時間結構,電影將這些歷史中難以捉摸的創傷,變成了可被觀看與理解的悲劇敘事。
六、 歷史現實的電影反映
科幻電影多為「美國」製造,它們在講述時間終結時,必然會調用聖經背景、社會信念或歷史語境:
冷戰與核恐懼:
早期的末日電影(如1951年版《當地球停止轉動,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直接影射「冷戰」威脅。

科幻電影、黑色電影1951年版《當地球停止轉動,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現代重拍版(2008年版《當地球停止轉動》),則將威脅轉向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的破壞。
戰爭與「恐怖主義」:
在電影《世界末日》(Armageddon, 1998)中,隕石襲擊紐約的場景,引發了關於「薩達姆·海珊」轟炸的台詞(Oh, we at war! Saddam Hussein is bombing us!),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恐懼。
結語
科幻電影中的「末日」不僅僅是視覺上的「奇觀」,它更是一場關於時間本質、影像真實性以及人類存在焦慮的深度對話。從奠基經典的「社會預警」,到作者導演對「死亡」的私人探索,科幻電影始終在「終結」的陰影中尋找著「重生」的可能。透過對「時間結構」的精密拆解,與對社會現實的歪曲映射,這些影片讓我們在虛幻的「末日奇觀」中,重新審視我們作為人類個體與群體的「有限性」。
科幻電影並非只是在預測未來,而是透過「時間」的重組與玩味,將末日啟示,轉化為一種對當下現實、個人限度以及人類群體命運的深度探討。
參考書目: Sebbah, Alain. “La ‘Fin des temps’ dans le film de SF.” Nihilismes ?, édité par Éric Benoit et Dominique Rabaté. Pessa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