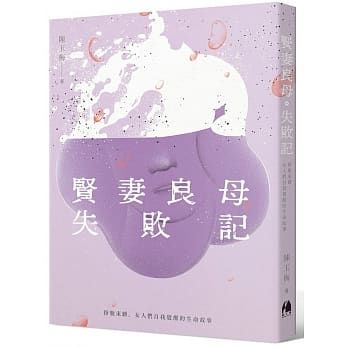作者取的書名《豪爽女人》,同時挪用了豪爽這個詞義,也應用了詞音來對應好爽,在1994年出版的本書在當時可說是非常的前衛,且文字也相當的不修飾而予十分裸露的表達,更可感受到那股想衝破父權桎梏的企圖。
父權體制(patriarchy)的現象
本書著作的時期距今25年將近大約一個世代的距離,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其實恰巧就是我們上一代在成人時期,確實隨著時間的經過有些事物變更了,例如1930年的民法第1059條第1項:「子女從父姓。」,而現在則規定為:「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及1051條:「兩願離婚後,關於子女之監護,由夫任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變為1055條第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又或是刑法對於強制性交罪(強姦罪)曾經對於不能抗拒是必須要有抵抗,到今日司法實務認為違反意願不以積極抗拒為要件的變革。更甚者,在女性主義的運動下,性關係的發生更需要積極同意(only yes means yes)的存在才可確保雙方(尤其是女性)的性自主。
在以前的年代中,傳統女人就像馬一樣,拼命的做、被予取予求,但(男)人在吃飯食時,自己在吃草,甚至跑到暴斃也都被如敝屣般丟棄。而女人的方面,也深陷這個體制中,把男人當作飯票,對於對象的尋覓並不是依靠情感,而是現實的功利計算,跟著誰才能享受到好的生活,而並不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把自己定位在依附於主體的存在。
父權的現象至今仍存,固然憲法規定有平等原則,然而現實跟規範從來在其間就有一條鴻溝(gap),現實中還是可以看到像是在繼承事實的發生中女子拋棄繼承權、將家庭中的財產一律歸於丈夫名下,或是在我們的語言中對於男女的結合並不使用平等且中性的「結婚」一詞,而經常會出現「嫁」、「娶」這樣的對立語詞。這種種都反應出在性別議題上有主客之分,而主體為男,客體為女,這就是父權社會的現實。
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
這種父權社會中的運作模式作者稱作「賺賠邏輯」,「簡化地說就是:在和性相關的事上,男人不管怎樣都是賺,而女人總是賠。我想指出的是,這個建立在一夫一妻交易制度上的身體情慾賺賠邏輯,使得女性的身體和情慾(以及人生其他方面)遭受不利的差別待遇和差別發展,因此這個賺賠邏輯是女人在追求情慾、身體、以及其他方面解放的過程中要打擊的頭號敵人。」
「這個基礎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交易本質。在我們這個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中,女人必須歸屬某個男人為妻,以身體以及身體可以執行的各種功能(如性交、生育、家務勞動等)來交換一個長期的、穩固的社會位置(即名分)。這種交易是一夫一妻(甚至多妻)婚姻制度的真正意義,而我們目前熟知的愛情只是這個交易的一部份活動,甚至有可能只是美化劑而以。」
「如果這個制度要繼續運作,如果女人要維持她的交換價值,她就不能白給,不能只因為自己喜歡就提供身體及服務功能給男人。因此,社會常規教導女人,他必須等男人提供婚約(代表穩定關係及名分的正式文件)、愛情(有可能引致婚約的預備動作)、或者至少金錢或物質享受等等條件之後再進行交易(『給他』)才是道德的。社會常規也教導男人,他必須付上某種代價(『承諾』、『負責』)才能得到女人的身體以及這個身體的有用功能。」在這種主客體的建構中,先天地因為性別之故就底定了社會中的不變位置:永遠的贏家與永遠的輸家。無論是視線所及或是肢體接觸甚至是性行為,雖然在生理層面上這些事件都是中性的,但是在性別關係的視角中都在這個邏輯之下成為了只要是女體被看、被碰、與其性交都是虧,而只要看的、碰的、與其性交者,簡言之,只要是相對於女體這樣的客體,就永遠是賺。理由就在於這些行動都是在賺賠邏輯中的背景裡來進行觀看的,進而在原初的邏輯設計下就已底定的結論自不會因行動的性質而有別,而是依照身分(性別)來決定。
只要是身為女人,在這樣的性別結構中永遠是第二性,無論個性是內斂保守還是外放豪爽都承受同樣的壓抑,對於這種結構的突破,差別將是在於面對的態度:遵循規則?抑或是跳脫規則?作者認為「不斷增加的豪爽女人才是打敗賺賠邏輯的主力。唯有他們才至少在主觀上已放下少賠或不賠的保守心態,唯有他們才能痛快的、自主的、不帶交換條件的說『我要』,因此他們說『不』的時候絕不是為了終極的交換進行討價還價,而是真正的自主的『不要』。豪爽女人在自我意識上是非常強悍的,在精神上是非常自由的。」而在這種類型女人—豪爽女人對於父權體制的衝撞中,也會產生同樣身為女人的「好女人」的憎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也比較了解為什麼所謂的『好女人』(也就是堅持少賠的女人)會憎恨所謂的豪爽女人(也就是不甩交換的女人)。因為,後者在肯定並執行自主的解放意願時壞了交換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她們所說的『我要』為好女人寄望的終極交換或者已完成的交換帶來極為不穩定的變數。她們正是那些會引誘男朋友或丈夫背離交換約定的『壞女人』。」這種情形描述得最為貼切的正是在李昂所著的《北港香爐人人插》的林麗姿,她風情萬種、窈窕淑女,與極多的男人交歡,在參加婦女運動時也被其他保守類型的婦女予以鄙視,甚至對她用身體換取權力的狂言予以輕蔑。而賺賠邏輯,作者論稱此乃架構於父權社會之上的壓迫體制,而且這不僅是對女人的壓迫,同時對於男人也是產生某種扭曲的誘因驅使著去從事特定的行為,諸如性騷擾、窺視等,進而成為焦慮與壓力的來源。
性壓抑與性騷擾
「性騷掃就是性壓抑」,這是作者的宣稱,而正因為是性壓抑,所以即便在表面上看來是一方得利一方受害,然而其實是兩敗俱傷的,蓋因漸漸的,情慾在這種模式下會縮窄,精神甚至將萎縮。尤其,性騷擾並非成人才有諸如暴露甚至猥褻的行為,在幼年時男孩就可能會出現有掀裙子、看內褲、拉肩帶的行為,因為這並不只是個人的道德品格問題,更多的是這個社會提供了一條最簡便的路給不同的性別,遵循著這套遊戲給則自然是最省力的,自然而然的(雖並不完然自然的)在性別圖像的帶領下不同的個體依照自己性別的樣貌而成長。這就是一種框架(frame),在所有人的聚集體—社會中所成形的一種框架,而這裡的名稱就為性別角色,例如一個男人應該要是勇敢的、不落淚的、堅強的、外放的;相對的,一個女人應該是溫柔的、內斂的、守家的。框架的存在對於社會中的個體有指導的作用,然而一體兩面地,也有束縛的作用,這個圖像讓個體知道了方向,但是也在萬千的可能性中擇取了其中一條而排除了其他,而在自身偏離時也將受到社會中的同伴予以譴責。
正因「性騷掃就是性壓抑」,作者認為「因此,我們對抗性騷擾的方式絕不是更多更強的性壓抑,絕不是談性色變的驚弓之鳥心態,絕不是更多更密的監視及保護系統。這些做法只會強化性壓抑,更加壓抑女人,恐嚇女人,並不能改變女人在性壓抑和賺賠邏輯之下的不利情境,不能為女人增加一絲力量,而且,更可能會強化兩性之間本來便以充滿緊張、猜疑、與敵意的情慾關係。...為了對抗性騷擾式的性壓抑,我們需要更大的情慾空間更多自在的情慾流動,這意味著拆除身體交易的制度,打亂賺賠的邏輯。只有在嶄新的、自由的情慾環境中,女人才可能透過經驗、討論、和反省來認知情慾。也唯有在女人知道而且體驗過真正的愉悅之後,他才會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否在遭受騷擾—沒有自我和自主的女人如何明白自己的意願及感受呢?」這是種積極的倡議,也就是相對於消極性的建立更多防禦性的機具如監視器,不如擴散情慾的流動,讓這股洪水淹沒父權體制,進而重建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讓性壓抑不再存在而得以從根本處絕除性騷擾。
玩與性解放
而在前述提及對於規則的跳脫,作者稱此為一種「玩」的態度,「『玩』是一種對既有體制,既有規範,既有權力關係的大不敬態度。在『玩』的時候,一切現實世界的壓抑力量都暫時懸置,孩子不理父母的教訓,學生不甩教官的警告,兩個做愛的人痛快地拋開本來的身分和權力關係。這種『玩』的態度對現有的、靠性壓抑來馴化人群的社會而言,形成一股強大的腐蝕力量,是會鬆動壓抑、挑戰權威的反抗力量。」拾起這種態度,面對父權體制的壓迫與在其中的自我否定時,並非在規則中求勝,而是挑戰規則進而超脫之,這種玩的態度是種解放,是性(別)解放,「性解放的女人是愛女人的女人。在父權制度之下,女人從來便被規劃為搶飯票的敵人,可是,性解放的女人是拋棄父權邏輯的女人,她們不再有理由恨別的女人;相反的,女人是情慾資源交換及累積的盟友,女人是多元情慾發展和操練的夥伴。...性解放的女人也是愛男人的女人。她們了解性壓抑對每個人的身心殘害有多嚴重,她們明白也同情男人對性的焦慮和恐懼,她們用最自在、最輕鬆、最有經驗的『玩』心,引導不同的男人女人走上情慾品質提升之路。」這種解放無論男女,只要是「人」都是一條得以實踐的道路,這也是因為壓迫並不問性別,壓迫乃係對存於體制中的對象為之。
而壓迫的現象在女人身上尤其明顯,面對著丈夫的種種不是,諸如酗酒、外遇、賭博、家暴、不養家等等,可能有種說詞:「為了維持這個家,我要撐下去。」,然而這就是一種壓抑,或許說詞十分地堂皇,然而作者提到這不僅是對於自我的貶抑與壓縮,也是對於孩子教育的敗壞,「你的自我壓抑將是你孩子人生的起點。不快樂不滿意的母親養不出快樂滿意的孩子,你對孩子的全心投入,日後只會成為孩子的情感負擔。」也正因於這樣的母親失去了重心,反而將全部的心神灌注在孩子身上,讓他必須背負著這樣的重擔成長,而在這樣的情形下孩子確實可能成為一株揠苗。
作者之所以倡議對於現狀的打破,用玩的態度來面臨所有的日常—父權社會的常態,進而重新塑造出一條解放之途,正是因為,「兩性不平權體制的維繫不是經由什麼強大外力來之爭;相反的,他倚靠的正是我們沒有被挑戰的日常生活方式,正是我們最習以為常的兩性不平等互動模式。」。作者舉例代表父權體制的乃是婚姻與愛情或任何穩定性的關係,其認為婚姻是個重要的性壓抑方式,相對於此,外遇則可能是情慾的「最後一搏」,「不搏就看著自己的情慾沉寂,生命無奈,搏了卻又要面對另一種死亡(夫妻情意、親子和樂的死亡)。」所以作者熱烈的倡導要出軌、要外遇、要脫離現存的體制,對於出軌的妻子予以鼓勵、對於出軌的丈夫予以支持,也對於介入家庭的第三者予以贊賞,簡言之,只要是能偏離常軌甚至能顛覆者,在作者的觀點中都能得到正當化,蓋因其所訴求的就是對於父權體制的顛覆。正如作者所言,「女性主義的性解放論述因此必然是出軌的。他不但溢出父權體制為女性身體和情慾規劃的『軌道』(愛情、婚姻、生育),同時也歡欣鼓舞的慶賀女性同性戀情欲『出櫃』,走出黑暗封閉的孤絕空間。女性主義的性解放因此也必然是『變態的』。如果說我們社會中『正常』的情慾模式和資源是在性壓抑和父權制的框架中行形成,帶著扭曲僵化的烙印,那麼,衝破禁忌,充滿情慾波動的女性性經驗和性實驗自然也會被稱為『變態的』。」
批判
我們可以先同理在著作的時代作者的態度是其來有自的,在當時台灣剛處解嚴,社會運動與婦女運動在80年代開始風起雲湧,那時才正值解放的浪潮開始波濤,而從最基礎的層面來看,至少本書能顯示出當時的社會有多麼地閉俗,在作者的倡議中會收到諸如:「你這麼倡議性解放,我來(或我找人)讓你爽。」這類型文字的黑函,又或者是在著作出版年度中作者參加的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提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遭到兩位醫師的反駁「鄭丞傑醫師在自立晚報(1994年6月6日17版)說男性無法使女性達到性高潮是不能,非不為也,而另一位醫師江漢聲也附和這種說法,並說對性高潮的態度應該是『不忮、不求,而女性的性高潮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立晚報1994年6月13日17版)」(按:本書中也提及知識與醫學專業對於性議題話題壟斷的權力與謬誤,諸如將問題化約至生理層面,並把「性」用生物性的觀點理解,而不從社會與文化的層次來思度),這在今日來看或許十分荒謬,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觀念也確實在改變,就像人類也曾認為宇宙的中心是地球後變移到以太陽為中心一般。而作者最核心的主張或許可以書中這段話做為代表:「一個文化的活潑發展,不斷重生,是和那個文化中的情慾有多自由流動直接相關的。」蓋因情慾(或更直接的說性慾)與性相關,而性與人格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若人格能自由的發展,那麼文化自然而然能更活潑與開放,進而產生更寬敞的自由。
不過仍然能就書中數點予以批判。首先是作者認為一夫一妻制是父權社會的產物,而父權社會亦與資本主義的相輔相成等語,故只要能破壞這制度的都在其觀點中予以正面評價。作者的觀點當然是激進的,書背寫著媲美第二性的著作,然而我在閱讀時更感覺像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煽動性的文字、實踐的倡導與激進的觀點、對於既有秩序的全面反抗以及將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掛鉤並且以商品交易的觀點來詮釋性別關係,這讓本書更像是一種觀念宣傳的小冊(pamphlet)。然而,一夫一妻制並不能說是父權社會的產物,更且父權社會並不只是將性別角色予以固定配置的單純模板,父權社會的核心特質在於支配(domination)的性質,以及對於男性氣質(masculinity)的崇拜,所以即便是女性主義也可能會是父權式的,母系社會也可能是父權式的,更且在父權社會幾乎是世界性的常態下,在世界各處也有著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基此可知,父權社會與一夫一妻制的關聯性並不那麼的直接,甚至,一妻多夫也可以是父權的。
而在作者正面評價的各種衝破體制的行為中,其中一種是第三者,在此就以第三者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先予以指明者為作者所說的這種第三者,並不是抱持著為了扶正擠掉元配那種心態來進行情慾互動的外遇,而是以自發自主的情慾發展來發展關係的外遇。惟固然抱持著此種自主的態度就不會如同原先仍在規則內的外遇一樣繼續鞏固了父權體制,然而這是只在這個方面是如此的,沒被審視到的部分是那外遇的男人。在相對的互動中,這就像賺賠邏輯,如果今天一位女性為了表現自主性(autonomy)而穿著性感、裸露,甚至更進一步就像林麗姿一般睡遍了男人而取得權力,然而觀者或是與其性交對於女人而言固然在主觀的層面上她可以認為我是自發自主的,我是在彰顯我的主體性,然而我們要如何判定這樣是為自主而非精神勝利法?作者稱:「如果豪爽女人只是『白給』的傻子,完全不攪亂賺賠邏輯,那麼我們的社會該不會介意她們的存在與活動;但是事實上,豪爽女人經常遭受嚴厲的指責與冷酷的放逐,這顯示他們的作為必然干擾了賺賠邏輯的運作及合理形象,勾動了性壓抑之下的情慾暗流,因此他們才會遭受父權制度的打壓。」這樣的解答是十分無力的,甚至是敷衍的,僅因可能遭受的批評就稱已經干擾這個體制所以才遭受打壓,這樣的推論更是十分薄弱的,而且這種做法有弄巧成拙的風險,也就是單方面的認為我是個自主的裸露、性交的主體,而且是自由的,但是在社會的現狀中因處於另外一種價值觀的領導下,這樣的主張仍會在主流中被淹沒,亦即在客觀(間主觀性的客觀,即intersubjectivity)的觀點中這仍然是個送到嘴邊的肥肉。那該怎麼辦?在面對某種社會結構的問題,在客觀層面上的主流認知如何透過行動打破?又或者是在初始階段這些被(客觀)評價為「免費」的事物只能成為行動的代價?在這裡本文所能提出的說明嘗試,或許是必須是要以具有「集體性的政治運動」來進行才能有效撼動體制—亦即政治化。例如free the nipple的運動中主張,女人的乳頭是被建構的色情符號,而為了打破這一點,諸多女性在非色情的環境中將乳頭予以暴露或是藝術化,使得原先與色情文化的連結消失,然而如果不是這樣,而只是在如個人性的、隱密性的或甚至在男性視角下(諸如攝影)的暴露,仍然是繼續提供給原先所欲打擊的體制養分而已。
最後,本書中也常可見得有過度、不當連結的情形,例如作者稱「色情行業事實上是在處女情結的交易模式之下氾濫的。」理由是在賺賠邏輯中換不到長期飯票的女子要換短期飯票,或因不是處女而價值大減進而投入色情行業,然若只要不對性感到羞恥禁忌,成為愉悅的經驗而產生尊重與自信,那怎麼會有色情交易?作者如是說。色情氾濫是因社會不夠開放,未提供女性發展獨立經濟管道,更因不容許女人肯定性與身體。又或者聲稱婚姻與愛情等穩定關係或使得情慾衰退到萎靡,原因在於這些是父權式的愛情與父權式的婚姻。又或者是出現諸如「有人說,兩人有愛情時做愛比較愉悅比較爽,但是即使你的性愉悅不能沒有愛情先行,你也不能規定別人都非得如此不可。事實上,許多人的經驗都可以證明,和不相識或初相識的人做愛比較沒有顧忌,沒有禁忌,不必擔心形象得失,反而做得自在,感覺很棒,而且還因為陌生新鮮而特別感覺興奮。對他們而言,無愛之性一點也不減損其爽度。」在批判他人僅為個人經驗的主張時,實際上作者也只拿了(多數)個人經驗當作論述基礎。又或者在面對性騷擾時主張有更多的情慾流動即可,而無需有防備的設施一般(監視無效)。惟色情行業或是女性投入性產業跟處女情結的關聯並不大,因為即便沒有處女情結性產業仍然存在甚至蓬勃(例如今日與我國之外),蓋因性產業除了商業化經營是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營利外,不得不投入其中的女性之情形不少是經濟貧困,而非在賺賠交換中因為貶價只好換取短期飯票,甚至作者提供的解方是讓性開放、情慾流動,那麼色情產業就會結束的結論也是在前先的不當連結中得出的無端結論。其次,穩定關係的發展未必會使得情慾萎靡,此乃作者基於性解放的觀點下對於情慾的理解乃是與性解放掛鉤:多樣化、多人化、多經驗化,這個假設並未經論證,甚且作者的激進態度可以認為是只要與父權制度有關的一切都應該予以撻伐一番甚至革新,然而世界上存在的社會幾乎都是父權式的,而社會中的各種事物也幾乎是父權式的(就連法律也有被這麼主張),那麼在這激進的觀點之下似乎整體社會應該要予以顛覆那才是真正的解放了。在面對性騷擾這樣的問題時,作者更是表現出在全書中不時出現的過度理想化到近似天真地步的態度,即透過讓情慾更流動,那麼賺賠邏輯與父權體制就會鬆垮,進而性壓抑就會解消,這才是治本,而從來無需治標去裝設監視器或是提醒女性攜帶防身物品。退萬步言,縱然所言為確,然而改革從來並非一蹴可幾,遑論這樣的理解並不全然符真。就像被害人檢討並不是要去二度傷害,而可能是提醒或督促(潛在)被害人什麼樣的行為能降低被害的風險。
結論上而言,作者提出的主張與宣稱是很煽動性的,同時也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不過仍難以掩蓋過度的天真,但無論如何當我們同理作者寫作的年代與企圖時,仍可見得此文本的意義。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派別本身只是一個分類,而從分類來認識任何一種理論或甚至一個主張(者)都會是過度簡化的。我們僅需暸解這種解放思維的核心在於:不只是對於女人,而是對於所有人的尊重以及自主性的實踐與倡導,亦即,「只因人之為人,所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