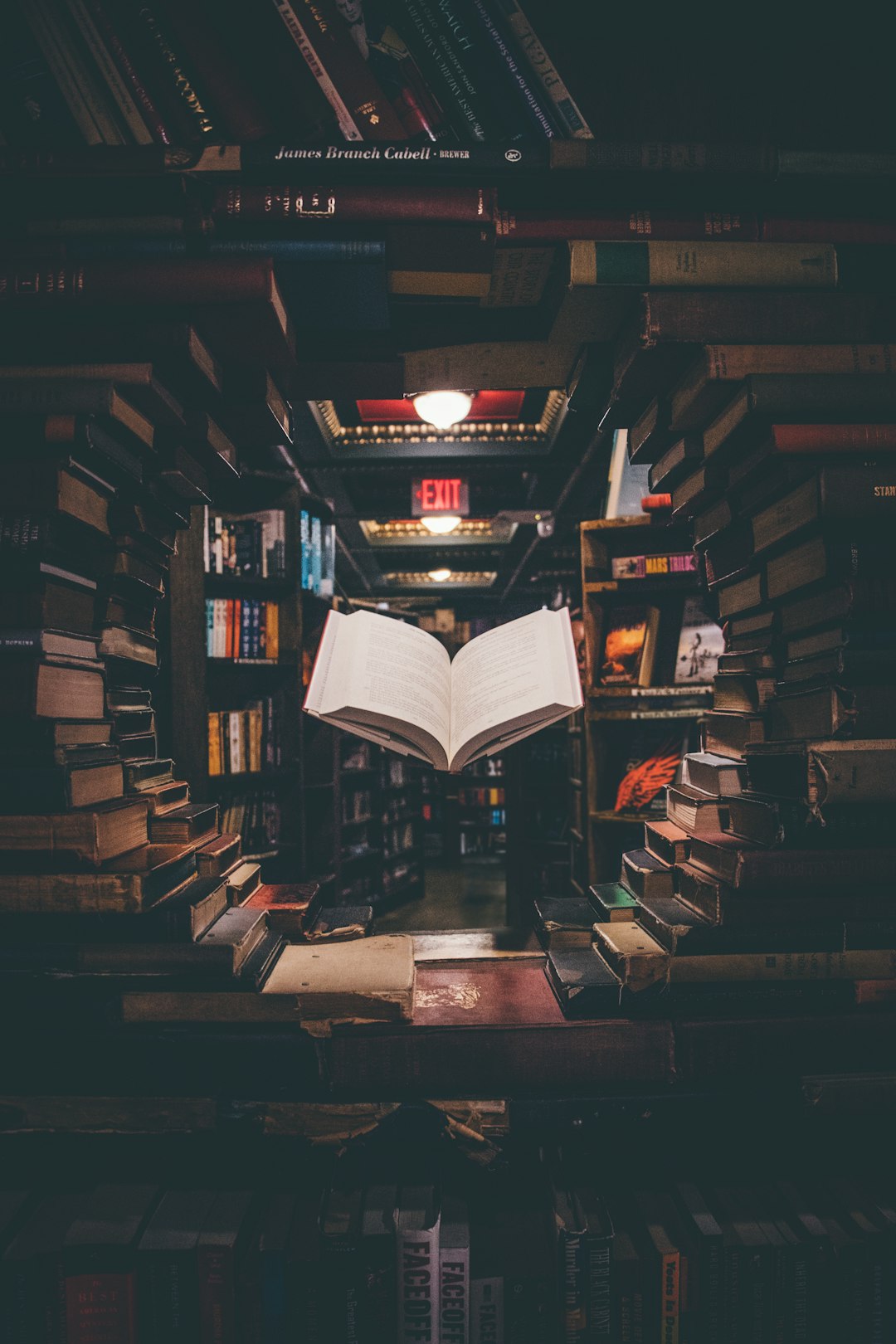「典範是一可被重複套用的範例,而此一範例在原則上能用同一類型中的任何個例充任…典範的成功…起初只不過是它在一些特選的事例中,所呈現出的成功的保證而已。常態科學之工作即在於使保證不致成為空文。」(頁36)
*
大部分的科學家在整個研究生涯中,就是在為典範做「善後工作」,這些工作大致包含:- 擴展對某些事實的知識,因為這些事實已由典範指出是十分重要的。
- 增進事實與典範預測兩者間之吻合程度。
- 精煉典範。
(頁36)
書中還提到,在典範成功之前與之後,科學家的行為、以及研究的問題也會改變。就我自己對這段的理解,在典範之前百家爭鳴的狀態,對於核心問題還沒界定,所以任何的「why」都能提出;而在典範出現之後,因為問題已被定義,科學家為了精煉典範從事的科學研究應該會轉為提出「what if…」。從提問的形式應能明顯區辨一門學問是否到了成熟階段。
*
因科學家基本上不會去做不在典範範圍內的研究,研究的方向基本上也被限縮了。作者確實也提到了這件事,他表明常態科學的研究範圍是極小的,所以眼界也受限制。典範迫使科學家將注意力集中在某個小範圍內的專門問題。
這情形似乎與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學者形象不太相符。一般人或許多認為學者就是「博學多聞」的人,然而事實上學者僅是在某一知識點上鑽研較深的人;甚至或許很多讀到碩士的人都有類似的感受:「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的無知」。
感受到自己無知的這種體悟若以上述科學本質的觀點來看,似乎就容易解釋。因為我們的視野的確被迫縮限在專一的問題之上,我們縱使為了研究讀了大量文獻,這些文獻內容也都是圍繞在相似的問題範疇中,以幫助我們認識該問題的立體形象。
這也是我自己當初做研究時覺得不自在的地方——我感覺自己被限制住了!在知道外面還有好多種問題,腦袋也有好幾種想嘗試的實驗時,被迫只能專注在某個問題與特定研究手段真的不太舒服,尤其當我自覺是個需要有空間「創作」的時候。然而,常態科學工作並不是藝術創作。在我感覺他是為了將這世界整理得更有秩序而誕生的活動,因而「超出規則」的任何行為,通常都是不被允許的。
曾經我對這樣的活動感到不耐,但離開研究領域,重新再檢視這段過程後,我感覺常態科學工作雖然看似呆板、不斷重複類似的事,但它不是不能創作,只是創作(這裡我指新理論的發想)是建立在前期非常縝密、紮實的研究成果上的開展,這種開展不一定能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靠一己之力堆疊而出,而可能需要耗費幾世紀的時間由許多學者一生的成就綜合才能獲得。也就是說,可能有好幾代的科學家在這條科學研究的洪流之中,注定只能完成常態科學所規範的「善後工作」。而且事實上也因為科學這樣有條理的進行,才能幫助我們對這世界有系統地理解(這在後面章節有談到)。
但或許我這樣講還是太過偏頗,說得「善後工作」好像是種無可奈何下從事的活動,我承認自己對於科學的憧憬在於「創造」,所以才會稍稍認為善後工作較為「無趣」。事實上,一輩子投入於科學之中的科學家擁有著更深厚的動機,這也是我自己仍在嘗試探索的部分,剛好下一章節作者將會分享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科學家願意持續地進行常態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