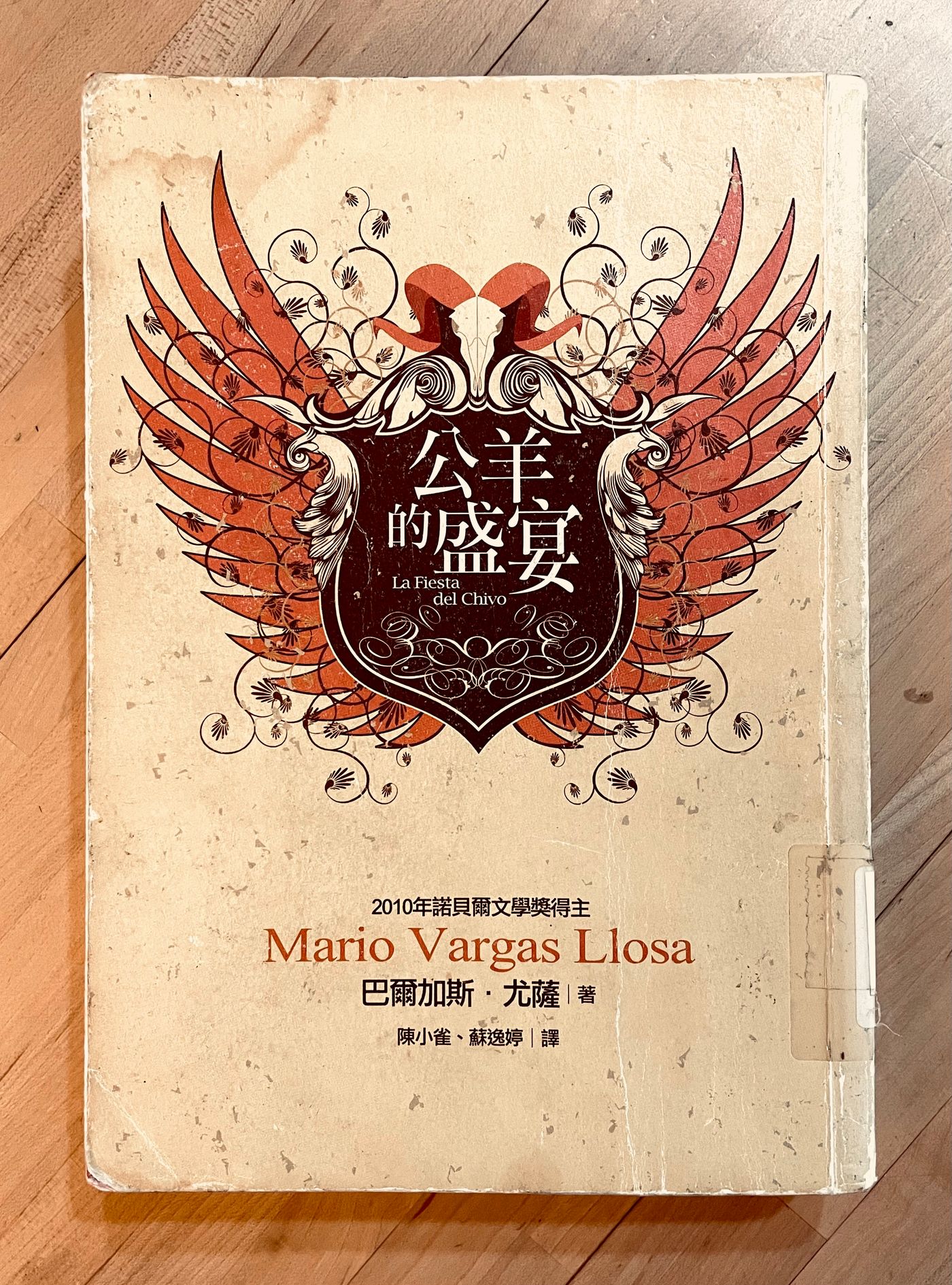真正的奴役,並非臣服於主人之下,日夜受人所控;而是當你已經脫離枷鎖,卻寧願轉頭跪地,懇求主人再度從你手中贖走自由。
三十年的暴力,讓人心已被服從制約,於是叛變的將軍終究無法下令奪權;於是忠勇的軍人決議聽令處決摯愛;於是失勢的參議員不惜出賣女兒的初夜;他們看著元首的時候說,元首,我如此行事是對您的服從。即便多麽渴望自由,他們最終依舊選擇親手折斷自己的翅膀。
羅曼沈浸在一種被催眠的狀態之中,心想,自己會有這種冷漠的表現,都要歸咎於元首,儘管特魯希優的肉體已死,但是,其靈魂與精神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卻還在奴役著他。——P.402《公羊的盛宴 La Fiesta del Chivo》

特魯希優掌權超過三十年,被暱稱為「公羊(Chivo)」,他暴虐無常的統治,輔以大量的金權攏絡,將整個國家變成了他獨一無二精心享用的饗宴。我在多年前因為當時的讀書會成員簡介,曾經閱讀過《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對於拉丁美洲從舊殖民時代的經濟掠奪史,以及殖民者退出之後,如何繼承該掠奪體系的強人統治,以及而後世界貿易資源傾斜導致的新殖民主義等,有些許的著墨。《公羊的盛宴》作為而後的閱讀文本,剛硬的寫實主義風格,更加清晰地將上述的歷史事實轉化為故事。自此而後,我對拉丁美洲這塊大陸的形象,也才更加豐富了起來。
尤薩到底是一名什麼樣的寫作者?他是如何看待特魯希優在拉美永劫回歸般的歷史傳統裡扮演的角色?這一部群像劇作品,又為什麼值得一讀?
拉美文學的叢林幽深且神祕,首先,讓我們從尤薩開始說起。
文學即是叛逆的火:尤薩作為堅定的政治批判者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或許並非台灣閱讀者熟悉的名字,然而其在世界文學以及拉美地區的影響力可謂深遠。一方面是他爆裂敢言的華麗語言,使他的作品具有強烈的辨識風格,算是拉美魔幻寫實主義後,又一波奠定寫作地位的頂尖人物。一方面是他對於政治的敢言以及實踐,使他不僅曾經在秘魯以政治新人之姿參選總統,亦不時針砭時事:他於 2020 年 3 月,西班牙因為 COVID-19 到來措手不及,疫情飆升,尤薩即在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政府必須為了隱瞞疫情初期資訊付出責任,並且批評「中國模式,亦即政治獨裁的自由市場,不應是第三世界的唯一模範。」此言一出,自然遭受中國政府強烈反擊,即刻下架中國市場內尤薩所有出版書籍。只是尤薩辛辣且堅定的態度,以及其一以貫之的寫作概念,自然也不可能會因為封殺動搖。
文學就是火,它意味著叛逆和反抗,作家的價值就在於抗議、反駁和批判。
——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

尤薩的寫作風格何以具有強烈辨識度,亦可從他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學院引言窺見一二。瑞典皇家學院認為:「從總統到妓女,他對於人們有著無設限的關注,從政治家的自負到刻畫愛情的精湛情節。……尤薩一眼就能洞察無知的愚蠢與邪惡的消沉,利用虐待傾向的刑罰主義與階級虛榮來描繪男人的友情,是他非凡的寫作能力。」我在閱讀他的作品時,時常因為他大膽、露骨的用詞感到壓力,尤其他在描寫高壓下人性的強悍與懦弱時,可謂直言不諱,只因他誠實呈現極權統治之下必當扭曲的群體行為,絕不搽脂抹粉。若另外一名拉美文學巨擎,外交官詩人聶魯達的詩作是豐美而壯闊的地景,尤薩的小說即是一場華麗卻殘酷的暴風雨——《公羊的盛宴 La Fiesta del Chivo》在翻開第一頁開始,就宣告著這場盛宴必當鮮血淋漓。
一旦成為盛宴的賓客,便再也不能離開
《公羊的盛宴》由三條全然不同的故事線開展,三條故事線並不一定有所交集,然而卻是特魯希優政權在三十年統治後,即將邁入倒台過程的群像書寫。這三個故事中,一則發生於特魯希優倒台後二十年,一名當初逃亡的成年女性回到故鄉,揭開當時她父親為了保住政治地位,將她當成性獻祭的過往傷疤;一則是特魯希優第一人稱視點,貪污、濫權、招妓,可謂是他魚肉國家的聲色犬馬日誌;最後一則則是驚心動魄的反叛者復仇計畫,敘述一群被極權統治逼近牆角的多明尼加公民,如何策劃暗殺與政變,且而後被政府清算的過程。
作為讀者,整個閱讀體驗,即是在上述這三條支線裡,以全知視點重構特魯希優時代的風景。特魯希優坐在政治餐桌上大快朵頤,分贓著國家資產,並在過程中剷除阻擋他享用美食的障礙。殺戮之稀鬆平常,有如橫切端上餐桌的肉排。被他邀請入座的袍澤與親屬,即便最初政治理想清高,也在經手虐殺他人與自我催眠的循環下,喪失了離開盛宴的能力。而到最後,當元首吃完了主菜但尚不饜足,袍澤與親屬也心甘情願躺下,成為這場血宴上一道新的甜點。
明知這是一場一但開始就無法離開的盛宴。為什麼這些人當初願意入座呢?
尤薩的解釋是:在特魯希優掌權的三十多年裡,這些袍澤與親信,用他們全部的時間在政府與公有事業裡為偉大的元首賣命,而元首的確在過程中一定程度實現了這些袍澤與官僚的國家理想:他的確帶動了工商的發展、帶動社會建設、創造新的財富;他抑制了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的蔓延,並確保了多明尼加在戰略地緣上的國家安全。經歷過一整個世代欣欣向榮的情景後,他的人民與近身官員,因為上述這些國家的成就,是以景仰與愛慕在擁護他。他們發自內心渴求能夠在那豐碩且強力的羽翼下求得庇蔭。

這些人是這樣想的:在這個極權者、國父、強人、國家的意志之下,若能跟隨他,放棄一點自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在真正影響到我的生活以前,選擇性忽略一些眼前的事實,難道不是情非得已嗎?即便這個元首動用軍情與特務,在他國謀殺記者、毆打神父、將罪官員、屠殺移民、臨幸任何他與他的兒子看上眼的女子,甚至在公眾場合污辱這些丈夫與父親。但只要元首可以對抗戰亂,對抗美國,讓這樣的國家在屈辱了上百年的剝削後終於成為了一個能夠站起來的國家,是不是這場血腥的盛宴,也是值得的呢?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退讓出空間,典當出自由,一點一滴的,蠶食終究成為鯨吞。人們以為典當的是可有可無的權利,卻最終才發現典當的不止是自己,是牽連其中的所有人,以及他的一切,包含忠誠、愛與尊嚴。尤有甚者,追隨者這般對於元首的害怕、屈從與懦弱,甚至在元首都死了以後都不會消失。因為他們早在過程中成為了特魯希優撤守徹尾的奴隸。
當暴力將生命變成一片荒漠
三篇故事裡情節紛雜,然而,我認為最能夠合理化上述描繪的「自我囚禁」以及以此早成的生命枷鎖,就屬「智多星」與女兒的故事最為怵目驚心:「智多星」身為特魯希優政權的最優秀官僚,其女兒終於在逃難二十年後,由美國返回多明尼加。她看著曾經榮華而衰亡的家園,與眼神已然渙散的失智父親,她問:「你知道你做了什麼,以及你曾經後悔過嗎?」
這名女子在二十多年前,也和其他國家內的青少女一樣,對父親一心一意輔佐的元首充滿敬重;甚至憧憬特魯希優那英俊而高傲的兒子,希望有一天能夠在晚餐或宴會裡遇見他。少女崇拜父親的智識,服從父親的決斷,並且信任父親的指點。然而父親寧願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親手送葬女兒的尊嚴與純真。彷彿對他而言,任何人的價值都不過是一場交易。
然而發生在閨房的描繪卻才是最荒謬的即景:當特魯希優發現,他好不容易拐騙來的少女已經因為驚嚇在床上動彈不得,他卻因為年紀過大無法勃起,他的盛怒與其說是針對性的無能,更大一部分是時間對他造成的困境:性是權力、勝利以及自尊的象徵。性是他作為國家宰制者的報酬。他的精神還有辦法宰制這一切,但他的身體卻在污辱他:衰老是強人最沒有辦法抵抗的敵人。
少女在那夜還是被送回家了,但她的純真已死。而她死掉的也不僅是純真,而是從今而後對任何人的信任。她不再知道家人的愛是否真實;不再能夠泰然面對陌生男子的眼光;也不再有能力建立任何親密關係。既便特魯希優最終也已死去二十年,可她被留下來,禁錮在華美記憶裡,被那晚的記憶凌遲,就像她永遠記得她是如何被摔進過於俗爛的巴洛克風格大床,眼見敬重的元首像是失控的瘋狗對她進行恐嚇,而她只能失去聲音。
元首閣下將我的生命變成了一片荒漠。
奴役的形式有很多種:智多星作為父親,在這三十年間,眼見如此多同袍在這過程中迷失,原以為可以逃過一劫的他,依舊親手折斷了飛向自由的翅膀。以為可以用官僚身份保護家人的他,最後依舊因為政治前途背叛了他原應守護的人性尊嚴。而智多星的女兒則從此之後被關進了受創的牢籠裡,她而後的整個人生都無法從那晚的惡夢中醒來。即便她有多功成名就與試圖治癒自己,她都無法抹除那夜崩壞的記憶。
最讓人悚然的是,特魯希優統治的三十年裡,他們也只是其中兩個例子而已。
讓想像力漫遊即是最高的政治風險

《公羊的盛宴》絕非是一本能提供愉快閱讀體驗的作品。作品內高壓環境的描繪無所不在,暴力與流血的情節亦處處可見。且就算特魯希優最終被暗殺身亡,尤薩亦沒有使用溫情的筆法,續寫多明尼加對於未來的希望:畢竟極權倒台之後,再度上台的理想家成為下一個極權的例子所在多有。尤薩的目的非常清晰,他意圖帶領讀者在這荒蕪卻震懾的群像劇裡,讓我們直視國家背後,有如蜘蛛網絡的權力系統,以及被埋入地底的黑暗故事。並也讓我們以上帝的視角站上特魯希優的餐桌,看見極權內部的集團裡,是如何靠著持續不斷剝削他人與彼此,來編織著自欺欺人的幻夢。對他來說,這樣嚴肅且拘謹,能夠直言批判的筆,才是他做為作家堅守的核心價值。
那些懷疑文學有這些功能的人,請捫心自問,為何所有的頑固政權會從出生到死亡控制人民的行為,如此害怕而必須建立審查制度來箝制人民的行為,並且以猜忌之心來監視獨立的作者。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讓想像力漫遊書中的風險,而反叛思想化為創作之後,讀者一經比對,發現自由可以讓創作存在,而創作則實踐了自由,然而,在現實世界裡讀者卻受制於恐懼和愚民政策。
——〈閱讀和虛構的禮讚──得獎演說〉Mario Vargas Llosa
尤薩一生波瀾壯闊,自年輕起即是二十世紀拉美極權的第一線批判者。回頭再看文初他對於時事的針砭,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他的骨氣何在。閱讀完此書後,我最大的警醒有二,一是反思權力作為雙面刃,帶來的盲目與險惡:正因為特魯希優幫自己創建了太多權力的濾鏡,讓他直至最後一刻才發現,他不止讓他人成為了獵物,他自己也成為了盛宴中最大的祭品。其二則是對於平庸之惡的警醒:若我們總在日常威嚇下懷有退讓一步也無妨的嘆息,在似是而非的花俏語言中迷失,或許我們也早已站在下一場盛宴的門口而不自知。
那邀請我們入場的門票,究竟是蜜糖還是毒藥?那遞到我們手中的酒杯裡,斟滿的到底是鮮血還是紅酒?身為台灣人的我,或許也早就有了答案。
方格子另外一名格友作品《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小說中的作家與詩人》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在此也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