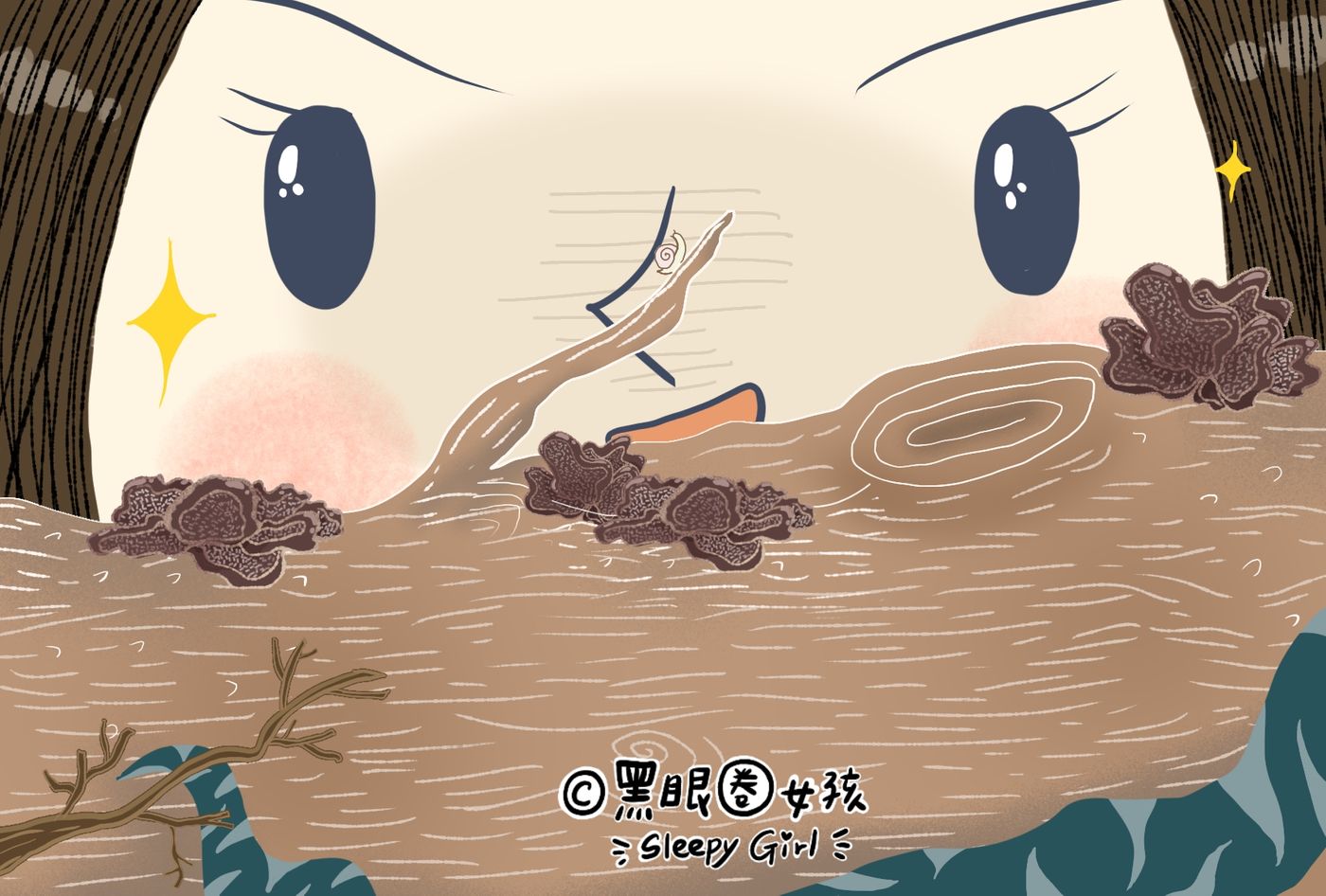關於饑餓,關於寒冷,關於世態炎涼,關於旁人冷漠的眼睛跟嘴巴,有誰比蕭紅寫得更讓人感同身受,驚心動魄呢?她用老家哈爾濱回憶轉化而成的早期短篇小說集《商市街》裡,隨手就可以撈到冷靜的冷,絕望的絕:
孩子生下來哭了五天了,躺在冰涼的板床上。漲水後的蚊蟲成群片的從氣窗擠進來,在小孩的臉上身上爬行。她全身冰冰的,她整天整夜地哭。冷嗎?餓嗎?生下來就沒有媽媽的孩子,誰去管她呢?
雖然,「只要他在我身邊, 餓也不難忍了, 肚痛也輕了。」但是,如果他跑了呢?而他果然就跑了。這樣的閱讀經驗,不就是「真心話大挑戰」無限重播版的折磨嗎?

蕭紅一個人活得太辛苦,終究被故鄉,被男人給辜負。慕勒不一樣,她活在有愛的父母身邊,受到比較好的教育,而且持續得到發表機會。
德國文學的圈外人
蕭紅的回憶,往往是從饑餓出發。慕勒的回憶,永遠跟欺騙有關。蕭紅的饑餓是自己的事,慕勒的欺騙則跟一個時代,一個族群,一個時代的一個族群有關。
慕勒出生在山間的低地區,這裡世代講德語,想要有好發展就得學羅馬尼亞語跟俄語。慕勒大學念的是羅馬尼亞與俄國文學,畢業之後,卻因參加德語作家爭取自由的活動而丟掉工作。接下來的幾年,她寫作並當德文家教跟幼稚園老師貼補家用。1987年,她和也是作家的先生移居柏林至今。
生於一個在羅馬尼亞講德語的家庭,一生有一半時間用德文發表關於羅馬尼亞主題的作品,註定在生活跟創作領域當中都是,邊緣人。
31歲就得到德國文學獎,之後陸續拿到卡夫卡獎和柏林文學獎等獎項的她,即便獲頒諾獎之後的介紹文字中,德國媒體還是會提到她算是「德國文學的圈外人」。
慕勒得獎之前,唯一被出版的中文譯本小說《風中綠李》(台譯本為《風中綠李》),跟《狐狸那時已是獵人》還有《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被合併稱為她的《羅馬尼亞三部曲》。
這三部作品通通跟恐懼有關,也都是慕勒個人經歷跟故鄉受壓抑年代的氛圍的創造性再現。很早就是「德國語言與詩歌研究院」院士,並在不同國家的大學教授寫作的她,認為語言的使用必須精准而有韻律感。因為在她的心目中,語言可以構造「我們的眼睛跟心靈」。
慕勒的書寫策略包括了,詩化的散文體文字,用意識流描述人物的內心和想像,展示出碎片化的故事拼貼。

風吹得再猛一點兒
慕勒小說裡的人物發言,很多時候都不會用標點符號標明這是對話,而是讓你在閱讀過程當中發現,那可能是想法,可能對別人說出口過,也有可能只是說給自己聽。讀者會覺得自己就是書中人物:
一位先生的襯衫要保持潔白不容易。如果他四年後跟我回家鄉,那就是我的愛了。如果他穿著白襯衫在村裡行走有本事讓路人豔羨,那就是我的愛了。如果他是一個體面人,理髮師上門來,到了門口脫鞋,那就是我的愛了。在跳蚤跳來跳去的髒地方保持襯衫的白淨不容易,蘿拉寫道。
蘿拉是《風中綠李》的主人翁,她從貧窮的山區到城市念大學,希望跟可以保持白襯衫乾淨的人在一起。我們後來就會發現,只有加入某種階層,才能過上這種體面的生活。
讀著讀著我們會發現,蘿拉其實已經死了。我們是跟著她的室友,從她留下的文字,她說過的話,拼貼出她的過去。
為了得到更好的發展,包括求學,得到更好的分數,在校園得到比較好的待遇,羅拉得跟不同男人那個。她知道主動去這麼做,在心理和身體上面傷害最小,而又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可是,蘿拉穿著白襯衫死了。而空氣中傳來的歌聲唱著:
昨天晚上,風兒
將我吹向戀人的臂彎
風吹得再猛一點兒
我就會被吹斷
還好,風兒停了。
所謂的「風中綠李」代表的是脆弱與殘酷。機會主義者還有跨過他人屍體而毫無憐憫之心的人,會吃李子,而善良的大多數人,都只能被吃。
欺騙就是我的工作
蘿拉的祖母晚上睡覺前會唱歌給她聽,並且說該讓風中綠李休息了。風中綠李是想要過正常的,普通的生活的欲望。他們從小就被教育,不可以讓風中綠李占上風。
《狐狸那時已是獵人》和《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裡的「我」,通通都知道不可以讓風中綠李牽著走。前者的主角被MM員警盯上,家中的狐狸皮在不知不覺中被撕掉一點一點。後者的主角,更是對於高壓狀態處於「毀滅吧,累了」的狀態。
慕勒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此人像只大野雞》,講的是一家人想要申請護照始終有這個那個問題,最後是女兒P睡才走完最後一裡路。這些被行雲流水,彷佛像歌聲般文字寫下來的紙堆底下,絕對滿滿的都是魯迅所發現的「吃人」二字。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說:「荷塔·慕勒以詩歌的精煉和散文的直白,描繪了無依無靠的人群的生活圖景。」關於她描繪得無依無靠人群的生活源自何處,慕勒是這麼說的:
我的寫作層面是那個巴納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後來,是那個集權主義國家羅馬尼亞。這個國家讓一切經歷都保留著自己的本身,因為權力的視線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後來稱之為「集權主義」和「國家」的東西,只是一個偏遠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慕勒說,「欺騙是我童年時的工作」,她從小就知道她得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按照《風中綠李》裡蘿拉的朋友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別人會覺得可笑」,有同情心的便會說你是瘋子。
怎麼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
有人記下了。
遙遠卻真實而清晰
慕勒的獲獎演講題目叫做,《你帶手絹了嗎?》
對我們來說,家裡沒有其他東西像手絹那麼重要,包括我們自己。手絹的用處無所不在:擤鼻子;出鼻血時擦鼻血;手或胳膊或膝蓋擦破的時候包紮傷口;哭的時候擦眼淚或者咬住手絹抑制哭泣。
慕勒還講了幾個關於歷史、親情、友誼、羞恥和尊嚴有關的手絹的故事。那些回憶,就跟她的小說跟散文裡面的筆調一樣,有點遙遠卻真實而清晰。
心理學家阿德勒說: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小說家海明威說,不幸的童年是創作者的寶藏。
童年的,青少年階段的,大學畢業工作受到的壓抑和扭曲,讓慕勒可以一生反芻並轉化成作品,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謝謝文學的魅力,我們才可以發現回憶不會欺騙。
謝謝文學的距離,我們才可以平靜地思考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