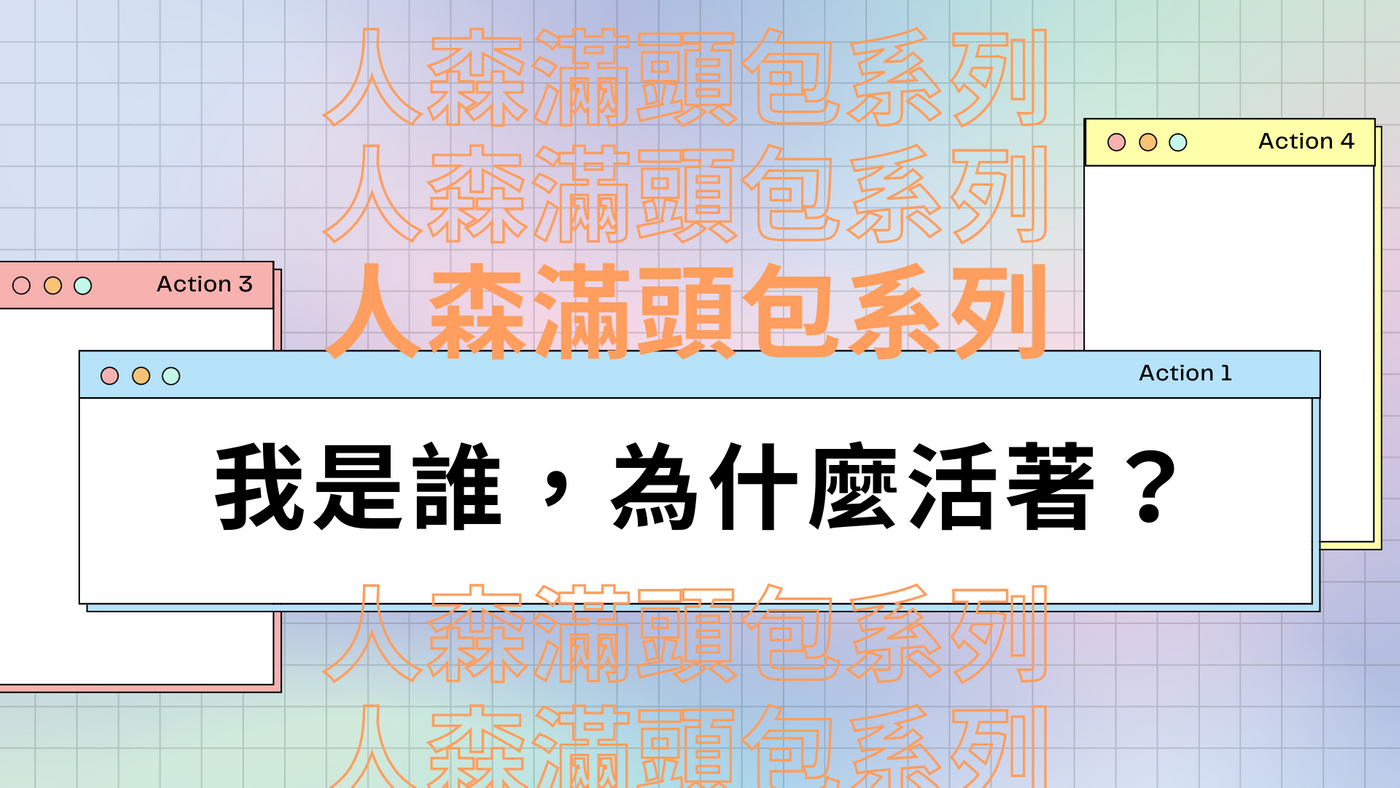我是誰?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我是什麼樣子的?老實說,這個問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我來說都是不重要的,別人想要我是怎麼樣子,我就是什麼樣子,我生命唯一的目標就是當一個恰如其分的人,盡可能的符合我身邊所有人期望的樣子,很累嗎?我並不覺得,當我只有這一種活法的時候,我可不會顧慮自己的狗屁感受。
這個問題給我的感受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我很樂意跟你分享更多。我是誰,我是一個沒有頭的男人,大眾臉,三十五歲的男性,一個胖子,微微駝背,牙齒不整齊,永遠戴著一副眼鏡,頭髮是平頭,自我小時候開始,我就有白頭髮,嘴角總是不自覺的向下,當我被觀察的時候,我就會全身不自在,這就是我,
我盡力表現出不在乎別人看法的樣子,但內心又強烈的渴望他人的認同,我不允許自己流露出不應該有的情緒,批評自己,對自己的無能感到悲哀與憤怒,這就是我想必你對我一定已有了部分了解,一個沒有頭的男人阿,乍聽之下驚悚又離奇,但又是那麼稀鬆平常的事情,漫無目的,遍尋不著自己的目標的人們,盲從他人給予的目標,活著他人規定的人生,自以為是,很多時候只是別人眼中的工具而不自知,他人命運的蛀蟲,帶給別人的傷害比祝福還多,這就是我
這是我的生命故事,是我正在經歷的一切,有時候我會往過去奔去,為了藏匿我的心思,也為了釐清我的心思,有時候我眺望不可知的未來,覺得我在那裏應當已有了一席之地,很少很少的時候,我活在當下,我知道自己的不可取之處,我知道,是我的惡習造就了我的一生,我也知道改變必須依靠持續的行動,可知道不代表行動,知道就只是知道而已。我必須找到改變自己的動機,賦予他意義,那是必經之路,我可能會在半路上夭折,我確定這就是我
我會占用許多篇幅來描寫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釋放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心思,讓他像一條夠深的河流,以流動的思緒捲走我內在的泥沙,我的情感也應當被細緻的描述出來,而不是讓自己沉溺在無意義的恐懼之中,我的恐懼與我的情意是一致的,我冀望自己對於所愛之人是有用處的,有價值的,只要能夠被利用,我便覺得心滿意足,我知道這是病態的,不自然的,有毒的,這是我的生命經驗對自己的設限,我想要盡可能的獲得存在的資格,儘管那過程那結果都將帶給我痛苦,那種扭曲的慾望像一條環繞我頸部的繩索,抽乾我的呼吸系統,令我的靈魂窒息,我不知道自己死了幾次,那種存在感的死亡讓我變得更加空虛,更加孤獨,很多時候我不活著,我只是看著。
儘管有家人與我同住,我仍然感覺孤獨,不被理解,我是個怪異的人,我不能表露自己的想法,因為我的軟弱不被現實所接受,我的軟弱沒有價值,那持續掏空我的痛苦在警醒著我,我不能讓所有人知道我沒有頭這件事情,我必須為自己掛上偽裝,我要去模仿我心中最羨慕的那些人,以他們的方式行動,以他們的想法思考,以此作為我的維生手段,我知道那是非常粗淺簡陋的模仿,但大多數時候,這已經很夠用了。沒人會在乎我真正的感受,除了我自己以外,喔,大多數時候我也不是很在乎,這就是我。
我躲藏在他人的眼光之中,在自我抗辯的過程中,在時間的流逝裡,我是誰?我是誰取決於我的行動,我的行動是如何成形的?是什麼塑造了我?是那些語言將我轉化,編譯,操弄著我的思想,是誰的意志引導著我,發出聲響,問出問題。
我是由一連串的事件所引發的結果嗎?我是事件的本身?我是誰?我的意志決定了整個世界的哪個部分?用處、意義、價值,我該用什麼方法詮釋他們?我想將所有的空格填滿,然後又一直分心,這是我,知道跟做到是兩回事
我膚淺的認為這是我有史以來最大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為我多次的從分心的狀態中回到我本應進行的工作上,也因為我對自我的淺薄分析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滿意,我不知道這種拆穿自己的伎倆能不能奏效,但對我來說,這種剖析不失為一種虛實交錯的描寫,我語言中的含意是不可能被精確的解讀的,當我對於技巧運用更多的是依賴自己的本能。
我知道這只是我的一面之詞,但你真該看看那時候我所面臨的處境,我總是在夜裡回到童年中的動物園,我跟那些動物提到種種關於未來的可能性的時候,他們臉上驚訝的模樣簡直跟你們此時一樣。
我可以從這種狀態中跳轉到另一種狀態之中,如氣體轉變為液體,我生命之中的每個結構沿著我的思緒,時而分散時而密集,我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當我說我已經完結的時候,我便已不復存在。我是誰?我是一個持續轉動的風扇,我的動力來源是任何一個濕熱的呼吸。
我就是我,我沒有意義。我不在別人的掌控之中,我是無限的,是過去以及未來的總和,我是神秘與日常之間的任意一點。我是循環。
我也是咒語,當你以靜默的眼神複誦著我,我的全部,當我們在各種的可能之中竟然也得到了全然的統一,你將也是咒語,我是昏迷,你是清醒,也並不一定,後來我們在凝望之中開始了泡沫化,海是愛我們的,海一向如此。而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