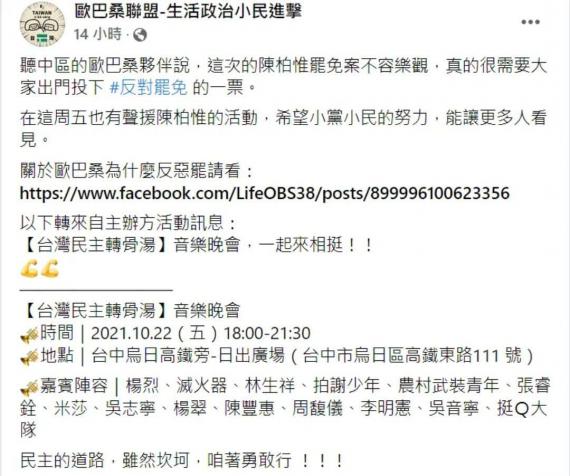「幹!媒體報導版面刻意縮小了」。
「三台電視也完全封鎖了」。
「大概只剩自立及首都早報的報導,但首都是新創立的報社,訂報率才剛起步。只剩自立早晚報可以宣傳」。「關心的恆關心,不關心的恆不關心,你能拿他如何」?
「照你這麼說,那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這件事,其實我們也不需出頭搞運動嘛,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好啦,好啦,沒時間答嘴鼓啦!講一些實際的突破方法,比較重要」。
決策小組面對運動困境時,通常會由吵架式的辯論,轉為場外抽煙尿尿方式解決。

新新聞封面1990.05
「我們可以用噴漆方式,在台北市各處噴上反軍人干政標語」。這個提議引起決策小組眾人產生興趣,也停止爭吵了。
「用什麼器具噴漆呀」?
「用剛出產的新產品—鐵樂士呀」,某愛好美術的決策小組成員,從包包裡拿出一罐像殺蟲劑的噴罐,然後在國家劇院空白的牆面上,噴上「反軍人干政」五個字,大家看的腎上腺素都湧上來了。

小蜜蜂噴漆大隊 1990.05.20
「這個好,攜帶方便,噴了就跑,量警察也不一定抓得到」。
「只是白天路人多,若被老芋仔或跟蹤我們得便衣特務,迅速通報警方,還是有可能被抓到」。
「看來要變成貓頭鷹,在夜間行動比較可行,而且是人少的子夜」。
「不是解嚴了嗎?應該沒有宵禁了吧?我們也順便來測試這個禁忌是否真的開放」?
「不錯耶,但是台北那麼大,我們只有500人,要噴哪裡呢」?
「地下道、公家機關圍牆或大門。千萬不要噴私人建築,免生法律糾紛」。
「那我們就把500人,扣除守住指揮中心50人,其餘平均分配四個大組來做,如何」?
決策小組找來台北市地圖,放在地上,大家圍成一圈,或蹲或趴盯者地圖看。
「範圍也不要拉太大,人員也不要太疏散,以便一旦被抓或出事,得有個照應」。
「如何照應?如果被賊頭抓呢」?
「被賊頭抓,那就得請台權會的律師團幫忙了」。
「若是被便衣或特務抓呢」?
「那就圍毆他,通常他們頂多倆人一組,我們裡頭一堆高中打群架出身的,順便練身體」。幾個決策小組成員,開始興奮地磨拳擦掌起來。
「那就不要通知媒體記者了吧?就說是老天顯靈噴的」。
「哈哈哈哈哈!這回答妙」。
於是,決定的四個區的行動起始中心,東區從國父紀念館開始;西區從西門町;北區從台北火車站;南區從台大本部。
各分組設負責組長及副組長,一旦有事,就打電話到支援中心,該中心派遣幾位同學,向熟悉的社運團體辦公室借整晚待命,譬如台權會。
於是決定了北區由范雲及台大大陸社等人領隊;東區由陽明醫學院等社團領隊;西區由東吳的蘇菲亞領隊;南區由台大大新社、傳真社等領隊。約定從凌晨00:00分準時行動。
在廣場的500個學生,興奮地不得了,有的人先鑽到睡袋補眠,有的像我一樣喜歡載妹妹夜遊習慣的,就決定先回宿舍洗個澡休息一下,快到子夜時再回到廣場上。幾位參加南區也想先洗澡的同學,決定一起共騎機車到我外頭租宿處休息。北師兩位沒辦法回宿舍的妹子,決定一起到我那兒洗澡休息。
一場彩繪台北,突破媒體封鎖大作戰,我們稱之為「小蜜蜂行動」,開始倒數計時。這是臺灣首度突破媒體壟斷的運動始祖。
●
洗完澡之後,趁公館附近還有一些麵攤還在營業,大夥兒決定先去飽餐一頓,順便喝幾瓶啤酒。夜半的台北,菸酒之下的革命熱血,簡直快要沸騰了。
快到11點,我們回到中正廟,各大組進行內部分工及展開地點劃設。我們建議先從地下道開始,每10人一組,負責一座地下道或人行天橋,如附近有公家機關的牆壁,且大門沒有值夜警衛的角落,就是作案最佳地點。
其實,大家根本不怕被抓,因為那是光榮的勳章,萬一因此入獄,想來也不會太久,反而可以「黑又紅」。為台灣犧牲,一切都值得,這才叫做「革命的滋味」。
其實,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促使我們腦中,開始產生各種悲劇的可能,與其傻傻坐在家裡被抓,不如做好「武裝革命」的準備,要死也要拖個陪葬的。什麼人生前途,生涯規劃,通通丟到馬桶裡,就當作沒有了。因為與其活在沒有民主的臺灣,還不如勇敢的死去。
子夜一到,中正廟近200部機車,全都後座載一人,按照各組先前規劃的作戰地點及區域,開始分頭駛去。
我這組10人,分配到羅斯福路直到中正廟這一段。地下道超多的,馬路上正在施工的捷運工地,很適合我們用S形繞來繞去,偶爾刻意鑽進小路或小巷道,目的是讓調查局或憲調組難以跟蹤。
尤其憲調組特務,都有基本打扮:
1. 平頭。
2. 身穿便衣或黑西裝,但不打領帶。
3. 腋下夾著一個牛皮紙資料袋,裡頭鼓鼓的,那是無線電對講機。
4. 屁股鼓鼓的,那可能是左輪手槍。
我們既然還沒學過擒拿術一類的武藝,自然還是學天龍八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段譽的淩波微步,逃往下一站就對了。如果真的被跟上了,就派2人負責引他們去下一站,我們就放棄那一站,直接跳棋般往下二站行動。引他們的人就暫時退出行動,在該站散步談心個一小時,然後回中正廟。
大約凌晨三點前,我們這一組把羅斯福路彩繪完成,也沒有人被跟。正要回中正廟,小組成員吳金治、台大政治系徐麗斐以及兩位世新的朋友,表示可以去公車總站,把公車大噴一番。我表示,這樣很冒險,那裡可能有人看守,不宜前往。但他們四人說趁天亮前趕快去噴,四點前一定撤離回中正廟。我其實知道擋也擋不住,於是就祝福他們行動順利。

1990.05.20 噴漆於公車
回到中正廟,就聽說才不到二小時,范雲那一組全被抓到警局,指揮中心趕緊通報律師前去保人。到早上四點半,那四位伙伴還沒回來。於是我載著北師的范曉玲,直奔公車總站。快到目的地時,遠遠看到那四人,旁邊還有幾位大人,雙手環抱於胸,兇狠地監視他們。
我們於是停下機車,佯裝散步靠近過去,四個人正在拿長刷子,沾上混有香蕉油的水,表情悲憤地一台又一台地刷乾淨。唉!即便我身上帶有相機,但不能使用閃光燈下,也無法拍攝,不然可以成為他們人生獨特的紀念照呀!
當然,洗完就沒罪了,四人筋疲力盡走出來,我們趕緊帶他們去喝個熱豆漿早餐。然後,討論復仇公車的方法。略微想好之後,就回到中正廟,向決策小組說明整晚戰績及下一步行動。
1990.05.04,台北市民一覺醒來,出門上班時,走入地下道或爬上天橋,全都傻住了。反軍人干政的訊息就這樣擴散出去。相信上午八時前,郝柏村在家中接到電話,應該把手上咬了一半的饅頭給摔到地上,桌上的豆漿也大概被摔離桌面。郝龍斌趕緊低頭喝他的豆漿,郝媽媽忙著叫傭人來打掃。
滿臉怒火的郝柏村,下令調查是哪些人幹的?憲調組長忙回報一份學生名單給仍身著軍裝的郝總長。

1990.05.20
攝影:邱萬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