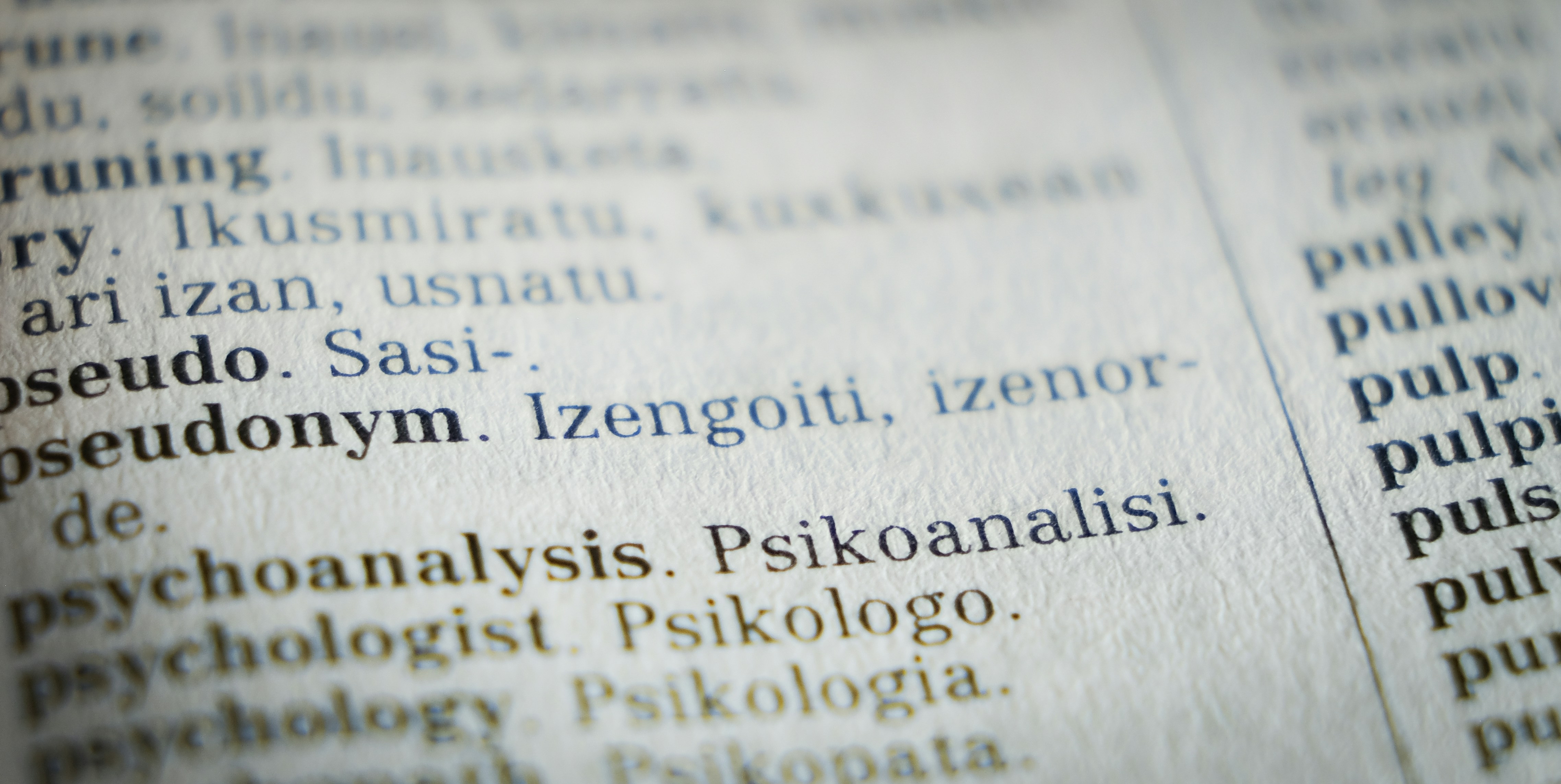「中文是怎麼學的?」
在學中文的第一年,我和當時尚未成婚的太太住在蘆洲一棟老舊公寓的頂樓加蓋的房子裡。如今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彷彿蒙上一層夢幻的薄紗。我們憑藉著僅如孩童般稚嫩的中文和些許英語,勉強維持著溝通。每天固定時間,她的iPhone會響起輕快的法語歌曲,為寂靜的空間帶來一絲活力。走出那間沒有窗戶、漆黑如夜的臥室,外面的天色依舊昏暗,讓人分不清是早晨還是夜晚。
「台北有沒有太陽?」
我隨口問道。台北那無休無止的雨和肆虐的颱風讓我驚愕,彷彿永遠陷入了無盡的雨季。她笑著回答「這裡就是這樣啊。」那句話中帶著一絲淡淡的寂寞。
當時的我,對台北那永不停歇的雨和猛烈的颱風感到驚訝。歡快的法語歌聲與豪雨的節奏格格不入,但我仍然得去上學。iPhone的螢幕上顯示著老師發來的訊息「今天有上課」,旁邊配著一個愉快的小熊貼圖。外面的陰暗天氣讓我懷疑這是否真的是早晨,但LINE上的小熊那麼陽光,讓我猜想應該是早晨吧。
每天早上都會前往文化大學的華語中心。順帶一提,文化大學的華語中心位於大安森林公園附近。「你是在山上上課嗎?」這樣的問題我被問過無數次,而這個問題是無法逃避的,哪怕我回答「我是台日混血」。太太則每天早上搭捷運去上班。我們同時出門的話,剛好可以趕上我的課和她的上班時間。我討厭早起,總是像颱風般快速準備好,穿上我喜歡的Dr. Martens當雨鞋,匆匆衝出家門。

(紅綠燈倒了,但學校還有上課?這讓我感到驚訝。)
儘管睡得很晚,我們還是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在早餐店一起享用早餐。雖然晚餐每天都是我們自己做,但對於討厭早起的我們來說,做早餐根本不在選項內。原本沒有吃早餐習慣的我,因為「她要吃」,所以每天早上和她一起吃早餐。太太一直很喜歡美而美。第一次她帶我去美而美時,那樸素而懷舊的氛圍讓我驚訝且感到溫暖。在日本,這樣的地方或許不會選來約會。可以說是懷舊、復古、可愛,也可以說是髒舊。但她告訴我,越老的店越好吃,至今她仍常說「傳統的早餐店最好吃」。
那時的我,對台灣生活充滿新鮮感,再加上中文不流利,每天變著花樣點各種餐點。
「玉米是什麼?」
「corn」
「玉米漢堡和玉米吐司有什麼不同?」
「麵包種類不一樣。」
看著麵包和食材的搭配,就像尋寶一樣,我一個個詢問菜名,逐漸進入中文的世界。雖然看似菜單很多,但實際上菜單並沒有那麼多,但這種尋寶的感覺讓我很開心。而最吸引我的是奶酥厚片吐司。我喜歡厚切土司上黃色甜美的奶酥,經常點它。
年輕時,我在日本的美式披薩餐廳工作。那時製作的卡士達醬披薩深受歡迎。卡士達醬的甜滑就像青春的一頁。製作卡士達醬時,火候非常重要,火大了會變得乾燥,無法使用。雖然味道相似,但口感差異使得它不被日本人接受,失敗的卡士達醬會被店長斥責。
然而,奶酥吐司彷彿驕傲地說「我不是失敗品」。早餐店裡不會響起店長的怒斥聲。
「阿姨做失敗了嗎?」
「????」
我問太太,她卻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那味道每一口都讓我想起青春時光,那段對音樂和興趣充滿熱情的日子,即使在店長的怒斥下也勇往直前的記憶隨著奶酥的甜味在口中展開。奶酥的甜味和我青春時期的甜美重疊,乾燥的口感則讓我聯想到社會的現實和不愉快的回憶,心情複雜。但我卻喜歡這種複雜的感覺,只需30元便可買到。
當被問「好吃嗎?」我總是回答「不確定好不好吃,但我喜歡。」一邊走在通往學校的路上,一邊用比父母之愛更甜美的奶茶,靜靜地沖淡那複雜的情感。學中文不像奶酥和奶茶那麼甜,但我終於能在台灣生活。
之後,我回了日本,四年前再次移居台灣,這時我的中文學習已達六年。由於有機會出版第一本食譜書,我也參加了一些廣播節目。雖然在日本也上過廣播,但在台灣是第一次,當時非常期待。平時和太太百分百用中文交流,以為應該沒問題,但事實並不那麼簡單。錄製廣播時,我緊張得詞窮,幸虧主持人幫忙,才沒讓節目冷場。錄製時,主持人甚至提醒我「別一直看太太」,那六十分鐘就像一場聽力和口說測驗。
「要是有人能替我說就好了。」
我心裡想,完全沒集中在聽力測試上。回憶起高中時英語聽力測試中也有同樣的想法,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一直說的是只有太太聽得懂的中文。」節目錄完,我無法填寫答案,只能逃回家。
那之後,沒有收到試驗結果或不合格通知,也沒有再收到邀約。因為之後兩年,我沒再出版新書。當意識到自己中文會話不流利時,無力感勝過了悔恨。
「原來我還沒站上起跑線。」
然後,我感到悔恨。這裡是台灣,不必勉強邀請日本人。我用全糖珍珠奶茶安慰自己。

27歲時,我在淡江大學華語中心學了一個月,之後在文化大學學了八個月,輔仁大學學了三個月。YouTube上有很多「一個月就能說」的影片,但我學了一年,發現自己沒這天份。15歲和20歲時也試過學中文,但在日本沒機會用,很快就放棄了。母親曾溫柔地說「你學不會中文就別勉強了。」現在自己當了父母,我才明白「母親,您應該更努力。」
雖然廣播錄製一塌糊塗,但日常對話卻能應付。「中文是怎麼學的?」這樣的固定問句和隨之而來的「中文很好」的恭維,剛開始讓我很高興。
但每次聽到相同的話,漸漸厭倦,甚至覺得煩。有天我回答「我是台日混血。」對方立即接受了。「難怪啊。」這瞬間,我感謝已在天國的母親。
「每天早上喝紅茶,因為我是英國紳士。」
「我愛法式吐司,還配酒喝,因為我是法國人。」
現實中,也有愛喝咖啡的英國人和不愛法式吐司的法國人。同樣的,回答「台日混血」就會被自動理解為「會說日語和中文」。多麼便利卻又殘酷。
時光倒回到我32歲,學中文已經五年。當時我剛開始做YouTube。語言天份差的我,經常收到「別說中文」「聽不懂你在說什麼」「用日語說」這樣的評論,就像基隆的雨不停地落在我身上。一年後,出了食譜書,上了廣播節目,結果卻如前述般慘淡。我意識到必須更努力學中文,不能再用奶酥和珍珠奶茶放縱自己。

之後,我並沒有付出血淚般的努力。如果問我是否付出比別人多的努力,也不是。但比別人花了更多時間。結果是,我現在只需回答「我是台日混血」,就能輕易避開「中文是怎麼學的?」這個問題。
當疫情結束我能回日本時,我立刻去了母親的墓地。那個溫柔放棄我學中文的母親,在墓前我不自覺用中文和她說話,感到心裡一陣溫暖。母親日語不太好,或許用中文能更多交流,也是我學中文的原因之一。想著母親是否也在美而美吃著奶酥吐司,上次掃墓沒問到,下次要記得問。
現在的我,能點無糖飲料了。但每次吃奶酥,我都會想起母親放棄我學中文的那天,和店長怒斥聲響徹的廚房,這些回憶不再那麼糟。雖然我更喜歡卡士達醬,但寫完這篇文章,我依然感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