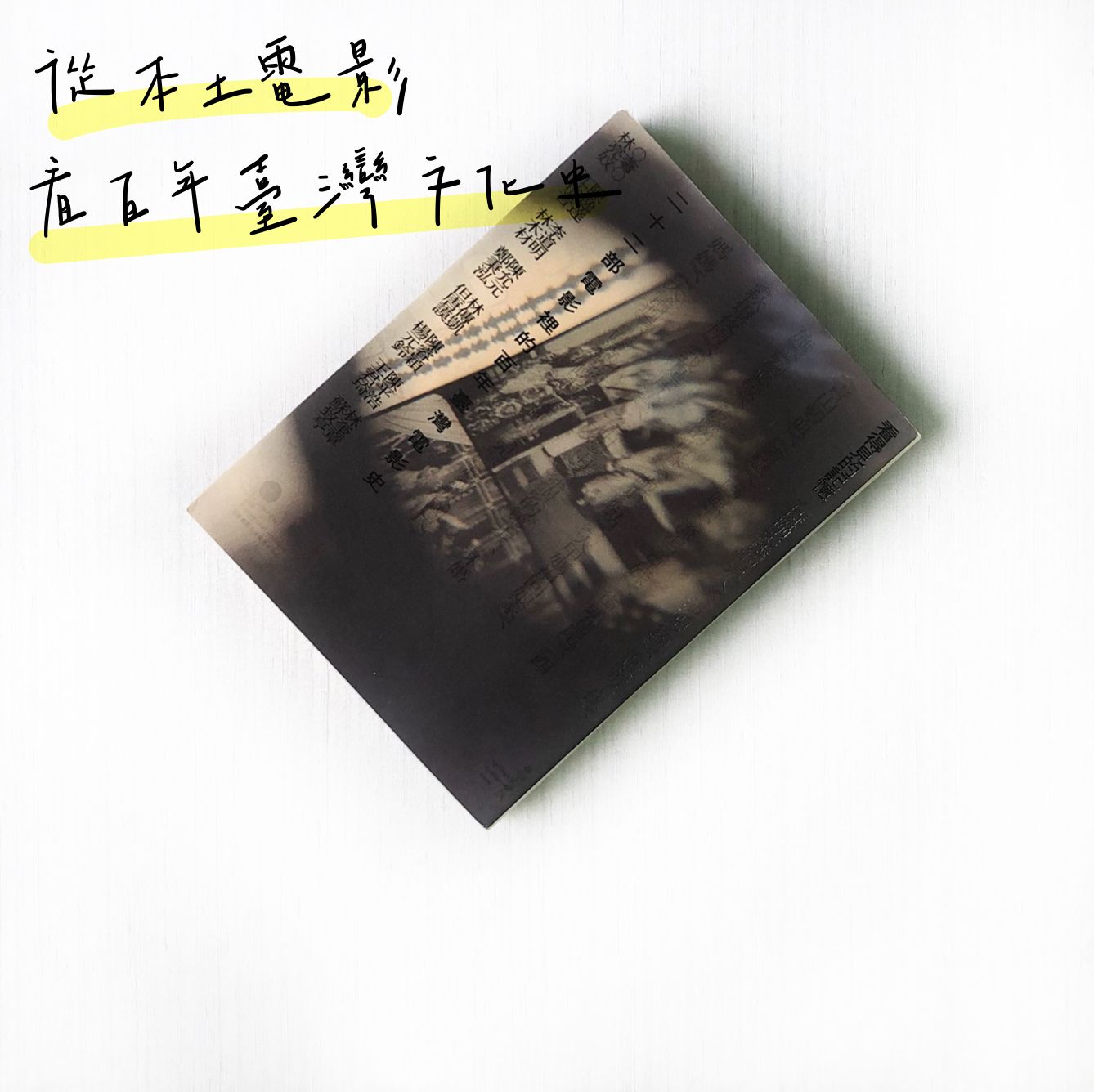聽聞《聽海湧》上架 Netflix,我開始挨家挨戶轉知親朋好友。我知道這是一齣難過的故事,也知道忙碌的生活裡,沒有人想自找罪受,讓自己更加痛苦。
但是這個故事,我們需要它。
我需要它。全影集自今年 8/17 在公視首播起算,已公開放映兩個月之多。關於本劇的各種細節探查和技術討論,除了在官方推出的紀錄片《漂流之海》可獲知許多寶貴資訊以外,也已有不少影音和文字類的劇組訪談。
所以在這裡,我打算從個人的生活經驗出發,聊聊我所看見的「聽海湧」──是我們終於伸出雙手,掬起了這片海,才讓浪聲得以湧動。

填補縫隙,是為了理解另一個人
在《漂流之海》中,擔任本劇歷史顧問的政大歷史系教授藍適齊說:
「(歷史研究)我們要保持中立、要保持客觀,可是這絕對不是完整的歷史,因為我們都知道在歷史當中,你我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都有情緒,我們都有情感,而且更重要的是,情緒跟情感會決定我們的行為。」
繼續往下談論之前,我想先提及兩個名詞:「大眾史學」與「歷史寫作」。
大眾史學:依據周樑楷教授的定義,包含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的三個意涵。(引自《歷史臺灣》第8期:大眾史學專題.主編序)
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年紀,或是更年長(講得自己很老),看到這組關鍵字,很快地就會想到「故事 StoryStudio」,一個於 2014 創立至今,專門分享歷史知識的新媒體。十年過去,也許以時間來看不那麼「新」了,但他們確實為往後開啟一個全新的歷史檢視角度:歷史是寫給所有人看的。
2016 年的《人社東華》第 11 期內,同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彭明輝受訪時言:
「受比較多留美學者的影響,靠向社會科學,這樣的發展,我個人認為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史料無所不用其極,研究的主題千變萬化,鉅細靡遺,但書寫的形式只有單聲道(Mono)。」
遺憾我沒有能力去驗證這些脈絡是否正確,關於文內提及臺灣的歷史系教育缺失書寫訓練的這一塊,很期待有相關經驗的讀者和我分享現況。
在這十年裡,不少人隨之握起歷史的筆,而社群媒體也成為助力,我們因而得以透過網際網路,學習刻劃自己的時間。很多的現在進行式於是能被及時記下,聲音再微弱,也不必等待百年即有見證。
這是「大眾歷史」令人感慨而樂見的變化。我們學會了成為自己的記錄者;而「歷史寫作」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根基於既存的事實,以有意識的敘事,去呈現一個想訴說的主題、價值、變遷或人物故事。
但相對地,資訊過於分散、破碎的結果,以及大數據抓攏不同群體的方式,也讓每個人心中的歷史愈來愈難撼動。
吃資訊需要時間,消化成論點也需要時間,而我們畢竟只有一雙眼睛,五百種解釋裡,只能選擇相信有餘力捍衛與辯證的那一種。
為此,我們更加需要一段引人入勝的、經得起推敲的、能夠承載時代又不摒棄個人的,好的故事。
再引一段藍適齊教授於今年 10 月 9 日的公視座談會演講時,分享的觀點:

「我們看了這麼多歷史人物的故事,我們什麼時候知道他們長什麼樣子?我們什麼時候知道他們生氣的時候是什麼表情?可是,一旦從歷史取材,成為電影或戲劇之後,因為有聲音,有影像,其實它能夠呈現的歷史情境,事實上可能比文字能夠呈現的,還要更貼近真實的生活。」
我很難忘記的一段史料分析對談,是他們在審視一份國際軍事法庭的紀錄書,泛黃的紙頁上,以打字機謄寫著數名被告。
大寫的字母和拼寫方式,一目了然的日本姓名,紀錄書的副標題也闡明 Japanese War Criminals(日本戰爭罪犯)──「可是他們都是臺灣人,」藍教授說:「只是他們被要求用日本的姓名。」
用一個陌生的名字死在戰爭後的戰場上,是什麼感覺?這彷彿質問屍體一般的問題,沒有人能知道答案,我們只能猜。
編劇透過史料去猜,演員透過劇本去猜,導演透過毛片去猜,觀眾透過畫面去猜。
行刑的那一刻,無論是絕望或解脫,早就都在異國那座簡陋的絞刑台上休止,可是經由戲劇,而能夠模擬現場,去虛擬出一份真實的痛苦。
第五集開頭,在軍人的陪同下,台籍日本兵──精確點的說法是日籍台灣兵、台裔日本兵、台灣人日本兵,滿溢立場選擇的文字遊戲──拉扯絞刑用的繩索確認結實度,一扯,讓人體變成屍體的騰空地片轟然下墜。
他什麼都沒說,就盯著地板上的洞,在黑黝黝的夜裡。

我們想像自己成為他,也在那個草木碎黃的季節裡,用盛滿末日的眼睛,去凝視一份從未預想過的終結。
我們也想像自己是持槍旁候的澳洲士兵,看著一個必定罪惡的囚犯,泛淚的眼神裡有落魄的恐懼。
我們還想像,那顆埋在洞下、由下而上拍攝他表情的鏡頭,是我們來自未來的回視。
無數的「為什麼」和「我覺得」如同撞球桌上的圓球一樣四處滾動、碰撞,空白的台詞讓一切無從解惑,但失語本身似乎就已經是答案。
──在沒有影像的時代裡,這是史料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是用填補史料的縫隙,努力去了解一個人。一些曾經活過的陌生人。
已經習慣用標籤展示自己的現今,就連在日常交往之中,都很可能拼湊出失準的認知,於是我們對彼此想像破滅、疏離,又跟別人建立新的關係,快速親近又遠離。
如果你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那便能明白,從零到有地去靠近一個陌生人,甚至是一個再也無法言語的人,這是一段多珍貴的歷程。
能共享這份理解,共享這段人生──我們何其有幸。
側寫未解的世代失落感
全劇定調在 1943 到 1946 年,太平洋戰爭停息,爾後一場軍事法庭開始,倒敘地鋪陳新海三兄弟在戰俘營的最後一段人生。
我想盤點幾場令我印象深刻的戲。
首集〈黑鳶〉震撼頻頻,最難忘是新海輝站在田中指揮官和羅領事之間當口譯,成為言語和情緒的容器,用一腔來由不明、無處發洩的憤恨,噴出「我是日本人」的深切自認,警鐘般想把自己擺正,卻沒料到日輪的投影卻愈來愈歪斜。

二集〈赤陽〉承接懸疑之處,補述日本律師和澳方審團的立場,新海志遠和羅領事的對證──那甚至稱不上攻防,僅是單方面的指控與贖罪般的全盤接收──完美收束了悔恨交鋒的起點,連帶揭開往後每一組罪與罰的真相。
三集〈強風〉寓意戰情與審判情況都急轉直下,田中指揮官跛著腳上下臺階宣達事令的背影,從最初用自摑以身作則的堅定指標,在連夜趕製、卻又一朝令毀的新起降場上,他無言的身影顯得荒唐而渺小。人們意識到,「無常」將直指死亡,不再有轉機。
四集〈侏儒象〉的母子象,起初暗喻領事太太母子的處境與情感,至此已然成為某種守護的概念。錯縱的劇情線中,每個人都在拚命逃生,尋一條不見亮光的活路。新海木德遭定刑後,奔逃向海的長鏡頭,對美術和質感師來說是巨大的考驗,最終成功給了淚水潰堤的時間。
終集〈海湧〉,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三方對質的法庭戲是通篇的最高潮。整整二十分鐘,每一個演員都徹底臨在那個審判現場,我們都彷彿被往昔附身,用靈魂去承受言語的搥打,在否認與否認之間來回撞擊。發現每個人都受盡苦,卻沒有人能被徹底憎惡──那麼這滿腔的酸楚與痛恨,又該朝何而去呢。

最後一集的法庭戲,我抱著膝蓋哭得泣不成聲。
那時我彷彿分裂了一部分的意識出去,飄浮在半空,很旁觀地看著自己被難過淹沒的失控模樣,心想,為什麼我會這麼激動呢?這故事發生的時代,距今已然八十年(或者說,也才八十年),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有所體驗,我的祖父母輩彼時頂多剛出世,對健忘的人類來說,都是遙遠的歷史。
新海志遠撈起槍,對著雙眼無神、表情平靜的領事太太咬牙開槍時,我為什麼會這麼痛呢。
新海輝站在一列被告當中,聽著澳方與日方激烈辯駁如何將戰爭歸責,低頭垂目默默滴淚時,為什麼會這麼痛呢。
新海木德睜著白得嚇人的大眼,遵令揮下硬實的木棒,學著長官一棍棍痛打戰俘時,我又為什麼這麼痛呢。

細數完這些精細的場面與情感,我發現每一幕每一句裡頭,都有著似曾相似的徬徨:人們試圖在亂世中像緊抱一根浮木般去抓住信仰,卻發現懷裡的只是搖搖欲墜的空口白話。
信仰崩壞的那一瞬間,記憶隨之破碎,新海志遠於是在證人席上向所有人逼問,自己在戰俘營這一年多、牢獄裡的十年時日,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維持最後一絲理智,努力保有混濁的人性。
三兄弟中,一向將親日立場踩得最硬的新海輝──我想在這裡該叫他劉榮輝了。劉榮輝低著頭沉默不語,淌下淚。
那是令人暈眩的一滴眼淚。
不只是同情,也不僅因心疼。那滴淚水穿越畫面、穿越劇本、順著南風吹過來,零零落落飄在這塊扁舟般的島嶼上。過去無法言說的迷惘,此時此刻與現在重疊。
「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原來,婆羅洲上的戰俘監視員們想要相信的,和現在的我想要相信的,其實是同一種未來──我們心中有著橫跨三個世代以來,仍然未能解決的、相似的失落感。

1946 的你,與 2024 的我
為了幫助描述這份失落從何而來,我想我得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成長經歷。
如果聲稱自己是變革的一代,恐怕過於自大了,國內最激烈的社會運動,早在我出生之前便已落幕。然而,在生活與認知上的變革,才正要開始。
按常見的說詞來劃分,我這一輩算是Z世代,也就是 1990 後到 2010 前這段期間出生,有一說法又稱「數位原生世代」──在我國小的時候,智慧型手機和社群網路正式普及,開啟不分老少人手一機的生活方式,再也回不了頭。
人們練習如何把握自己的話語權,而和生活零時差的網路世界,同時滋長起最初型態的社群焦慮。不過,那時的論點還不太會一群一群聚集起來,仍然得靠本就緊密的社群彼此維繫,而最大宗的聲響,依然來自聲光無限的傳統媒體。
開始認識臺灣史之後,才慢慢驚覺這和日本時代下,以極高行動力印誌登報、傳達訴求的臺灣人如出一轍──那股「把聲音傳出去」的渴望,從來都沒有被消滅。
我求學時方用起不久《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用的最多是九○暫綱和九二課綱,和上一代最大的差異是,臺灣史開始獨立成篇。這改動並沒有讓我變得多愛歷史,該睡照睡,為了應付考試而死背。跟大多數學生一樣地生活。
渾噩度過的時日裡,彼時唯獨日本時代的篇章背得最全。因為我喜歡日本動漫畫嗎?還是因那是一個不遠也不近、剛剛好的時代?
或者,是因為提及那個時代的人時,我看見更多在編年史之外的聲音,一些吆喝、嘶吼、笑鬧的聲音,透過充滿生機的創作,一幅幅一頁頁一本本地從圖片上演出來。我是被那時代蓬勃又轉瞬的靈光所吸引。
也許都是,也許都不只是。
「數典」的時候,我的心思慢慢走過那好幾冊背不完的教科書,國籍與認同在文字裡流離,總在快感受到指引時戛然而止。從是成為了不是,又從不是被命名為是。最後的最後,停在一個未明的進行式。
論述總是這樣:
我們是優越的,但不被認可;我們有名字,但只能由別人決定怎麼稱呼;我們要為自己驕傲,但是要習慣這份驕傲是孤獨的;我們是偉大的想像的共同體──可是要想像成什麼樣子,別問,照題目寫就好。

羅進福:「我看日本人把你洗腦洗得很厲害,讓你甘願做一條狗!日本人教你翻譯你就翻,日本人教你殺人,你殺嗎?」
新海輝:「我吃日本米,讀日本書長大!私は日本人であります!(我是一個日本人。)」──第一集〈黑鳶〉
看到這一幕時,你很難不心想,我和新海輝又有什麼不一樣呢。讀過的書、聽過的音樂、讚過的貼文、滑過的影片,構成了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然而,書裡是一組敘事,書外又是一組敘事。社群上是一個社會,社群外也有一個社會。新聞裡是一個世界,新聞外又是另一個世界。
感受到矛盾的時刻,總比暢通有理的時刻更多。我不知道該如何判斷,只能四處看,到處聽,蒐羅了又散去,聚集了又捨離──為了去解讀一條我看得懂的人生路徑。
解讀。解讀。解讀。

威廉.柯爾:「如果沒有要處決俘虜,為什麼你要拔出軍刀威脅下屬?」
高橋莊治郎:「北川國夫拔出軍刀,並不是要砍殺下屬。軍刀對日本人來說,是武士道的象徵,是象徵著義勇奉公的精神。新海輝因為是台灣人的緣故,所以誤解了長官的意思。」
威廉.柯爾:「不要再誤導庭上!命令是從田中徹那邊下來的,他們每一個人都知情,全部都是共犯!」
沒有人告訴過我們,如果自己所解讀的內容,有一天開始發現好像讀錯了,該怎麼辦。如果我讀的都是對的,革命又為什麼會發生。
我用的稱呼其實不對嗎?我下了有罪的決定嗎?我也成為了讓世界錯誤的共犯嗎?──沒人想成為落敗的一方,但在被時代巨輪輾壓的時候,脊骨碎裂的那一刻誰都會痛。
從在螢幕前學著家人的樣子唾罵,到綁上布條走上街頭,再到有時在、有時不在路上,用自己的態度決定該朝隊伍靠近或遠離,慢慢長出自己的想法,慢慢學會在一些場合沉默,一些場合昂揚。
將這一段路走到今天,不多不少,正好十年。
究竟算快還是慢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只是我一直跟在他們後面,自私地幻想我們要一起去同樣的地方,但其實我跟不上他們的腳步。到了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 我們本來就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
──傅榆《我的青春,在台灣》
-
即將離開大學的倒數第二個學期,我拉著朋友偶然修了一門大眾歷史寫作課,理由是我想有個正當理由盡情寫東西,順便湊個心甘情願的學分。不過那堂課似乎是第一次開,大碩合辦,除了我們之外大多是該系研究所的學生,難免皮皮挫。
課上導讀了很多不同的非虛構作品,我們讀日記、讀相片、讀職業,一些很數據的東西經過書寫,漸漸變成了想像得出來的生活。
沿著教授安排的主題一路往前讀,然後落在一本書上。
我在這裡遇見了《終戰那一天》。
一兩年後的現在,《聽海湧》出現了。
滾了很久很久的生命簡史的輪,彷彿在此終於有所段落。
過去曾經的徬徨、躊躇、不安和焦慮,那些從文字裡揣想的面容,終於在螢幕上清晰,在新海輝受刑前永別的關懷裡,凝成新海志遠的淚水滑落。
「回去台灣,好好過生活。」
1946 的你,和 2024 的我,或許有什麼地方仍然一樣吧,我想。
可能以為自己是選擇的一方,卻常在時代的轉角跌跤,不得不躺下。天空和地面變得顛倒,頭下腳上地讀出一串看不懂的質問。眼淚掉落地面的時候,因為天氣太乾太熱,很快就蒸發了。
戰爭已然落幕,可歷史沒有和解。不論願與不願,我們即是故事,即成歷史。
但是沒關係。
好好過生活──用盡一生,去解讀這幾個字,就是對時間的誠懇書寫。

本劇相關圖片取自《聽海湧》臉書粉絲專頁。
介紹就到這邊啦,希望你也能喜歡上這部作品,一起留言聊聊你對《聽海湧》的感想吧。
歡迎加入我的沙龍,看更多動漫畫、影劇的心得評論和生活書寫;也推薦追蹤我的 Instagram,隨時更新不同的資訊分享和生活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