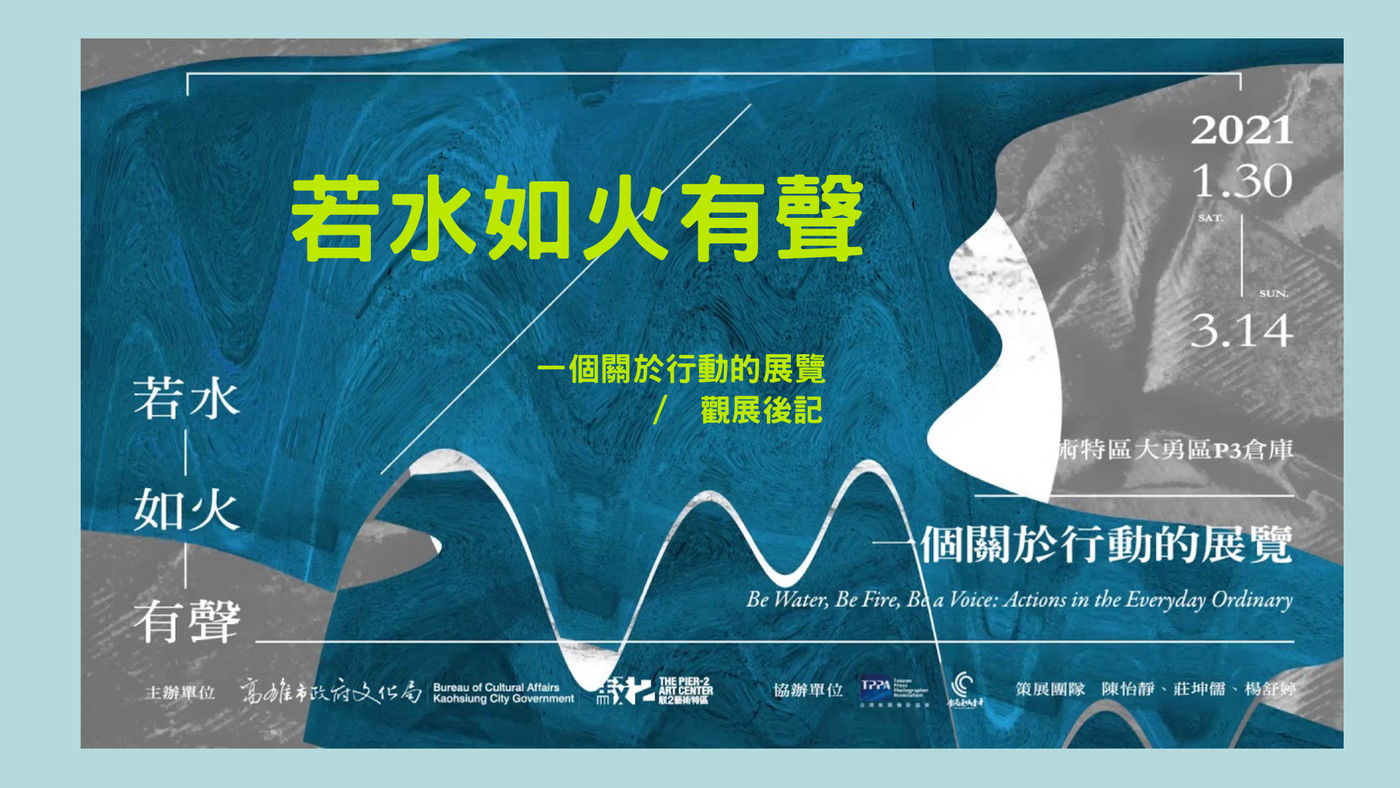也許這會是最後一次了,畢竟我們都必須學著長大,人類終究不屬於海。海浪反覆進退,我們的年少也是。於是我們踏遍山海,尋找聲音,在青春的斷裂與相連,持續行進。

2021年12月18日,踏入二十歲的第三個月,一個值得秋冬,無關痛癢的季節。三年前守在電視機前看開票,儘管同婚公投落敗,一年後他們也能夠彼此緊緊擁抱。我們應該相信的,似乎是世界會慢慢變成我們所寄望的樣子。
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法案的國家,如果我們都以身在這座島國而自豪。如果兩個相愛的人,毋須再被限制。如果我們都能相互靠近,無關信仰。
四年前和友人C在張曼娟老師《當我提筆寫下你》新書發表會時認識,由於我們是全場年紀最輕,被點上去看誰舉手最快。會後,我匆匆忙忙地用背包裡的紙條寫下聯絡方式,遞給了C。我們來自不同的城市,那是16歲,單純地只需要擔心會考的時間。
粉色柔軟,將一切溫潤返還,藍色的浪一波波上岸,層層白色浪花拍打,我們迎著海,期待踏浪。海浪是有聲音的夢,迴盪在積累千年的岸,每一次生死之間的跳躍。靈魂像是水面上的粼粼波光,順著光的反射蔓延遁入天際。
2014年3月18日,太陽花學運。13歲,正逢私立中學入學考,隱約記得有人衝進立法院,太陽餅和香蕉,大人們說他們很壞,阻礙國家發展,我不懂為甚麼新聞每天都在播。只覺得他們翹課衝進立法院,應該真的是壞學生。他們成為了課本上的人,成為考題,我一次次選出正確答案,關於反服貿、關於學生運動,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紅色的勾,我以為這些選項,便足夠捍衛正義。
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看著年紀相仿的中學生血流如注的模樣,才體會到內心一陣陣翻湧。和同學縮在教室角落,看著即時新聞一同憤怒,卻又無能為力。那時我已經知道九七回歸,知道承諾五十年不變。
我拿著一則一則新聞畫面巴著母親不放,我告訴她:「你知道他們又……。」,她說:「妳考試是都可以考一百了嗎?這不關妳的事。」大人的世界總是習慣告訴我們「沒有關係」,受委屈的時候,想努力說話的時候,其實只是要我們學會練習忍氣吞聲地過日子。
夜晚總也有月光孱弱的時刻,這時候海從藍色變成了黑色。
剛滿十八歲的秋季,準學測生,第一次瞞著爸媽走上街頭,穿著黑色T恤與長裙,參加「護台抗中 牽手撐港」的遊行。我和在校刊社認識的學弟D,拿著手板,捧起支離破碎的詞語,向路人解釋事件經過。
市民廣場遊客來來去去,建立自己的島,車水馬龍的街道,集會的人們穿著黑衣,綁上亮黃色的布條,沒有人能夠知道,海的另一端究竟何時會被照亮。
活動開始前,來自香港的姐姐,雙手仔細撫摸傳單,讚嘆紙質很好。一名身高不高的中年婦女經過,說她也是香港人,不斷地向我們道謝,最後和姐姐抱在一起哭。在場的人,看著她們就這樣哭了出來,顯得手足無措,只能拍拍他們的背給予安慰,我站在旁邊靜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其實我們都清楚吧,事情已經不會更好了。
如果今天的擁抱是光,明天子彈發射擦出的火花也是。
「你願意和我一起支持香港嗎?」
一次次遞送傳單,但畢竟是海峽另一端的事,換來的是一次次地拒絕。我甚至開玩笑地跟學弟D說:「以後看到別人在發傳單,還是乖乖收下好了,他們好可憐喔。」畢竟日常,總是重複地碎裂又重組,也唯有我們親手體會,才能有所感受。人性像是一道道暗流,我不斷觸礁、挫敗,然後在矛盾裡沉淪。
我們總是生存於忽明忽暗的世界,試圖去接受與抵擋,所有事物對自身黑暗的入侵。反送中運動過程中有句口號:「Be water.」,意為要像水一樣流動,既柔軟又剛強。
我不確定溫柔是否能治癒一切,但我確定香港人的不會。
隨著夜色籠罩,人們聚集到廣場中央,有隻身一人、有情侶,甚至有家長帶著身高及膝的孩子,不分老少、性別與國籍,各式各樣的人們,唱著〈願榮光歸香港〉、〈你敢有聽著咱唱歌〉,喊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對粵語一竅不通的我,看著羅馬拼音歌詞,一同唱著,無法全然了解歌詞意涵,感受到屬於一個世代的激昂,我知道我們身處於時間。
僅年過二十,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所有海誓山盟,不過空氣飄散的霾,是白加黑形成──陰鬱的灰,灰是所有無法破解且定義的邊界。塵埃也即便能夠折射熠熠星火,仍無法照耀宇宙。
回家後,我鼓起勇氣告訴母親我去了集會活動。
「以後不准去香港了,轉機也不行。」她說,沒有一絲猶疑。我對香港東方明珠的繁榮,甚至是中國廣袤地域的大山大海,文學裡的描摹,又何嘗不嚮往有朝一日能親眼目睹。現在,卻變得如此遙不可及且危險。
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只記得在現代小說概論的期末報告,有別於多數同學選擇張愛玲、白先勇等經典名著,任性地選擇了李維菁的《人魚紀》作為主題,我信心滿滿的交出報告,意料之外拿了很爛的成績。我不禁想著,人魚會不會嚮往回到陸地?如果回到陸地會失去聲音,她會不會甘願放棄?
想起〈山海〉的開頭是這麼唱的:「我看著天真的我自己/出現在沒有我的故事裡/等待著我的回應/一個為何至此的原因。」
比起草東沒有派對版本嘶吼的〈山海〉,其實我更喜歡好樂團的翻唱版。「草東像是他殺,而好樂團像是自殺。」Youtube的留言區,有人是這麼說的。
一年之間,《國安法》通過、眾志黨解散、媒體被追捕搜查,斷斷續續地看著香港人死去、被逮,事情越來越失控,城市的氣息隨著聲音漸弱。
高中的時候反覆想要死掉,跟很多朋友說過:「記得把我的骨灰灑在海邊。」,然後因為反送中,告訴自己要變得更強大才能守護某些過分在乎的事情,關於我,似乎有好轉的跡象。但直到意識到掙扎僅是徒勞無功,又再次載浮載沉,拚命說服自己要練習長大。
升大學,明明是更靠近公投權的日子,開始能對社會有所選擇,高中時青春的年少輕狂被無奈的情緒沖去。社會運動總是要承受更高的情緒風險,於是我選擇走向陸地,避開所有波濤,不再高舉標語吶喊,選擇性漠視新聞中的疼痛,捨棄自己的聲音。
19歲的我,跟18歲一樣拚了命的想逃,一樣如此易碎。於是,成為在山海間不斷跳躍的人。年幼的我們都曾立誓,不要成為討厭的大人。但如果我們連自己都無法保護了,憑什麼要為了別人奮不顧身?
意識到自己長大,不再為任何事物感到憤慨,社會化的凝視下,安靜地長出雙腿,成為更完整的人,變成社會理想中大人的樣子。
離學校不到十分鐘的南鐵東移事件迫遷戶黃春香家,教授在課堂上激動地描述事件經過,關於警察如何驅離民眾、關於政府如何脅迫居民。系上同學們紛紛拋下課堂前往聲援,只為了發出自己的聲音。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不再唱歌了,旋律已然遠去,自始至終我都未曾靠近,甚至還告訴同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即便是政府。」,又暗地裏感到愧疚,認為自己不該如此冷血,每天用讀書與寫字塞滿生活。
直到看到一直很關心環境議題的C,分享藻礁議題。或許是因為對C的信任,我久違地在臉書上轉貼訊息,默默和親朋好友收集連署書。一向被視為進步的環境保育價值,一波又一波地被沖散,「國民黨支持的不用看啦。」、「核廢料堆你家嗎?」、「通通得肺癌啦。」。
「非核、減煤、救藻礁。」早已是公投理由書裡明確聲明的事。我很像能理解,為何當初大人們要如此事不關己。
某次從台南返家剛下高鐵要轉乘公車,利用等公車的時間和C傳訊:「標籤又慢慢出來了,感覺會不知不覺被視為某些政黨的打手甚至是棋子,現在還好但以後呢?出社會後相關紀錄都會被檢視。」
C回覆:「對啊,我今天跟路人聊天,他也這樣警告我。」
社會像是消波塊,在綿長的海岸線上,醜陋地宣示我們不該越界,但我們卻不得不向前。各式各樣的政治陰謀論相繼湧出,誤觸漁網機關的魚,不斷地逃竄且無所適從。
2021年3月18日,三一八學運後的第七年,珍愛藻礁公投案連署書送件,連署提案通過。我在課堂上,偷偷地在桌上架起手機,看著C在記者會上發言:「謝謝大家願意在這樣民主的國家、自由的時代,願意相信我們有很多溝通和對話的可能。公投之所以珍貴,是在投下票那一天以前,不同觀點和立場都有被聽見的機會,讓議題更多元,讓公共政策還有社會更加完滿。」
C找我協助進行整理各方論點,讓民眾得以在公投之前,獲得充分的資訊後,再做出抉擇。我答應了,順道找了學弟D。我們共駛一艘船,在龐大的資訊裡面對波瀾,練習平衡正反方論點,練習同理。
某日,我和C一同去看了《複眼人》的舞台劇,一部由吳明益同名小說改編,關於海洋、山林與環境開發的舞台劇。進劇場前一天,看到臉書上出現許多關於第一天演出的負面評論,我和C抱著忐忑的心情進入劇場。
然而當天欣賞完畢後走出歌劇院,C說道:「是不是有時候因為大家不願意去面對現實,所以才會覺得它難看。」。
晚上我們和學弟D約了時間吃飯。昏黃的燈光下,即便C和學弟D第一次見面,我們卻像再平凡不過的學生,聊著學生愛情、校園生活,有說有笑。所有繁雜、破碎的紛擾,隨酒精揮發,我們又再次回到最原始的樣子。不管是我、學弟D與友人C,或是系上同學,我們試圖回應世界,但回過頭來真正得到的是甚麼?
我其實並不為新聞媒體報導:「大學生颳起粉紅風暴」而自豪,隨之而來反而是更多社會對立的擔心與焦慮。
然後黃家被拆,同學們開始說,警察是壞人。
但我爸爸是名警察,他不是壞人。
回到學校,面對成堆的文件,書櫃上擱著一疊來不及發出去的連署書,想起學期初某堂課,因為對老師給的社會議題不感興趣,毅然決然在分組報告選擇了自己一組,報告藻礁議題。
因應疫情爆發公投延期,鋪天蓋地的疫情新聞延緩了我們的戰役。林薇晨〈粵語課〉寫道:「最後學到的東西或許不多/唯有一件事情難忘/當教師說:學習語言的第一件事情/記得發出你的聲音」。
離20歲只剩兩個月,我再次游向湛藍大海。
「他明白/我給不起/於是轉身向大海走去」,〈山海〉末句是這麼唱的,即便在海中迷途,或許會失去所有聲音,並化成泡沫。最後公投落敗,我們整理的資料也未曾刊出,海浪仍舊跟隨日子。
巨浪讓我們浮沉,海水在光的折射下,不斷地變換,願我們成為山川的顏色,包容所有風雨,於是成為水,成為各種形狀,彼此緊密,賦予自己一些勇敢的海域。
*此作榮獲第五十屆成功大學鳳凰樹文學獎現代散文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