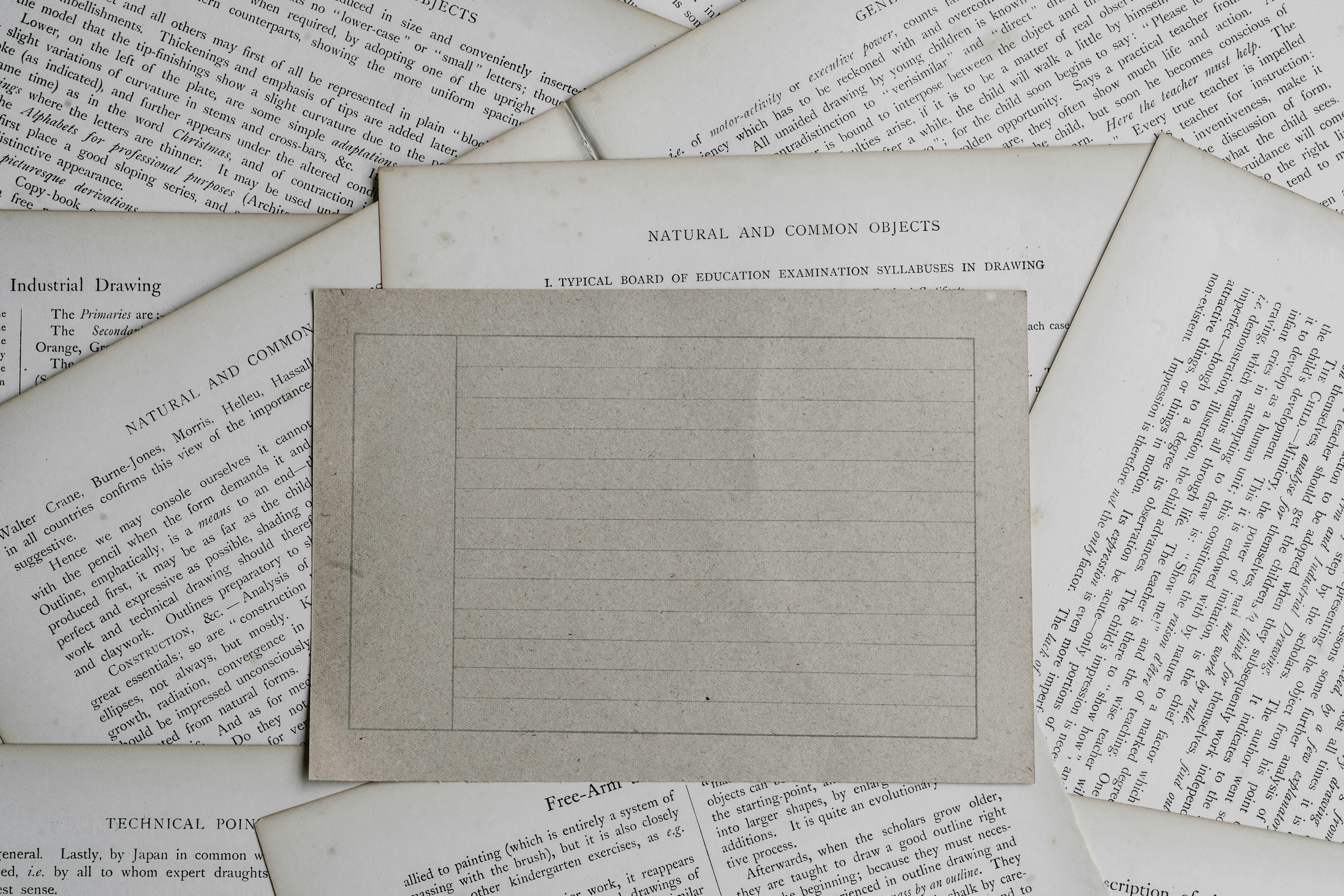老夫,是公司裡的本地書,大概民國四十幾年生的,也就是一九五幾年印刷出來的。跟我差不多年份出生的書,多是早期印刷廠印製。我的名字就叫《老夫》,外殼是精裝紅皮書,那紅皮之上的文字則是燙金字體。
我曾經也是風流倜儻的少年仔呢。
剛從印刷廠印出來時,有著鮮紅的外裳,若有光線,更可見紅裳外宋體字的流金潺潺。那時若有顧客買下我,翻開內裏,必定是純淨無瑕的雪白。當時我的同齡人,我們《老夫》一族都彼此戲稱「小潘安」。我們不老,少年正得意的呢。
然而歲月的確發揮了些它的一丁點作用,被印刷出來後,我們被存放到牛皮紙包裝,一放就是五、六十年。經歷空氣、濕度與陽光日經月累的影響下,如今我內裡早已不再是白淨無瑕且堅韌的書頁,只餘泛黃欲碎的脆弱羽翼。直到十年前,我所在的那層書才浮上到書海的表面,而五年前,我所在的牛皮紙袋才被拆封,被帶走了一本同為《老夫》的夥伴。

《老夫》所在的倉庫,充斥灰塵的氣味。
除此之外,我們生活的環境多是靜謐的,偶爾能聽到倉庫外頭車輛奔騰的浪濤聲,或聽見熾夏轟鳴在外頭的蟬鳴聲。連人類都極少走入我們這一區。一年頂多一兩次名為人類「庫存盤點」的嘉年華,才會摸著老夫蒼老的身軀折騰著。
因為極少出來,塵埃與灰塵早是我們所居住牛皮紙袋上的外牆塗裝。
而此番,時間未至五、六月或年末時,二月多時的今日,我竟被人類從牛皮紙袋抽起來。而人類把我抽起來後,甚至在我已然泛黃的內頁留下一個黑黑的拇指印。
被按下拇指印時,變髒的噁心感讓我條件反射。
我身上所累積的歷史氣息,不由得濃厚隨著灰塵味朝拿著我的人類撲鼻而去。
而就此讓他打了個大噴嚏,哈啾。
我的書封也濕了、髒了。
老夫我已是老骨頭了。
如今更是個又髒、又濕的老傢伙,前途未知。
本以為會在倉庫安養餘生,沒想到竟有人類會帶走我——雖然是以如此狼狽的姿態。
上次此區有書離開,已是五年之前了。但是那本書一去不復返,一丁點兒道別都來不及留下。這樣我們怎麼知道要去哪呢?老夫所在的書區,大家做鄰居都有至少二三十年了,作為住家的書架鋼骨、牛皮紙袋外牆,全都積了厚厚的灰,周圍的老鄰居也都是老居民了。不曾離開過此處。此區少見人類駐足,只有偶爾經過,根本無法從人類的隻言片語中獲取資訊。所以,沒有任何一本書「真的」知道大家會去哪兒。
不過地處偏遠也有別的好處。因為偏遠,不常有堆高機來往,偶爾人類會把三層書車放在我們這一區,來來去去,而上面有許多其他年輕的書。
我們也才就此知道這裡是個倉庫,也知道倉庫裡各個書系的版圖分布。因為好奇其他書的生活,在書架上頭,老夫也會遠遠對著底下的新書叫喊,向他們搭搭話。而老夫也才在偶然間,知道了旅行可能的目的地。
「老朋友,永別了。」
隔壁包裝的《說話藝術》是我老朋友,他是住在相對來說巨大無比牛皮紙包裝中唯一倖存的一本書。我們常常一起漫無目的地聊聊天,想要了解這個世界。但他忝為《說話藝術》的最後一書,竟然說出「永別」這種話啊。
不過老夫細想,這話也不算錯。
這的確是祝福呢。
畢竟幾年前,從「那本」繪本那兒,聽過一個故事。
**********
在二零二二年,也就是兩年前,老夫幸運地碰過一個旅行過又回來的挑戰者。
那是本講述藝術的繪本,書名我看不清,因為是繪本,配色豐富,老夫便暗自稱呼她為「小繪」。小繪是個女孩,很年輕,民國一百零幾年出生的。遇見她的時候,她過了五歲,但還不到十歲。
不到十歲的女孩,人類稱之為蘿莉。不過,以書的尺度來說,只要過了五年,剩下的書大概都算是熟男熟女了。(只是老夫這種活了六七十年的更熟一些罷了。)
蘿莉/熟女小繪,曾進入過「門市」。
那兒簡直與倉庫比來是伊甸或天堂,裏頭有冷氣,因為適宜的溫溼度,聽說只要在那裏,所有書籍的外表都相當童顏,效果堪比人類做醫美或電波拉提。即便,時不時就有「客人」這種特殊種族的人類會翻動她,但還是衰老地比我們這種倉庫的老骨頭慢。小繪自述自己被翻動時,總感受到自己是被愛的。氣味也不是老夫所在倉庫那種邋遢墮落的灰塵味可比的,冷氣、白光、清新的氣味,多麼美好的地方。而屬於藝術區作品的她,更是許多藝術工作者流連忘返的區域,藝術是人類共通的需求,她是偉大的、魅惑的、具有吸引力的。
而後來有一天,小繪真的被需求了。

小繪待在「門市」之中,是備受寵愛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