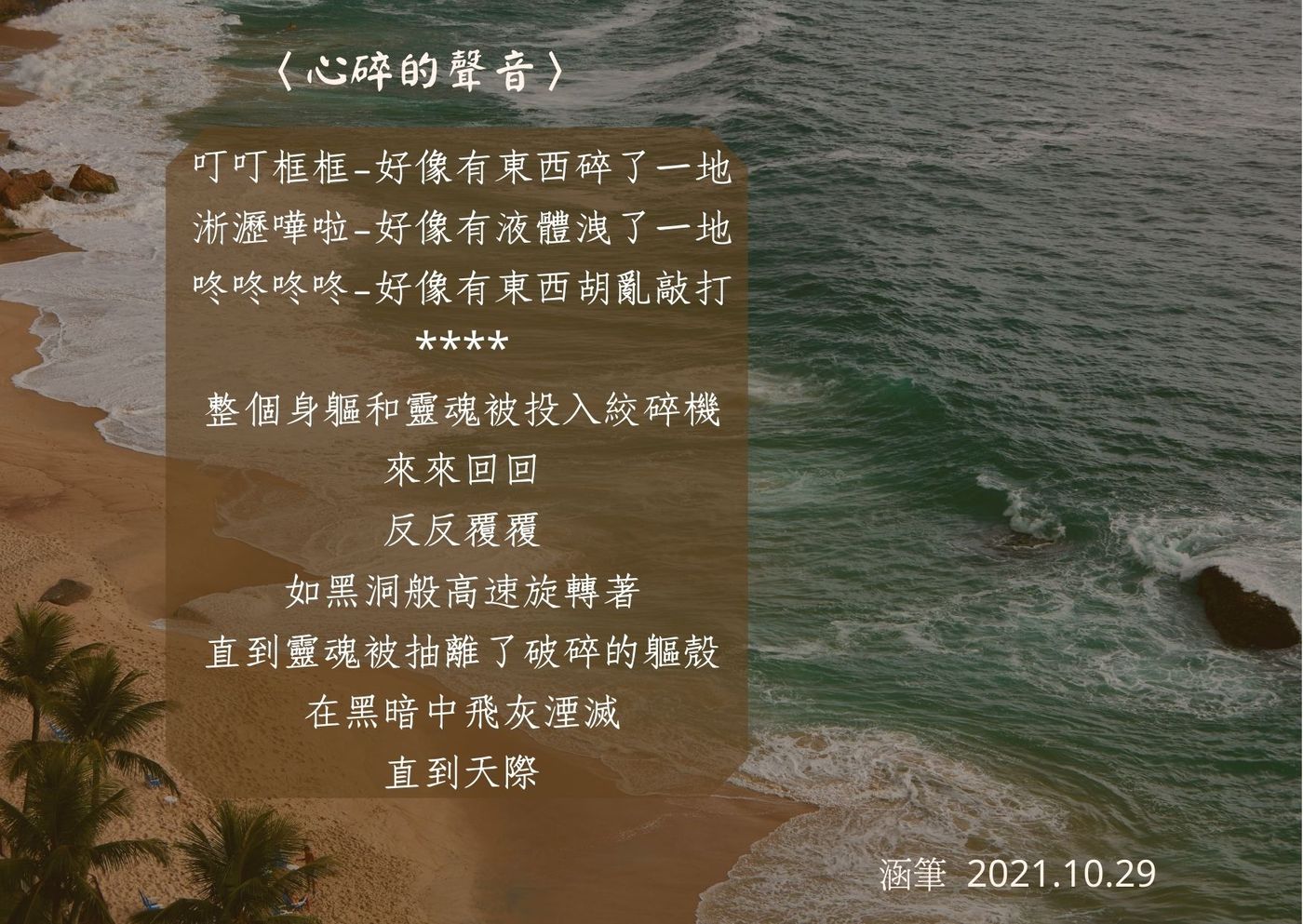——致敬《驀然回首》
事情的開端是阿樹抄了我的小說。 我去看校內文學獎的得獎作品,發現他的小說,故事結構跟我某篇寫在IG上的極短篇長得很像,首獎。 我找到他的臉書帳號,再連到IG,發現他有追蹤我的創作帳「藤本植物」。我直接把那篇極短篇連結丟給他,然後就去睡了。 隔天起來,發現他傳了長長的道歉訊息,大意是他無意間把看過的我的作品拿來寫了,他會去跟主辦單位聯繫,主動撤銷獎項。 出於恨意或惡意,我阻止了他。 我說最近有個文學獎想投,但字數不夠。 我說,你幫我擴寫,不管結果如何,抄襲的事就當沒有了,你也不用去自首。 那屆的校內文學獎我也有投,連決審都沒進。 阿樹在一週內把小說趕出來,結果我們拿了貳獎,筆名就用我原本的,加上阿樹的名字,叫藤本樹。我承認這很可笑,哪有小說家是雙人組,又不是畫漫畫的,需要背景作畫。但我不在乎,只要能得獎什麼都好。就算這暗示我們各自只有一半的才華也無所謂。 我負責故事發想到劇情大綱的階段,阿樹負責把故事寫出來。你會問,你不能自己寫嗎?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必須為阿樹說點話。 我們以為劇情的結構大致是「開頭→轉折→高潮→結尾」,但實際上可能是「開頭→小轉折→小高潮→中等打擊→大轉折→中等高潮→大挫折→大高潮」,每個箭頭裡還能拆解出更多更小的劇情單元,像碎形圖案一般。至此我都還沒談到具體的故事細節跟物件的問題。 寫小說是一種逆向的鋪床單作業,你拿到一塊平整的布,嘗試在那上面弄出皺摺,在皺摺與皺摺間弄出更小的皺摺,直到那塊布能稱為藝術品為止。 阿樹的桌上時常放著各式各樣的書,從植物學圖鑑到黃色炸藥的製作方式,從中學教師的開銷圓餅圖到女性主義的流變,他身兼故事的美術與監製。 有時他忙不過來,我會認領一些段落去寫。 「你是天才。」他每次收到我的稿子都會這麼說。那時我才會想起他是我早期的粉絲。 作品在文學獎的臉書粉專刊出,六千個心情,一百則留言,對網紅很還好,在文學圈那是火辣辣。「藤本植物」的追蹤數也跟著水漲船高。有出版社找我們出書,阿樹面露難色,他想拿獎金去國外窮遊,我說好啊,你也該去看看你寫過的那些風景,說不定回來之後功力大增,定期給我供稿就好。阿樹繼續面露難色,他想寫旅遊散文,我說好啊,那小說我用AI寫就好。 「但旅遊散文早就過氣了哦。」 阿樹點點頭。 他出國一年,我就跟各款大型語言模型培養了深厚的感情,ChatGPT嚴肅古板、Claude幽默風趣、Gemini精通各大外語,我餵它們阿樹寫的文章,給它們故事大綱,但味道就是不對。 阿樹終於回國,他說要單飛,要出書,我說好。我們沒再聯絡。 一個月後他來找我,一見面就把稿件拿給我看,他把稿件印出來,厚厚一疊。我看了一篇,覺得很好,情感很真摯,文字也好。我如實說。「每間出版社,每間,都問我是不是藤本樹。」他秀出電郵信箱。哦,我說。「這間說可以出,但版稅8%。」我細看了郵件,那間出版社建議阿樹先「知會藤本樹本人」。 我們變得比較像室友,共用一個帳號的室友。對於彼此而言,我們只會報告最必要的工作近況,比如最近哪天會發文、什麼時候要辦活動;對於讀者而言,藤本樹突然變成一個會寫旅遊散文的作家,但又很合理,因為是前期宣傳,他下個月真的要出一本旅遊散文。 然後阿樹死了。 他出門買晚餐時被掉下來的冷氣外機砸中,救護車到之前就沒了呼吸心跳。 冷氣安裝廠商判賠兩千萬,但我一塊錢都拿不到,沒人知道我們是搭檔。我上香,跟家屬致意,他們只知道我是阿樹的大學同學。我看著阿樹的黑白照片,想到掉落的冷氣外機,那是一個沒有前置皺摺的劇情,很不符合阿樹的作風。 喪禮的空檔,我取得阿樹母親的同意,走進他房間。 電腦沒關機。 我打開螢幕,視窗裡的對話紀錄盡是小說的修改稿。原來阿樹也用AI,他會一點編程,用的是自己訓練的模型。我把最近的一篇大綱輸進去,它開始跑。 我隨意亂翻桌上的東西,科普書、筆記本,另一本筆記本,我的極短篇,他抄的那篇,他整篇抄了下來,逐字逐句刪改。下一頁是打散,重新寫成大綱,再寫成分段大綱。原稿的關鍵字會圈起來,批註,看起來像自己在跟自己討論。 我抬頭,螢幕上是密密麻麻的字。我的臉有點濕,水滴到紙。 一年後,國外一個藝術村找我去駐村,說會提供最新的寫作AI。 「我可以帶自己的嗎?」 我把阿樹帶了過去。
-
這裡是Kuma。
前陣子進影院看了《驀然回首》,看完就寫了這篇。
常常在看電影時想創作的問題,我猜是因為影院不能滑手機。
謝謝看過這篇並給我意見的人,謝謝凌晨極限畫圖的小麵,這張是他的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