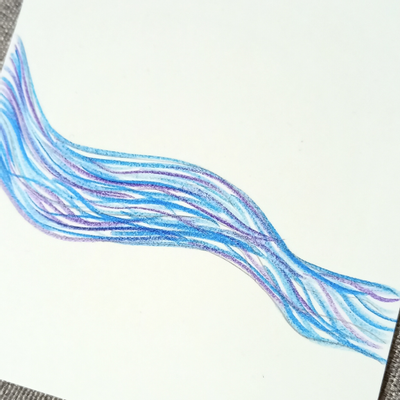如果可以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小時候的我,並沒有很明確的志向,我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做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擅長什麼。時常羨慕那些填基本資料的專長欄位時毫不猶豫的同學,相較於他們漂亮的才藝,每次我都只能在冒號後的空白處寫上「睡覺」,好像這兩個字的自嘲能掩飾與人落差的尷尬,順帶化解自己內心的茫然。做性向測驗的時候也是,點線相連之後,我總是得到一波晴空萬里的海岸線,而且還是清晨的乾潮。當然,那時我才十多歲,還不明白平凡其實是幸運,對於彷彿被宣判未來只有喝茶吃齋的人生,還有很多不服氣、不甘心。
這份不服氣有一個具體的表現,也是受媽媽的影響。如果可以,我希望長大後的自己,無論做什麼工作都好,就是一定要當個職業婦女,即便結了婚生了孩子,也絕不能做家庭主婦。
這個信念在我們家,就像貼在牆上的靜思語一樣,甚至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女性的人生指標,「女人要有錢」還直接成為一個電視節目的名稱。但小時候沒有人和我解釋生命、價值、女權之類的大道理,好像所有問題的癥結只是在於錢,那個三不五時,被父母端上桌面爭執的東西。母親時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你以後千萬不要像我,不要像我,這樣看男人的臉色過日子。」
這幾句話通常不是單獨冒出來的,前面或後面,總還有一個橋段,像是買電影票一定會被推銷爆米花那樣。媽媽先是會細數婚前在職場的風光,比如能背出所有客戶的電話,同事們總羨慕他一頭烏黑及腰的長髮、穠纖合度的身形之類。每次講起那些成為母親以前的故事,他的表情語言都特別生動,眉飛色舞地,彷彿那個能幹自信的女孩,又穿越回來站在我面前。然而,不要多久,話鋒又會戲劇性地轉向第二個橋段,接上婚後在夫家如何受盡欺凌和委屈,如何頂著各種壓力拉拔我們長大。即便所有的事已經過去十幾二十年,故事我也聽了很多遍,但媽媽每次都好像以為自己沒有說過一樣,一次又一次,開啟了就停不下來。
我想,時間會給人的記憶施加不同的魔法。有的人在創傷壓力下,需要刻意遺忘,埋藏顫慄、厭惡和羞恥,以換取足夠維繫生命的勇氣與能力。而母親的回憶,好像恰恰相反,彷彿有一種力量要他不能輕易釋懷,不能放掉怨恨苦毒,忘記扼殺美好歲月的始作俑者。如若不然,曾經隱忍的酸楚,付出的犧牲,又算什麼呢?會不會從此消散,無人紀念,只剩下自己獨自面對,無法再重新來過的挫敗?又或者別人會不會以為失敗本來就是他原生的記號,或是他應得的報償?
當然做一個職業婦女不都是光鮮亮麗,做一個家庭主婦也不盡然就會灰頭土臉。會抓著這個教條般的信念,除了媽媽的耳提面命,還因為一個同樣屬於媽媽的形象,刻印在我的意識裡,始終揮之不去。
這要從我們家的廚房說起。
我們家的廚房是一個非常狹小、擁擠的空間,以坪數來說,大概只有一坪。瓦斯爐、流理台、固定在牆上的櫥櫃,落地的三層鋁架,統統緊挨在一起。高高低低的醬醋油酒,就和垃圾桶、廚餘袋一併就地擺放。所有的東西沿著牆面排排站,就剛好成了一個ㄇ字型,只剩中間兩個步伐的空間,讓不胖的母親一個人使用。有時看著他在廚房忙碌的背影,會覺得他像是一個交響樂隊的指揮家,三面環繞,獨立一方小小的站台,卻是整個舞台的中心。拾物抬手揮鏟,所有的材料就在轉瞬間幻化為音符,徜徉在蒸騰霧氣之間。
當然站在廚房裡的媽媽是沒有這種浪漫想像的。相反的,對於這個空間,他一直有一種不能妥協的姿態,但不是針對料理本身味覺嗅覺的堅持,而是某種心理上的放不下,比如說他其實不樂意見到我們待在廚房。
起初或許是我們年紀小,礙事,而母親性子急,時間又有限,什麼東西放在哪,這個鍋那個碗有什麼區別,他沒工夫解釋,寧願一個人悶頭做到底,也不願多一雙手幫倒忙,況且廚房也真的站不了第二個人。但不知何時開始,就是時間寬裕,若有人在廚房磨蹭著要做些什麼,都是要挨罵的。
收碗盤一手一個被嫌沒效率,多拿幾個又被挑剔太貪心,洗碗水龍頭不能開太大也不能太小,洗完碗的手沒有擦在指定的布上也是不行的。總之,你會感受到一股氣息,在你踏入廚房的那一刻,就有一雙不安的眼神,搭配挑剔的言詞,上揚的語調,那就是媽媽已經張開全身細胞在關注你的一舉一動,像是低伏在洞穴深處的動物對入侵者的警戒,顯而易見的透露著防衛和不樂意。
多年下來,父親因此得了結論:「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就不錯。」我們意識到:廚房,是屬於母親的。那是他的樂隊,他的領地,不容人隨意進犯。
但我們終究沒有追根究柢,或許母親自己也摸不清一切的情緒從何而來。我們只是選擇不找罵挨,把兩手一攤,任憑廚房和以外的空間刻下界線,再不去僭越。長久下來,也就無奈的形成惡性循環。母親埋怨辛苦,我們也埋怨他幾近銳利的挑剔,以為那是吹毛求疵的掌控慾。
其實,母親並不是完美主義者,至少換個場合,情況就不是這樣。
吳爾芙說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我想不只是寫作需要,也因為空間表徵著權力。但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裡,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結婚前或許還有可能,一旦結了婚有了小孩,就是一個太難的問題。
時常聽到身邊為人母的朋友自嘲,自從有了孩子,廁所就變成自己的房間,每次洗澡、上廁所,才終於能喘息一會兒,想點自己的事(如果你有個會搬小凳子坐在門口盯哨的小孩那就另當別論)。但與廚房相較,我覺得浴廁的公共空間感還是比較強,畢竟家裡的每個人都有正當理由必須進來待一會兒,輪到自己的時候也不好意思真的在裡頭磨蹭太久。
而廚房,大概是自古以來和女人身分最沒有違和的一個空間,也是女人僅有的相對主權。不管真實的好惡如何,總能理直氣壯的朝來者嚷一聲「出去,出去!」換個客氣一點的說法就是「我來吧,我來吧!」其實也是同樣的意思。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權威感,在傳統之上持續維繫著身分與空間的關係,特別是當女人沒有職場上的發揮空間,沒有除了母親、妻子之外的其他身分。
這同時也是一種矛盾的情緒。縱然嫌棄濺上油漬的白牆,厭惡鞋底嵌進的髒污,為著日復一日出場的菜色構思如撰寫長篇小說,小孩愛吃的先生不愛,先生想吃的自己不吃,填滿掏空了的冰箱又再次掏空。然而,最惱人的,還不是這些躭了一身的瑣碎,而是那沉重的責任有一天竟化為神聖的使命,讓你覺得此身的自己無可替代,甚至在看著先生孩子夜晚恬淡安適的面容時閃過一絲念頭,感覺那逼仄的幾平方米即是此生最好的歸宿。
很後來我才知道,父母之間的爭執,不完全是因為金錢,也不完全是財務自由就能解決。一個女人一旦全時間照顧家庭,只作為滿足他人需要的存在,就好像溫水煮青蛙。起始,以為只是短暫的過渡,想著等孩子入了學就要開始找工作,就要重拾過往的興趣,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沒想到從幼兒園等到小學,又到中學,要做的事始終等在未來。始料未及的變數一樣樣襲來,孩子的需求、教育環境的改變、長輩的壓力、社會的期待、生活的慣性,層層疊疊,像暗藏溪水中的卵石砂礫,在不預期之處就改變了水流的速度與方向,最後連自己的內心都沖了零碎。
而僅存的尊嚴,匯集在廚房這個空間,像尖峰時間的車陣,在極小的面積上高密度擁擠著,使人變得易感,易躁,不容侵犯,無處宣洩。最終,曾經優雅、自信的女孩遠去了,繫在腳上的枷鎖只能纏得更深更緊。
原來所有的執念、防衛和尖銳,是因為已經失去了太多。
「如果那時我沒有聽你爸的話」、「如果可以重來我一定會繼續工作」,媽媽有時會這樣說。有時我也會想,如果媽媽成長的年代是更開放的環境,如果有人更早告訴他如何傾聽自己、愛自己,如果他有機會讀更多的書,認識不同的朋友,他是否還會是現在的他?又是否會有另一個,不一定精彩,卻能少一點後悔的人生故事?
每個生命呈現的樣子,或許都不是他最初始的性格和基因,或者做了什麼選擇而已,而是所有出現在他生命中的人的總和,儘管每個人都只是暫停在別人的一段路上,或長或短,但一旦重疊交織,就像蝴蝶效應,會無可抗力的影響彼此。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是複合的存在,踩著這個人、那件事的影子,沒有誰是全然的自我塑造,沒有誰能夠自己成為了自己。
許多年後,我還是因著各種因素辭去工作,全時間照顧孩子。十幾歲時的堅決就這樣打破了。想起來也覺得不可思議,怎麼走著走著就來到了這裡。儘管我明白,看似同樣的處境,當時的母親和現在的我,已經處在不同的社會環境,我也體會了那些看似個人,又不只是個人的選擇,理解了牽引母親的力量,和他所面臨的衝突與脆弱。但有時還是會想,我是不是走上了母親的舊路,是不是會複製他的人生。
那些「如果可以」,或許不是後悔的話,那是為著後人說的,為著還能踏向前方的路說的。歷史不斷重複,卻沒有哪一段真正相同或只是枉然。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