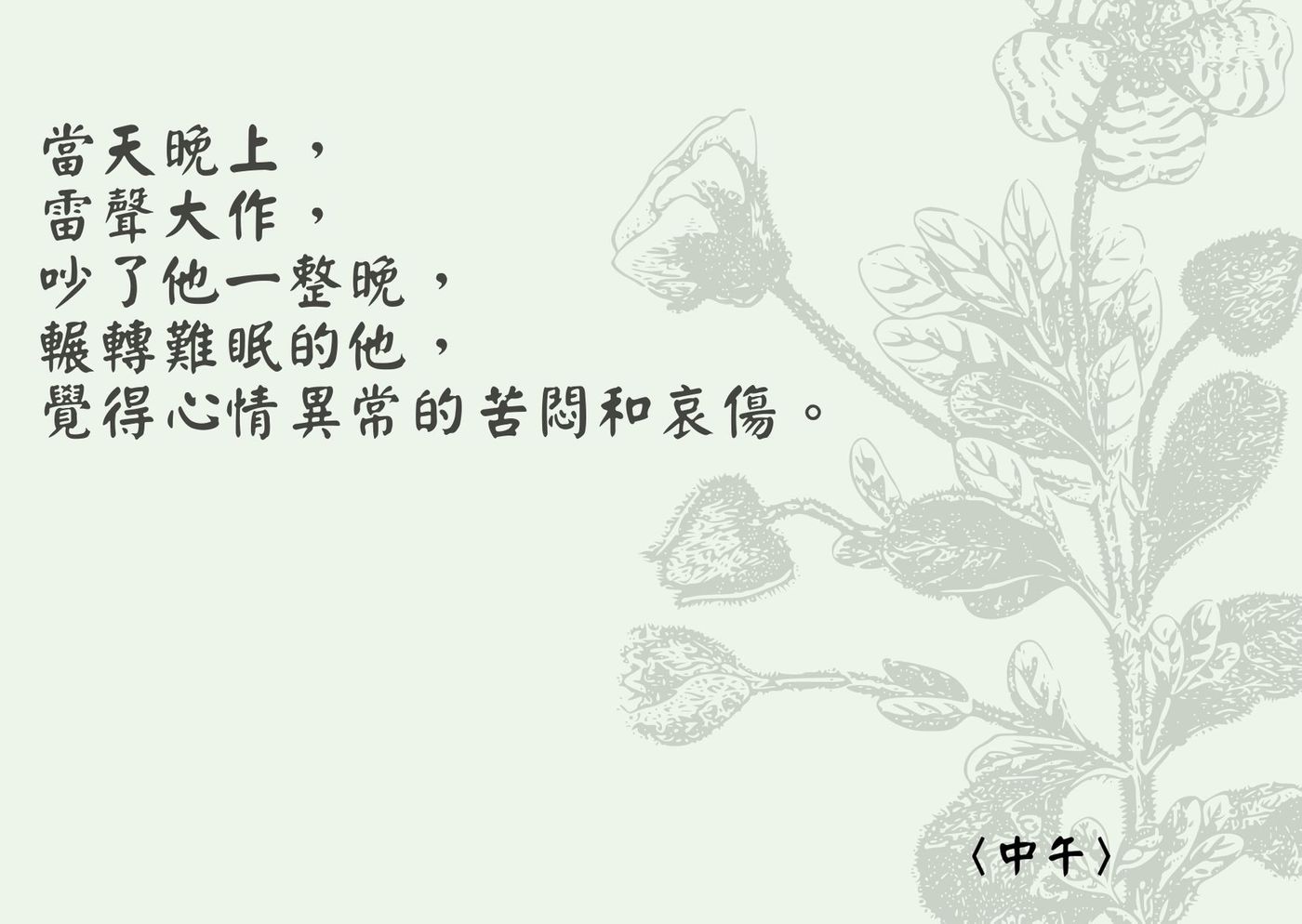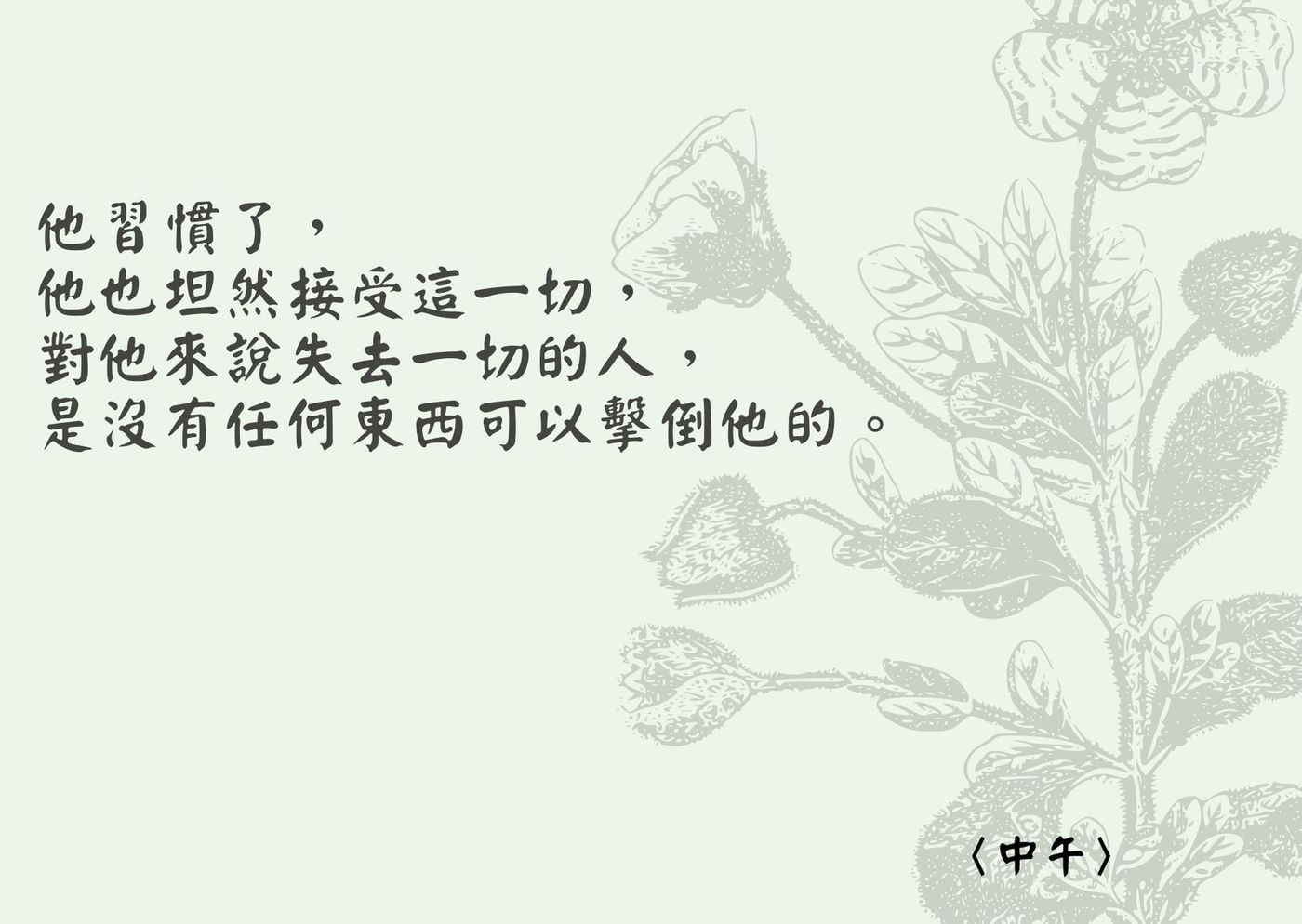他已為自己寫好一封遺書。
他在等一個雨天,然後離開這個世界。雨天是最好的時候,那好像老天爺在對他說:「好吧,孩子,你可以走了。」
他等了又等,等了幾天,未有落下一滴雨水。全城罕見地陷入乾旱,水壩的儲水量已達危險水平,池塘乾了,魚蝦的屍體都浮了上來,在熾熱的天氣裡發臭,直到乾癟。
或許老天爺覺得我還有什麼事沒完成吧。他心想。
他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會是什麼事。他孤獨地生活在空洞的城市裡,每個人被配給一個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套房,每天從同樣的窗口看一樣的風景,而風景裡都是灰白的建築物。
他的城市裡只有冷硬的建築物,四周沒有聲音,沒有人走動,沒有交通工具在路上行駛。如果這城市裡有發展建設的工程,至少還有打地基「咣咣咣」的聲音,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沒有人需要發展,他們僅在自己的小套房裡生活。
他們從不會想去拜訪鄰居,或者和社區的居民聚會,他們一直在自己的空間裡安靜地坐著、躺著,或蹲著,看著窗外的天空、天花板的燈飾,或牆壁上的掛鐘,等著天黑,複等著天光,一日復一日,直到老去老死。
城市裡的人越來越少,人們彷彿忘了什麼是情緒。很久以前,他們只從電視節目裡得到情緒,跟著戲裡的人哭笑,跟著娛樂節目感動落淚或愉快歡笑。直到十多年前,電視台裡工作的人都退休了,有些辭職不幹了,電視台的就倒閉了。從此,電視機在每個人的小套房裡成了裝飾品。
他的電視機裡養著一隻龜,像他的手掌這般大,甲殼上有清晰的脈絡,縱橫交錯,好像他手掌上的紋。電視台倒閉多久,龜就跟了他多久。他沒有跟龜說過一句話,只是默默地看著龜。人龜倆有時四目對上一整天,在彼此眨眼的瞬間得到樂趣,又彷彿傳達了什麼訊息。雖然,他從來不知道龜在想什麼。
某天晨光回到這城市時,他就找不到龜了。那龜爬出電視機,撇下他,獨自離去。他找遍他二十多米的小套房,仍然不見他的龜。他沒想過問住在隔壁的人,他們足不出戶,一天都沒開門一次,龜不可能從門下的縫鑽進去。
找了幾天幾夜,他絕望了。他看著空蕩蕩的電視機,就像自己的身體裡少了心臟,有一種失落的麻痺感。那天臨睡前,他便開始寫遺書,希望人們發現他的屍體後,會好好照顧他的龜(如果龜回來)。
會不會是老天爺要我把龜找回來呢?他心想。在全城乾旱的一個月後。
想到這裡,他開始收拾衣物,帶了簡單的乾糧,準備拿出他擱在衣櫃深處那二十年未使用的背包。他最後一次遠行是到遠方寫生,因為不小心掉入湖里差點喪生,他就不再出門。這次為了龜,他終於再拿出背包。
他把一疊衣物塞入背包時,有一塊硬硬的重物塞在底部。他伸手將硬物取出——沒錯,他的龜好端端地看著他。
他抱著龜笑了很久,笑得很大聲,整個城市轟然響起他如雷的笑聲。人們都嚇壞了,以為是地震,又以為是怪物來了,紛紛跑出自己的小套房,跑出建築物,到馬路上茫無目的地站著,呆望凌亂又狼狽的彼此。
下雨了。人們許久不曾淋雨,一時反應不來,只是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