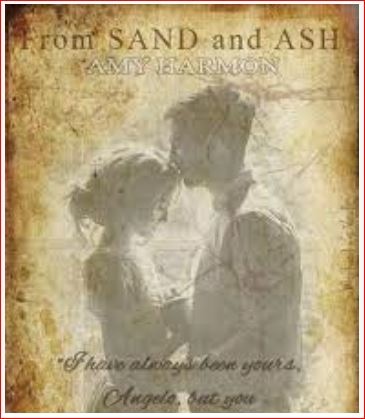戰爭結束了。但是戰爭的陰影與「敵人」,仍在這裡,與我們一同生存著。

《沉默‧真相》是一部於2016上映的德國電影,改編自伊莉莎白‧艾舍(Elisabeth Escher)的同名小說。電影講述一個猶太人小家庭的故事。雖然戰爭已經結束,但是,對猶太人而言,歐洲的生活仍遍佈著許多危險因素:未被法律制裁的加害者、對猶太人抱有偏見的警察,以及在教育界、軍隊、社區等社會各方面的組織中,潛伏的激進種族主義份子。因此,這個小家庭不得不以沉默與不斷的週遭觀察,抵禦種種的突發威脅。
《沉默‧真相》從漢娜的視角敘述整個故事。漢娜是這個家庭第三代的女孩,電影藉由小孩未知的、「好奇」的觀點,清楚呈現了每個人不同的考慮與行動。她的父親雖然本身不是猶太人,感情上對妻子凡事低調、隨時預防「身份」曝光的作法,無法體會;但也可以體諒妻子而不橫加干涉。漢娜的母親則身陷過往的創傷,不論對外人或自己的孩子,一概隱瞞家庭的猶太血統。漢娜的外婆雖大抵接受女兒的作法,不宣揚自己的猶太身份;但是並不認同其對子女亦隱瞞這一點。因此外婆在故事的前中段,便將猶太人的身份告訴漢娜。漢娜躺在沙發上,外婆坐在她旁邊。
漢娜:「我真的是猶太人嗎?」
外婆:「喔,天啊。你當然是一個猶太女孩。你不用懷疑。」
漢娜:「但是,這是什麼意思?」
外婆:「猶太人就是猶太人。就像是黑人就是黑人,亞利安人就是亞利安人。僅僅是這樣。天生作什麼就是什麼,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這部電影裡,「外婆」可說是對漢娜影響最大的人。她說的「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不能誤會成是抹滅族群的獨特性與特有的歷史蹤跡,而是別有意指:指向另一群人。當漢娜公開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遭受到宗教老師、前軍人等的攻擊時,外婆第一個告訴漢娜:猶太人就是猶太人,我們受到敵視與殘殺,不是出於自己或族群的原因;而純粹是來自敵人的惡意。
敵人
敵人,深深的改變了這個小家庭的命運。雖然敵對者的眼界被血統和傳統束縛,又在它們之上附加了虛假的想像,用同樣淺薄的濾鏡去過濾世界中的繽紛色彩。他們的生命不如正直的人多采多姿。但是,他們有暴力作為力量。許多暴力留下的傷口,難以復原。在《沉默‧真相》中,漢娜的外婆因照明彈而失明,便是歷史活生生的見證人。
漢娜的母親在戰爭期間,受到上司的威脅而被姦污。上司的威脅便是:如果不接受,那麼就舉報她的猶太人身份。戰爭結束後,這樣的傷口仍深深的留在被害者的心中。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納粹當政的戰爭期間,為了逃過祕密警察的追蹤,猶太人往往將能留下記憶的物品銷毀。即使在戰爭結束後,漢娜的母親也仍將這種應敵之道,持續下去。她不準兒女出遠門參加音樂比賽,因為那太過引人注目;反對她的媽媽與孫女說過去的故事;也任由姦污她並且毫無悔意的銀行經理,自由自在、用一個彷彿大善人的形象,在街上四處巡行。這一切,都是為了隱藏家庭「猶太人」的身份。然而,每當太陽落山,自己為自己設定的任務和行動休止時,睡眠接管了理性;敵人的陰影就往往化做腳步聲,驚擾著渴望安然入夢的人。
常常,
我在夜晚聽見正在逼近的腳步聲,
而你變成我流亡的場域,
你變成我的囚犯。
試試殺我
只要一次。
不要用逼近的腳步聲
殺害我。〈夜晚的腳步聲〉達衛許,李敏勇譯。
即使敵人無法再用合法的暴力攻擊,法律制度也有所改進;但在心中,被害者往往還是加害者的「囚犯」。而且,雖然納粹黨被消滅了,但種族歧視的觀念和非理性的憎惡,仍然留在許多人的心中。電影主要以「漢娜的宗教老師」這一角色,來描述這樣的情況。
漢娜的宗教老師是捷克蘇台德區的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不自願的被併入捷克。因此到了二戰時,納粹德國入侵此處,被當地德意志人視作解放者。她也接受了納粹德國的那一套種族觀念。
持平而論:認同納粹德國出兵蘇台德,並不一定等同於認同納粹德國的種族屠殺罪行。但是,《沉默‧真相》中的敵視猶太人者,正是把種種問題混淆起來,再以「非我族類」作為其轉移注意力的箭靶。漢娜的宗教老師以蘇台德德意志人所受的苦為藉口,毫無保留的接受納粹信念的荼毒,最終成為新的加害者。她的立場,到電影的結局也毫無改變。
記憶與生存
語言除了可以保留、傳達記憶之外,猶如房屋、日用品等物件也跨越了時代,保存了我們生活過的活生生的記憶。「語言本身」,語法、單字與思維方式等,也是一種「記憶」。不僅如此,「語言本身」還有一種特性:它不只會保持原樣而已;在孩子的語言中,往往聽得出父母的腔調,但是又不會完全相同。小孩的語言中也有單單只屬他自己的特色。借用薩依德《文化與抵抗》的說法:語言,可以把過去「帶往未來」。人生活的各項「習俗」,藉由生活者當下處境的變化,也常常一方面承繼傳統,一方面又具有「帶往未來」的特點。《沉默‧真相》結尾的喪禮儀式,也表現出了這個特點。
當漢娜的外婆逝世,漢娜的母親決定不再隱瞞猶太人身份,在喪禮上不使用基督宗教的《新約》經文,而是以猶太人的傳統代之。但是作為天主教徒,喪禮還是請神父來主持,以天主教的方式進行。穿的也是奧地利人一般使用的黑色衣服,而不是漢娜外婆所吩咐的傳統白衣。
外婆逝世。漢娜與母親在衣櫃裡找喪禮用的衣服。
母親:葬儀社的人說要黑色典雅的衣服。
母親發現漢娜衣服的異狀,蹲下來查看。她發現漢娜衣服原先縫合的下襬,剪為散狀。母親:這個是怎麼了?你做了什麼?
漢娜:外婆說:悲傷的時候將衣服扯裂是我們的傳統。白色的洋裝是最適合的。眼淚流進去心裡。
母親:還有鞋子。
最後,他們還是穿著黑色的衣服出席;也沒有完全照著傳統猶太人的作法,以撕裂衣服的方式表達哀悼。但是,這卻不代表他們抹煞了自己的身份;恰恰相反,漢娜的母親正是在這場喪禮中,第一次向外人展現出猶太傳統。一個活著的傳統,一定會由於所面臨處境的不同,從當下的歷史再一次得到形體。
這種「保存方式」與「實質內容」間的細膩的互相影響,在另一件事上也有所體現:那就是電影中提到的「相片」和「記憶」。
漢娜摸以前的相片盒子,想找看看有什麼相片。
外婆:「你不會找到什麼的。」
漢娜:「媽媽和阿姨,小時候的相片一張都沒留嗎?」
外婆:「沒。較早的相片一張也沒留。每一張相片都有可能出賣我們。」
在迫害時代,每張相片都可能變成辨識出身份,祕密警察據以求刑的「罪狀」。為了生存下來,不得不把這些乘載著回憶之物捨棄。但是,這並不代表敵人成功的消除了記憶,而是:乘載記憶的相片雖然銷毀了,歷史活生生的見證人卻活了下來。漢娜的外婆雖然曾把相片全部燒掉;但是取而代之的,過去的記憶她牢牢的記在心底。不論是「大樓管理員」、銀行經理對他們的迫害,還是她與逝世丈夫的回憶。她也牢牢記住從他人那裡聽來的推定死亡日期,以作為對亡者的記念。
漢娜:「老師說我連外公是誰都不知道。」
外婆:「我第一任丈夫,是吉迪恩范高,演員兼歌手。漢娜的外公,是在1943年4月9日,被解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囚號J70813。推測在1944年3月,送往毒氣室,屍體焚毀。」
面對敵人對自己「身份」的嘲笑,漢娜的外婆站在敵人(這裡的宗教老師)面前,以堅定的語氣陳述自己的記憶。在猶太人死亡與流亡的記憶中,敵人的罪行也無所遁形。當然,在公眾前宣示這件事,敵人並不一定會因聽見而有所悔改。但是,過往的記憶與當下的生存總是聯繫在一起。一個受苦的族群雖然仍身陷許多敵意,但在民主時代,他們已經能夠合法的、受法律保護的宣稱自己的連續性。
在迫害時代維繫生命想望的記憶;度過迫害後,或能成為重建生活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