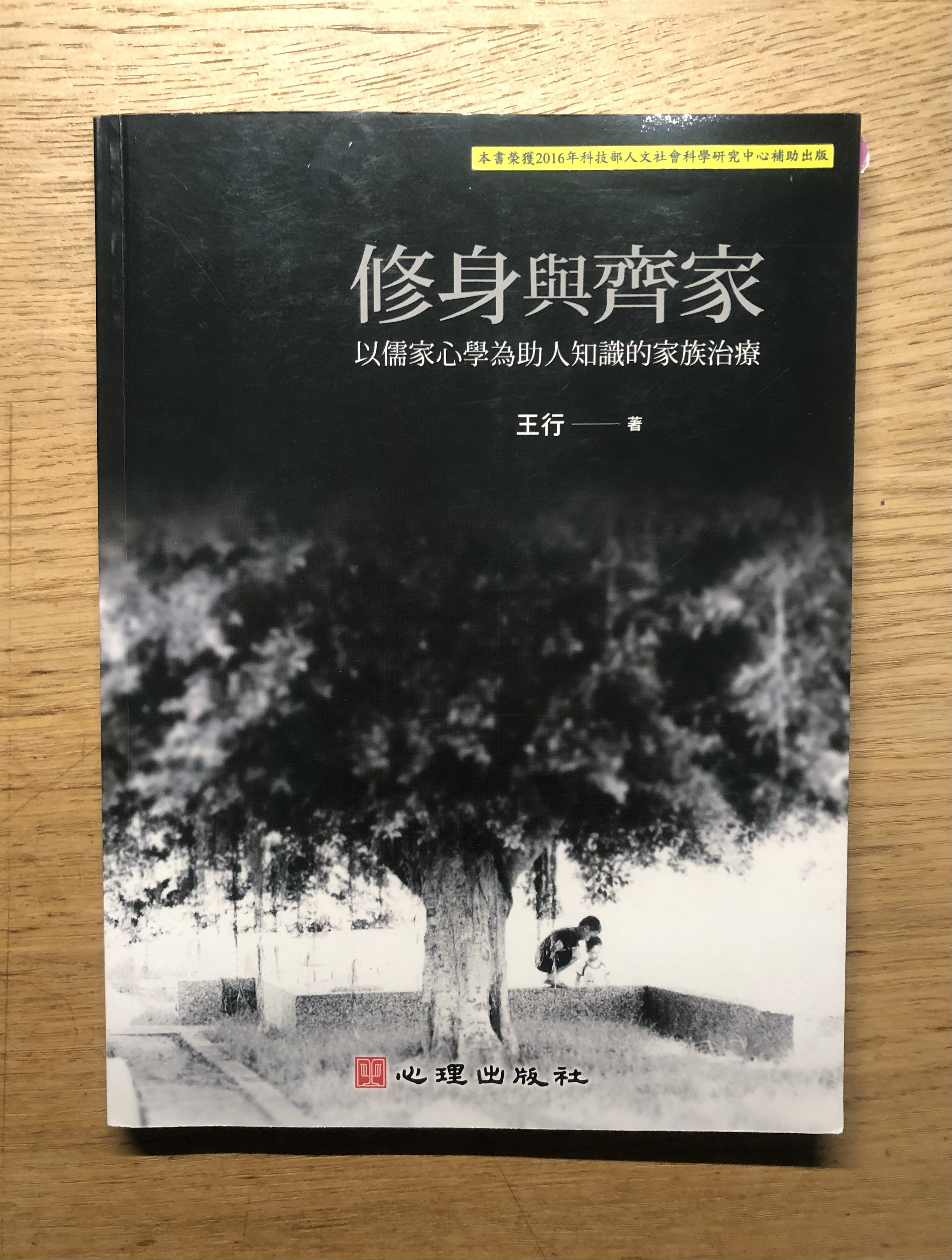五、性善之辯
在《孟子·告子篇上6》這一段,孟子的學生公都子,轉述了告子對人性的三種看法:
①無善,無不善
人性本身無所謂善惡,乃後天習成。
即有為善或為惡的可能性、可塑性。
③有善,有不善。
有些人天生是善的,有些人天生卻是惡的,這是命定論。
告子所說的人性,是就人的生理活動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徵象來論說的,即就人的生理本能與反應等等來說。故此,告子在另一段就推論「食色性也」。愛好美食,喜歡美色(不一定指女色),乃人的天性。其實,告子的觀點,還是前面他所主張的「生之謂性」。
如果按照告子的說法,把人在生理上的自然性向,來作為人的天性的話,這樣就無法體證人的尊嚴與價值,這和動物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孟子就回應:
只要順著人的真情的流露(如惻隱之情),就可以為善,這便是我所說的自覺心了。要是有不善的行為出現,那不是自覺心的本質。
例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不是四個心,乃是一心多面)等等,都是人皆有之的。而這些自覺心,發揮至圓熟的地步,就是仁、義、禮、智這些德性。而這些德性,並非由外在的力量所形成的,人自己本來就有的,只是沒察覺而已。所以說:求則得之,捨則失之。在得與失之間,真是壁立千仞,立竿見影啊!要是沒呈現出這自覺心,這完全是因為沒有盡心啊!
《詩經》說:天生下眾多人民,凡事都有一定法則的;人民能夠秉執常道,只因有喜好善的這種美德。孔子於是讚歎說:作這詩的人,真能體會到常道啊!
孟子接著就說:所有事事物物,必定都有一定的法則的,人能夠執守著這常道,當然就是喜好美德了。
按:以上這段原話的意譯,跟過去的學者所理解的,有些關鍵性的不同,特別與當代研究孟子性善論的學者迥異。筆者不敢說他們錯解,而只是筆者個人根據原文語意與孟子的思路,加以意譯而已。
這樣的意譯,就完全沒有「善性人所固有之」,而是指自覺心——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等等自覺心,人所固有之。這麼一來,就可以此自覺心,作為「人禽之辨」的依據,而不用說人性本善。事實上,孟子始終都沒有明說「人性本善」;而只是說人有自覺心,順著自覺心的流露,就會呈現善心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這些都是人有傾向於善的能力。當自覺心發揮至圓熟的地步,就是仁、義、禮、智這些德性。同時,孟子又認為這些德性,平閑時是隱藏在人心底裡面,而一旦發用,就會有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的氣勢,而那種正義之氣勢,是不能阻擋的。
人只要一念自覺,肯求、肯爭取,則得之,而自滿自足,毋須俯仰由人。如果自我放棄,則失之,這樣就是人生的遺憾啊!
(寫於2021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