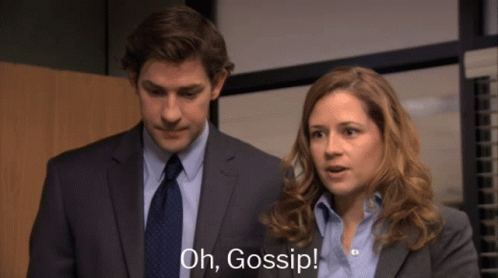會知道這本好玩的書是剛好看到蔡有蟲的《台灣豬,黑白切》好書不負責推薦,書名兩個關鍵字完全對到我這個貪吃鬼的味。在文章底下的留言有看到網友提到《蚵仔煎的身世》也默默收進口袋清單中。

圖片來源:博客來
P.S.這次是買實體書,封面印刷滿有質感的,放在書架上有種辦桌的喜氣氛圍。在跨頁間還有一隻小豬好可愛。
小時候有聽過大人說黑豬肉比較厲害但因為沒有比較基準分不出區別。當第一次在卡拉拉涮涮鍋吃到黑毛豬後驚為天人,柔嫩的脂香在口中化開,不像我以前印象中火鍋豬肉片吃起來纖維感很重。自此之後成為台灣黑豬肉忠誠的教徒。因此現在去火鍋店只要出現深坑黑豬肉便會毫不猶豫地點下去。自家煮咖哩除了雞肉或牛肉,改成豬肉也很美味,我很喜歡梅花肉與胛心肉各半斤搭配,一次可吃到兩種口感且耐煮,比雞肉多點肉感也比牛肉少點油膩。(從書中得知黑豬又分為吃餿水和吃飼料的豬,吃餿水的肉比較肥美,又稱「土黑」;而吃飼料的話不論黑豬白豬吃起來沒有很大的區別。(驚))黑白切源於古早台灣社會環境不富裕,只有在逢年過節有大口吃肉的機會,將食材善盡其用的智慧。因每家店的品項不盡相同,顧客在摸不著頭緒時可依據自己的預算請老闆「隨意切」、「都好啦」。也反映當時店家跟食客間的信任與互動,享受像開盲盒一樣的趣味。而南北也有不同的料理方式,在北部多是各個部位依據最佳口感白焯享用,而南部還會加入調味加工成熟製品。同樣點粉腸,在北部是未翻面刮洗的小腸,若在台南老闆可會端上一碟小腸內灌入豬肉與地瓜粉漿類似香腸的小菜。跟南北兩地不同的食性也有相關,南部通常會切一盤黑白切當成點心來吃,不光吃肉的鮮味,也加入創新的巧思。
曾經在網路上看過大陸某些鄉村有吃「年豬飯」的傳統,家家戶戶在過年會殺豬,並搶快在尚有體溫的將豬肉迅速分解。豬板油剔下煉豬油、豬腿加工成醃漬火腿、做臘肉⋯等,就連內臟都不浪費,想盡辦法延長保存期限。殺豬是慰勞過去一年的辛勞,也是慶祝新一年的到來。
黑白切有江湖術語,不完全等於解剖學的器官名稱。不直接把動物或器官名稱搬上餐桌,是餐桌上對動物奉獻生命的禮讚。
豬上顎有個江湖名字叫天梯、腰子和腰尺分別是腎臟和胰臟。例如豬頸肉別名叫松阪豬、僧帽肉是二層肉的別稱,因為形狀接近三角形像西方僧侶的帽子;臉頰肉因筋肉分布如綻放的花朵又被稱為菊花肉…等,可見攤商的取名之精妙。黑白切不以器官直接命名,作者打趣地形容也可比擬成吃法餐的優雅。
開始自己煮飯以後,才知道從食材到餐桌有各種眉角。從市場買的溫體豬就是比在超市買的少了腥味,多了甜味與Q彈。自己處理過豬舌、豬肚後才知道要煮出衛生美味的食物不是像彈個手指輕鬆就可達成的任務,因此對小吃店老闆升起了敬佩之意,也體會到美食得來不易每一口都值得細細品嘗。
書中幽默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作者愛吃、懂吃,也介紹了小吃背後不簡單的文化脈絡。(欽佩作者讓我見識到除了好吃之外還有豐沛的詞彙形容美味)吃也是情感的一種鏈結,讓人回想起某個當下或是與某個人間的點點滴滴。引用作者說的:「終有一日,我們都得自己設法復刻出心中的古早味,惟願那一天慢點到來,最好永無到來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