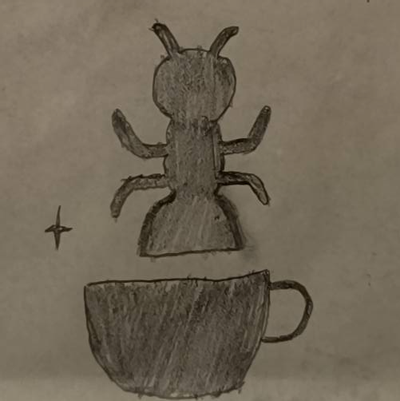那年台北的冬天特別冷,刺骨寒風像手術刀,從牆縫裡鑽入,彷彿連鋼筋都要被刮骨療毒般剔刮一遍,這才侵襲到人體表面。這時,人們只能窩在電暖器前,一邊搓著手,一邊呵出白氣,咒罵這該死的天氣,不讓人活了!
夜裡,抱著會被凍死的疑慮,進如寒冷的夢鄉,隔天,獨居老人猝死的新聞出現在報紙的小角落,沒人會在意,很快被遺忘。
蘇梔婉住在大安區一棟老式公寓的四樓,沒有電梯,樓道狹窄,牆上的米黃色油漆裂成長長的紋路。她的房間永遠亮著燈,窗簾總是半掩。鄰居偶爾在陽台抽菸時會抬頭看到她的影子,安靜、纖細,像一段被卡在時間齒輪裡的膠片。她在一家舊書咖啡館打工,那種店在台北早已不算時髦,木地板嘎吱作響,牆上掛著泛黃的爵士海報,吧檯邊有一台壞掉的黑膠唱機,只當裝飾用。她喜歡這裡的理由很簡單 —— 店裡的燈光偏暗,咖啡味能蓋過外面馬路的潮氣,而且,沒有人會追問她的私人生活。
如果要說她身上有什麼異樣,那就是她的眼睛。
那雙眼睛像深冬的港口,水面鋼灰色,裡面漂浮著一些過於古老的東西——戰爭的殘響、飛機的影子、紙鶴的輪廓。
她自己知道那是從三歲那場高燒後留下的。
三歲那年的高燒,她在夢裡看見過另一個自己——那名女子穿著二零年代的旗袍,頭髮盤得很緊,站在機場邊,對著一個穿飛行服的年輕男人揮手。
她知道那男人的名字叫何紹庭。她知道他右耳有顆黑痣,知道他寫信的末尾總會畫上一隻紙鶴。她甚至知道,他死於一九三八年的空襲。
這些記憶,不是看電視得來,也並非別人告訴她。
她母親在她第一次說出「我把飛機藏起來了,不要讓日本人找到」的時候,差點把家裡的觀音像打翻。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被當成說夢話的孩子,甚至老嬤嬤還曾經帶她去行天宮收驚。但這些影像和感覺,像一條暗河,一直在她心底流動。
遇見他,是在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後。
店裡的暖氣忽然壞了,顧客不多。她抱著一杯溫過的紅酒,坐在櫃台後面看一本關於二戰航空史的舊書。門上的風鈴響了,她抬頭,看見一個男人走進來。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外套,肩膀挺直,手上提著一個舊皮包,頭髮稍微有點亂,像是剛從一陣風裡走出來。他的眼睛並不特別亮,但很穩定,像是能看穿咖啡館的所有陰影。
他點了一杯黑咖啡,然後坐到靠窗的位子,從包裡拿出一本筆記本和一支老式鋼筆。
蘇梔婉在端咖啡過去時,視線掃過那支筆。
那是一支老舊的鋼筆,筆桿微微泛著深藍色的光澤,筆尖已經被長年的書寫磨得圓鈍。她的心在那一刻像被什麼擊中。
「不好意思,」她忍不住開口,「你的筆……是從哪裡買的?」
男人抬起頭,露出一個略帶疑惑卻不失禮貌的表情:「這支筆?………是我爺爺那一輩傳下來的。聽說他當年是個飛行員。」
蘇梔婉覺得空氣突然變得稀薄,她聽見自己用幾乎是耳語的聲音問:「他叫什麼名字?」
「何紹庭。」
她的指尖在托盤邊緣收緊了一瞬,還好她沒把咖啡灑出來。
後來的日子,他幾乎每天都來。
他叫何靖南,在大學歷史系任教,專攻近代戰爭史,最近正在整理家族裡的舊檔案,所以常來咖啡館看書、寫東西。
他很快注意到,蘇梔婉對那些泛黃的照片和航空史的書,有異常的專注。
有一次,他拿出一封泛黃的信請她幫忙辨認字跡。那信的末尾,畫著一隻小小的紙鶴。
她的心被那一筆勾得生疼。
「這封信……你知道是收件人是誰嗎?」她問。
「不太清楚,家裡說可能是我爺爺那一輩的女友吧!戰爭時斷了聯繫。」
她沒有再追問,卻在心裡覺得,自己的世界被一條無形的線重新縫合了。
他追求她的方式並不張揚,但很有耐心。
每天下課後,他會繞遠路來店裡,只為陪她喝一杯咖啡。偶爾帶來一些從圖書館翻出來的戰爭舊照,和她一起對照地圖,相互印證。
有時他會在她下班時,為她撐傘走過仁愛路那段長長的人行道。
她發現,和他在一起時,自己不必刻意掩飾什麼。即使沉默,空氣也不會尷尬。
那種感覺,很像前世夢裡,她在成都的茶館裡替他織圍巾時的歲月靜好。
一個下著細雨的傍晚,他們走在和平東路的人行道上。霓虹燈在積水裡反射,像一面搖晃的鏡子。
「蘇梔婉,」他忽然說,「我覺得我們認識很久了。」
她笑了笑:「多久?」
「可能,比我出生還早。」
她停下腳步,看著他,想說什麼,卻只吐出一句:「你相信前世嗎?」
他愣了一下,然後點頭:「如果是妳說的,我信。」
那一刻,她幾乎想要伸手去握住他。
那晚之後,何靖南來得更頻繁了。
不像一開始那樣只是喝咖啡、寫筆記,他開始主動邀她去別的地方 —— 二手書市集、海邊的小鎮、深夜還開著的獨立電影院。
他總能找到一些不擁擠、不喧鬧的角落,像是專為她挑的。
在永康街的某間小酒館,他會替她點清酒,自己只喝一杯淡得幾乎無味的威士忌;去基隆港邊,他會帶一條舊毛毯,讓她坐在堤岸上看漁船進出。
有一次,他們去北投泡溫泉。外面下著大雨,蒸氣和雨絲交織在一起,讓空氣像水一樣濃稠。她看著他對著玻璃起霧的窗寫下「紙鶴」兩個字,心裡像被輕輕按了一下開關。那一瞬間,她幾乎想告訴他,自己夢裡的前世、戰爭、告別、和那句「等我回來就結婚」。
但她忍住了。
因為她不確定,那是屬於何紹庭的,還是屬於何靖南的。
那段日子裡,她開始接納他的存在。
他會在深夜傳來一張老地圖的照片,說「你看,這裡是南京舊機場的位置」。她會回一句「我好像去過」,然後在黑暗裡獨自盯著天花板,回想夢裡的場景。
她第一次讓他走進自己的房間,是一個意外 —— 那天她突發低燒,他送她回家。
公寓的燈是暖黃色的,他替她泡了薑茶,坐在床邊幫她量體溫。
「妳的手好冷。」他說。
「一直這樣。」她回答。
他握著她的手,沒有再放開。那種溫度並不急切,卻有一種持續而長久的溫暖。
她看著他的眼睛,突然覺得 ── 或許真的可以再愛一次。
然而愛情的發生,常常伴隨著不安的陰影。
她開始害怕 —— 害怕自己只是愛著他身上殘留的前世身影,害怕這段感情只是宿命的延續而不是新的開始。
這種不安在一次偶然的場景中被放大了。
那天是周五傍晚,雨很大,她提前下班,想去找他。結果在系館外,她看見他正和一名年輕的女研究生並肩走出來。女孩撐著傘,笑容很亮麗,他低頭替她提著資料袋,那畫面在雨幕中格外清晰。
她沒有上前,只是轉身走回公車站。
回到家後,她盯著手機的訊息框很久,最終還是什麼都沒問。
從那之後,她開始保持距離。
他還是照常來找她,但她的回應不再那麼即時,見面次數也漸漸少了。
她對自己說,這樣比較安全 —— 至少在他真正離開之前,她可以先退出,不至於重演一次前世的結局。
但何靖南似乎察覺到了什麼。
一次深夜,他突然站在她的門口,手上拿著一袋熱騰騰的鹹酥雞。
「妳是不是在躲我?」他問。
「沒有啊!」她笑得很淡很淺:「只是最近比較忙。」
他盯著她看了很久,才說:「我以為我們之間,不需要說太多理由。」
那一瞬間,她差點就要把一切都告訴他 —— 包括她在雨中看到的場景,包括她的前世夢境。
但她最終只是低下頭,接過那袋鹹酥雞,說:「太晚了,你回去吧!」
兩個人的距離,就這樣慢慢拉開。
直到一個月後,他突然告訴她,自己要去國外開一個長期的學術會議,至少半年。
他沒有再多解釋,也沒問她要不要等他。
她聽著他的聲音,腦海裡突然閃過前世那個場景 —— 機場、告別、和那句「等我回來就結婚」。
她只是笑了笑,說:「祝你順利。」
那天之後,他就真的走了。
何靖南離開後,台北的春天就冷了下來。
夜裡的風從公寓的窗縫裡滲進來,吹動桌上的便條紙。
蘇梔婉開始失眠,她會在凌晨三點起來煮一杯黑咖啡,披著駝毛圍巾、坐在陽台,看樓下空蕩蕩的巷子。
她偶爾會想起他離開那天的表情 —— 不算冷淡,也不算留戀,像是一個人把自己的行李收進一個密封的箱子,暫時寄放在無法追查的倉庫裡。
她告訴自己,這樣也好。宿命已經重演過一次,她不想再經歷第二次機場的空等。
夏天來臨時,她的身體開始出現一些異樣。
先是胃口不好,後來是長時間的咳嗽。她一開始不以為意,以為只是換季的感冒,但咳到有血絲時,她還是去了醫院。
檢查結果像是一封冷淡的電報:癌症晚期。
醫生的聲音在她耳裡有些遠,她只是點頭,然後獨自走出醫院。
陽光很亮,她站在人行道上,突然想起自己三歲那場高燒醒來時,也是這種刺眼的陽光。
她沒有通知任何人,包括何靖南。
他在國外,應該忙著自己的計畫,何必再為她的病情而分心。
直到那天,她在咖啡館值班時,遇見了系上的一位老師。對方是何靖南的同事,聊著聊著,不經意提起:
「你知道嗎?他原本不打算出國的,是因為那位女研究生家裡出了事,他替她頂了研究計畫,才去的。」
她怔住。
「替她?」
「對啊!那女孩本來的指導教授臨時生病,計畫差點作廢,是何靖南說反正自己手上的案子能延後,就接了她的工作。那半年他幾乎沒自己的時間,聽說還自己掏錢幫她印資料。」
她聽著,心口像被什麼東西緩慢地推開 —— 原來那天雨中的場景,不是曖昧,也不是背叛。只是她自己提前下了結論。
她笑了一下,卻感覺眼淚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她在之後的日子裡,把他遺下的筆記本,撕下一頁,摺成一隻紙鶴,放在床頭。
有幾次,她差點拿起手機給他發訊息,卻又放下。她不想在這個時候,讓他跨越半個地球,為了一個已經無法改變的結局。
但命運有時會自己推門進來。
七月的一個清晨,她的病情突然惡化,被送進醫院。
在意識斷斷續續的間隙,她聽見有人急促地叫她的名字 —— 聲音有些沙啞,卻熟悉得像長在她的骨頭裡。
她費力地睜開眼,看見何靖南站在床邊,呼吸急促,額角還有未乾的汗。
「你……怎麼回來了?」她的聲音幾乎聽不見。
「我聽說了,一切。」他的手握著她的手,溫度燙得像要把她從深水裡拉上來。
「為什麼不告訴我?」
她微微笑了一下:「我怕……你又要飛走。」
「我不會了。」他的眼睛泛著紅:「這次,我會留下來,不會走了!」
她看著他,感覺時間在那一刻靜止了。
她想說很多話,想告訴他前世與今生的故事,想告訴他自己其實已經準備好愛上他 —— 不管他是誰。
但她的喉嚨像被綁住,只有一個句子流了出來:
「來生……請你不要飛得太遠,好嗎?」
他的手握得更緊,卻感覺到她的指尖正在一點一點地失去力氣。
外面的天光漸亮,病房裡很安靜。
她的枕邊放著那隻紙鶴,翅膀微微張開,像是準備要飛,但沒有方向。
何靖南坐在床邊,低頭,額頭抵在她的手背上。
他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再次遇見她 —— 或者說,才能再次被她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