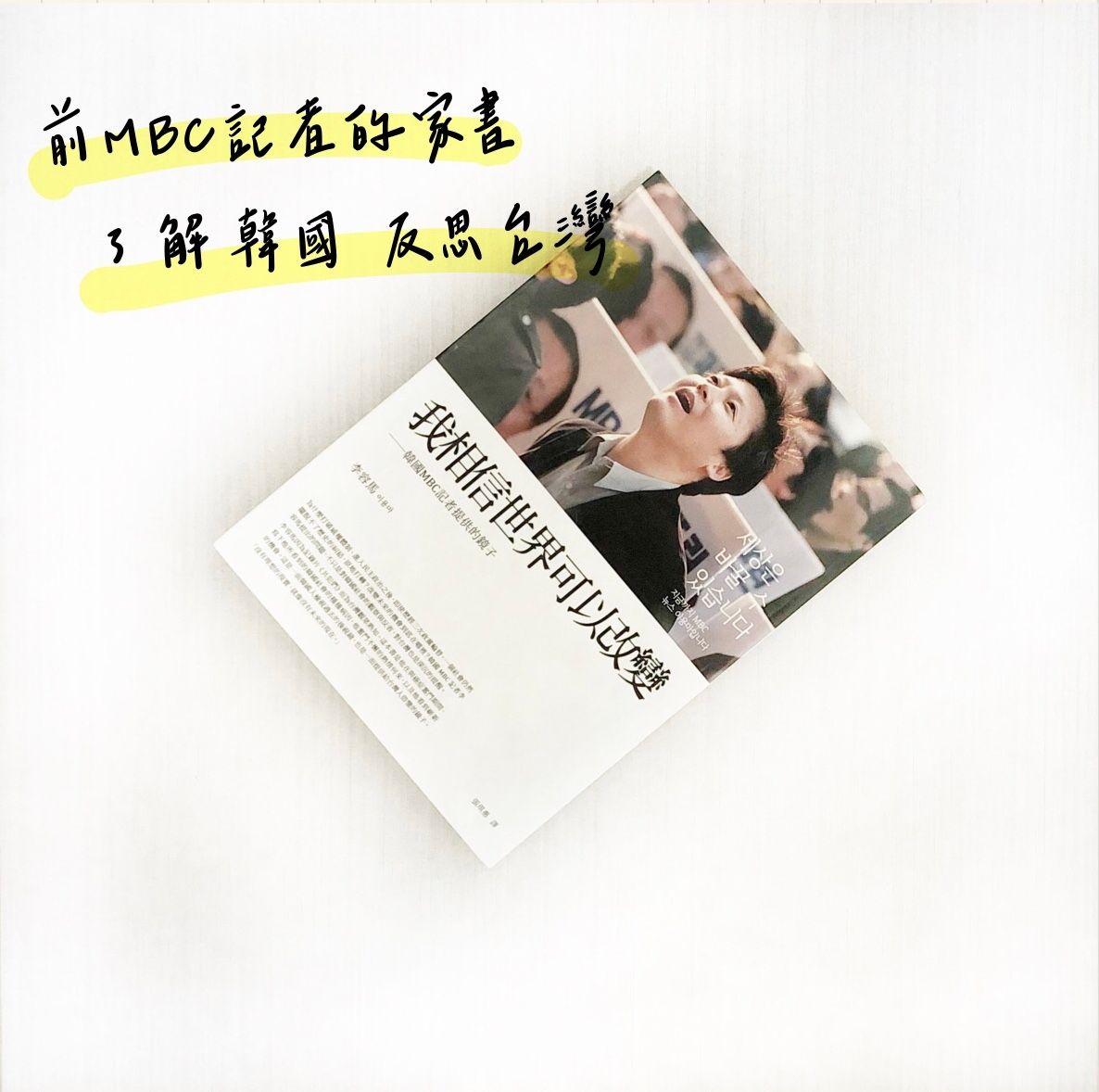刊於《中學生報》第654期(2025.9.8)文藝櫥窗
方法論 ◎洪萬達
洗澡的我總想這些:
呵鏡子的霧氣,以手腕拂之
臉完好無缺地顯現出來了
隨後又顯現一層薄薄的蒸氣了
我再用力呵它
人只剩下一點淡淡的駝色了
演戲的我也總想這些:
大步在舞台的兩側來回穿梭
擠眉弄眼──與對手
盡情地說話。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呵──把聲音
送給底下模糊的風景
2022年,新生代詩人洪萬達以詩作〈一袋米要扛幾樓〉獲得台北文學獎首獎;因為題材觸及時下流行的動漫和迷因,讓他同時受到了大量讀者的關注。在隔年出版的同名詩集《一袋米要扛幾樓》,這位詩人透過戲劇性的敘事,化身為一位想像力豐富的演員,向觀眾展現寫作技術的同時,也走出了不同於前行代詩人的一條路。
▍兩種情境引發的思考
閱讀這首總共十二行、分為兩節的詩作〈方法論〉,會發現洪萬達把極度重視個人隱私的「洗澡」和試圖引起觀眾共鳴的「演戲」相互連結,形成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對照。「我」在兩個情境之下的所思所想,究竟有什麼相同和相異之處?第一節的「我」拭去鏡面凝結的小水珠、短暫看清自己的容貌後,很快又被霧氣模糊了形象。詩中所述的行動和遭遇,彷彿揭示了我們探索事物時,在清晰與模糊間來回徘徊、反覆猶疑的狀況。這種困難與不確定就像是殘存的記憶,往往有意無意間就「只剩下一點淡淡的駝色」,無法回頭確認事物的真面目。
到了第二節,演戲的「我」彷彿變成另一個角色,「大步在舞台的兩側來回穿梭」,以誇張的表情完成一次次的呼吸和對話。這裡的思考富有機趣,觀眾理當是「演戲」的接收者,卻在這裡化身為靜態的景象,展現出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
▍社群生活的本質是舞台表演
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借用「戲劇」的框架提出了一套深刻的社會理論:社群生活的本質,無非是一場又一場的舞台表演。
這樣的觀念聽起來非常抽象,但仔細想想確實如此。在家中,我們也許是主動打理家務的女兒或兒子;在社區,我們可能是敦親睦鄰的好厝邊;在校園,我們被培養成尊師重道的學生;在職場,我們被訓練為進退得宜的同事。無論身處什麼環境,我們都無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倫理規範的影響,像是戲劇一樣「表演」出他人所期待的模樣。
這些公共場合作為表演的「前台」,我們會視情況調整自己的行為,面對觀眾完成一場又一場的表演。然而,在獨處而無人干涉的「後台」,我們能否真的脫去戲劇的面具,誠實面對自我的情感和行為?從面對社群的表演到洗滌身體的赤誠,洪萬達在〈方法論〉這首詩中,精準抓到了兩個迥異情境的相同之處,從而製造出了深刻的思想張力。
▍找到面對世界和自我的方法
綜覽整首詩,除了作為敘事者的「我」,唯一出現的其他角色是和「我」盡情說話的「對手」。如果演戲時的「對手」指的是其他演員和觀眾,那麼洗澡時的「對手」則可以被理解為鏡中的自我。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被鑑照出的形貌也就未必是真正的自我,而可能只是另一種的舞台──我們內心對自身的期待和想像。
這種關於存在和表象的思辨,也呼應了詩作的題目。在學術領域,「方法論」指的是對研究方法的討論;而在這首詩中,「方法論」成為了一種面對世界、面對自我的探索過程。此刻的我是不是正在扮演某個角色?那個角色,真的是我希望成為的模樣嗎?這些針對內在的深刻反省,也許是洪萬達透過這首詩作,試圖達成的事情。
當然,無論是順應他人的期待而改變自己、將聲音「送給底下模糊的風景」,又或是忠於自我內心而追求當下的快樂,一切都沒有標準答案。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要過什麼樣的人生,終究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刊於《中學生報》第654期(2025.9.8)文藝櫥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