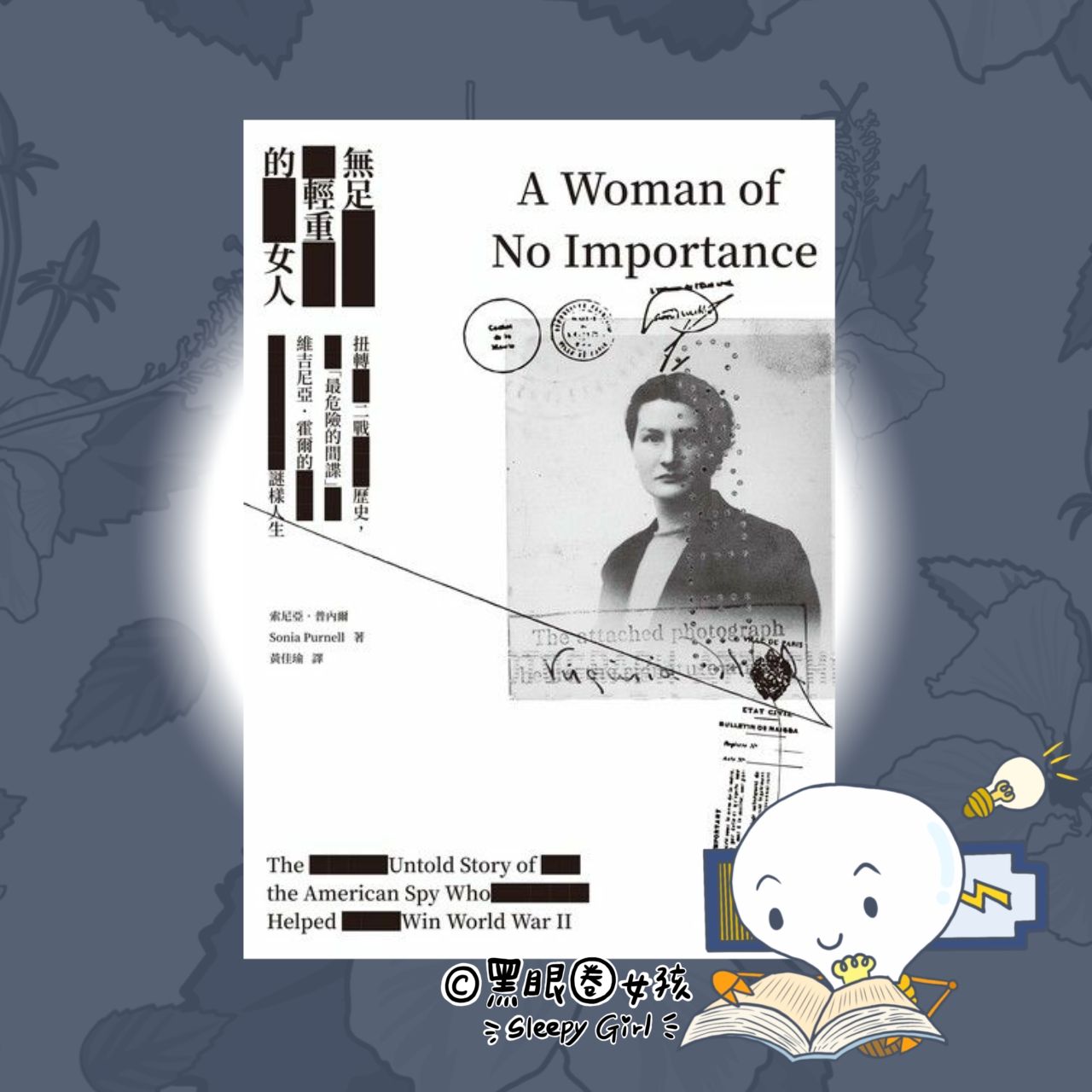一、前言
居民想要繼續生活,作家想要繼續發表作品,藝術家想要繼續畫畫。在其他納粹占領的國家裡,除了合作或是進行地下活動之外,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正因為在法國有更多的自由,人也面臨了更多道德抉擇,情況更為複雜。(Buruma 2009: 164)
2009 年,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於其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藝術評論〈德占時期的巴黎──甜美與殘酷〉(Occupied Paris: The Sweet and the Cruel)中,探討了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法國的種種樣貌。除了布魯瑪的敘述,我們也可以透過法國攝影師安德烈.祖卡(André Zucca)的攝影集《德軍佔領之下的巴黎》(Les Parisiens sous I’Occupation)窺探 1941 年的德佔巴黎。
弔詭的是,《德軍佔領之下的巴黎》中的巴黎,正如布魯瑪所言,其景象和其他德國佔領區不同──街上的人們熙來攘往,但不是為了搶奪物資;孩童聚集在巴黎鐵塔前的廣場溜直排輪;德軍進入巴黎後,在街道掛上隨處可見的納粹旗幟;德國的軍隊與巴黎居民擦肩而過,彷彿一切都是那麼地稀鬆平常──所有的影像透露著祥和與寧靜,德軍的入侵與否、絲毫沒有對法國的生活造成任何改變。
2008 年,祖卡的照片在巴黎市歷史圖書館(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展出時遭到了媒體的批評。這些「讚揚佔領者」、「強調被佔領國家的美好生活」的照片,怎麼能夠「不經任何解釋」就展出呢?(Buruma 2009: 161)再加上,這些照片是祖卡為當時的德國雜誌《信號》(Signal)所拍攝,以宣傳法國在德國佔領下的正面形象,讓他被批判為納粹主義份子(Nazis)。
然而,除了祖卡,許多當時的法國知識或藝文份子如沙特(Jean-Paul Sartre)和卡繆(Albert Camus),也運用相似的模式與德國達成某種程度的協作、以保全自己發表作品和言論的自由。

藉由這些例子,布魯瑪推測了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
寇克多(Jean Cocteau)和年輕的藝術家菲利普.尤利安(Philippe Jullian)一樣,並不能代表在納粹統治下的多數法國民眾。但就像他大多數的同胞一樣,他只是在努力求生存(débrouillard)。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什麼卑劣之人,他不過是去適應艱困的環境。(Buruma 2009: 165)
僅以這樣的理由去總結法國知識份子在德佔巴黎下的合作或妥協,或是試圖為他們擺脫被冠上的納粹主義之名,顯然是不夠充分的。我們所忽略的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與寇克多、沙特及卡繆等人同樣經歷了德佔巴黎時期。透過莒哈絲由伊曼紐爾.芬柯(Emmanuel Finkiel)改編成電影的自傳《痛苦》(La Douleur,台譯片名《莒哈絲的漫長等待》),我們可以在其中以不同角度切入德佔時期法國人的心理狀態。
德國佔領巴黎期間,莒哈絲偶然下認識了一位德國蓋世太保(Gestapo, Geheime Staatspolizei)拉比爾(Pierre Rabier),並藉由與後者的聯繫來打聽被逮補至集中營的丈夫侯貝(Robert Antelme)的下落。1944 年,莒哈絲與拉比爾進行了最後一次的會面。作為整部電影進行一半之處的分水嶺──法國解放前夕,同盟國迎向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這個段落對於理解莒哈絲、乃至於法國人的精神狀態,是相當重要的。除了不同於前幾次兩人的單獨會面,這次的邀約由莒哈絲提出,且莒哈絲在這次的會面中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的確,如布魯瑪所述,以及派翠克.布桑(Patrick Buisson)在《1940 - 1945 情色的年代》(1940-1945 Années érotiques: L'occupation intime)中所提到的,許多法國女性在佔領期間與德國人建立情人、或者肉體關係,以藉此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或者如我們在猶太裔小說家伊雷娜.內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的作品《法蘭西組曲》(Suite Française)及其改編電影中所看到的:許多法國女人在德軍佔領法國後,投向了德國人的懷抱,並對於法國男人的戰敗感到羞恥與憤恨。我們若不仔細地探究莒哈絲與拉比爾保持聯繫的動機,很容易便會將莒哈絲歸類到這些自願對德國人投懷送抱的女性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