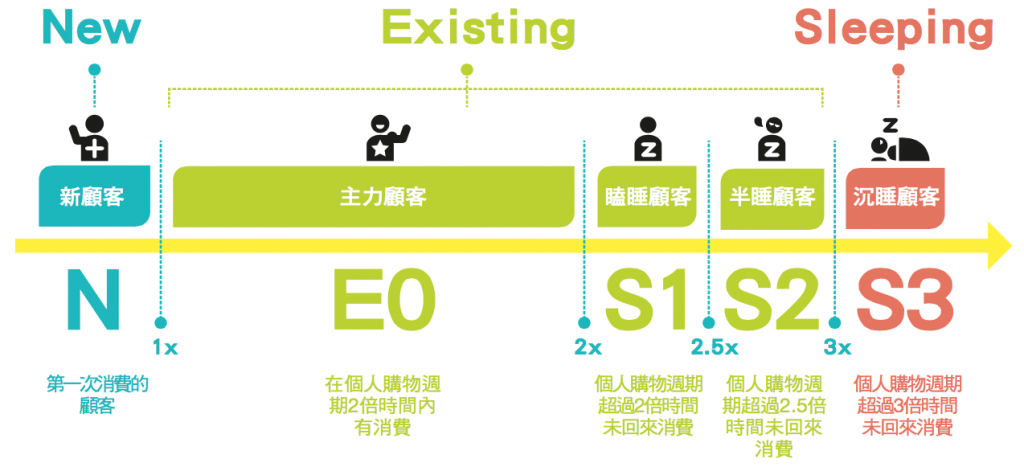完形肉義肢(一)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從診所下班後,偶爾會來到這裡,忘了是大二還是大三的時候,一樣是在這家咖啡店。
那時隔壁桌的客人哪,點了杯血紅得驚人的飲料,一根比焦炭還要黑的吸管就插在浮冰中央,我手托著歪鈄的臉看到入迷,立即陷入腦霧那種無法自拔的膠著裡,不只這樣,那彷彿想證明自己有多粗壯的透明玻璃杯,邊緣還掛著一片黃澄澄猶如大耳朵般的柳橙切片,仔細一看,碎冰上還倨傲著一片小花瓣,那簡直就是剛從花螳螂臉上剝落的豔麗殘殼面具。
「看來有人遲到了。」
開始等得不耐煩了吧,我還以為她一點也不在意呢,畢竟人是她約的,會不會迷迷糊糊約錯了時間或是地點了呢?我在心裡訕笑,搞錯赴會地點這種事發生的幾率有多高呢?反正我是不排斥待在這裡像無所事事的閒人那般,漫不經心啜飲咖啡,把自己攤在大片窗戶下讓陽光錯落進來盡情曬在身上,也不排斥被一圈圈熱帶植物般我也叫不出名字的室內盆栽擅自把人給埋沒起來,畢竟它們就像是下午時段客廳裡的狗狗阿,貓貓阿,或常翻身不順遂的巴西烏龜,總是安祥溫吞窩在一處,根本比人還要懶啊。
「原來是位大牌導演!」
沒差吧,意識漸漸潰散,睡一下無妨,我心裡不停這麼想,直到似乎有人用手肘戳了我(她動用全身最硬的部位像木棍那樣頂著我的肚子)。突然眼前不遠處出現有個人雙手撐著前臂式拐杖,上半身相當壯碩,肩膀厚實,手臂有我小腿那麼粗,但下半身卻萎縮得瘦瘦小小的,他緩緩走向我們這桌,伴隨著某種節奏那是腳下輔具磨擦地面的聲響,匡啷匡啷一段一段的厚實步伐逐漸靠近,我不由得正襟危坐。因為,那身影熟悉得就像是在街上巧遇到無法怠慢的親人般,使我整個腦袋都清醒了。
沒人料到拍攝這部叫「完形肉義肢」的紀錄片導演,本人罹患小兒麻痺,她那不耐煩的臉色瞬間消散,全身站起來表達著歉意,「實在抱歉,導演先生,應該和您約在一樓就好了」,連我也不得不陪著躬身說幾句話,可是呢,又不知道要說什麼,只好說實話嘛,「很抱歉,我家光碟機突然故障,那部關於肉形義肢什麼的,阿,其實是因為各種無法掌握的原因,我還來不及先看過您的大作,總之,十分抱歉。」我在心底確實是這麼說了喔,只是喉結突然腫成核桃,讓我發不出一絲聲音。
偶然認識一位正在復健科實習的學長,曾經陪伴一位右腿截肢的年輕女孩做了半年的復健,後來喜歡上人家,不料對方卻說:「可是我並沒有打算一輩子都在復健耶」,學長問我這話是什麼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阿,俗話說,只要條件具備,沒有什麼不可能,可是呢,截肢女孩與復健師直立人在醫院相遇,這樣的情境設定,很難成為愛情的起點,你問我為什麼?就像這位身障導演拍攝身心障礙人士的題材是很順理成章的吧,可是一位直立人想要進入身障的世界,是需要「正當理由」的,不是隨便一句我想關心對方就可以成立的喔,他們已經是另一種人類了,導演用科幻元素當作配樂,我想啊,是相當有自覺的呢!
「 導演使用科幻調性的配樂,是為了搭配像是機器人造型的仿生義肢嗎?」她提問了。那麼導演會怎麼回答這個無聊的問題呢?
「嗯,我的紀錄片是在探討肉義肢的存在論理。」導演會這樣回答吧。
「那麼什麼是肉義肢呢?」既然如此,她也只能這樣提問吧。
不過啊,她必定會逞能:「 那是一定的。這個說法是來自那位下半身癱瘓的女公務員,她說車禍之後做了二年復健,可是,下半身還是完全動不了,就算先生進入她的身體也不太有感覺,只能從對方的動作節奏想像若有似無的訊號,這種演戲的性生活讓她十分厭倦......」
那個畫面大概就是她描述自己很像情趣娃娃任人擺佈著,整個下半身都是虛空的存在。她受訪時坐在輪椅上拍著大腿自嘲說:「我的義肢是用肉做的喔!」,可是肉義肢完全不實用,甚至無法撐起自己的身體,它只是看起來比較完整罷了(還不時萎縮著)。為了度過那段扁平黯然的被動時光,她不時玩弄著自己的長髮,用一種十分平淡的眼神觀察著對方,突然自言自語起待會晚餐要吃什麼:「披薩嗎?」沒有想到對方竟也溫柔搭著腔:「好啊墨西哥辣醬口味,可是要很辣很辣的喔」,那畫面好像情色電影的一幕,男人奮力擠壓女人身體,可是音軌的部分像是從另一段完全不相關的影片截取下來的日常對話:「怎麼樣?你想吃咖哩香腸義大利麵還是酪梨沙拉三明治?我想喝啤酒,那妳呢?一樣是蘋果氣泡水嗎?」脊椎一旦受損,靈魂和身體就不再同步了,像是影像軌和聲音軌已經分離的影片,變成蒙太奇剪接的預備動作,要嘛就替換一個新的靈魂,不然就找一具新的身體。
他們的心阿,像一張紙被揉成結結實實的一團,已經「完全變形」了,像是個新造的人,重新用前所未有的實在感活著,和這樣的新人種相比,一般人倒像是漂浮在空氣中過著虛幻的生活。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