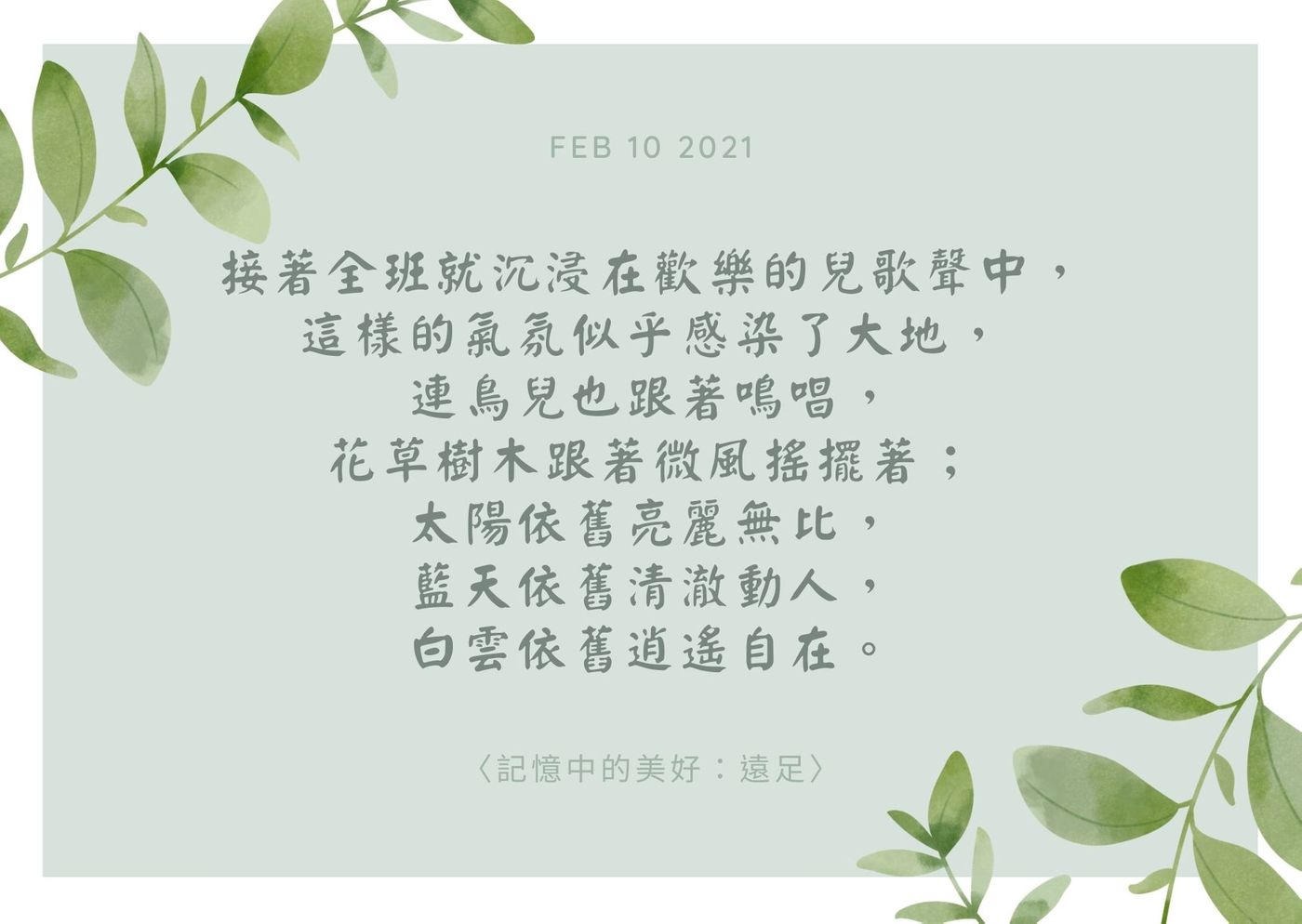佛洛斯特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未行之路》:
「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只可惜我不能都踏行∕身為一個旅人,我佇立良久∕極目眺望一條路的盡頭∕看它隱沒在林叢深處∕然後踏上另一條,差不多∕或許可以稱為更好的路徑∕因為它綠草如茵邀人上路∕然而若有人跡∕兩條路恐怕相差無幾∕當日清晨,兩條道路皆是∕滿佈落葉無人踩踏∕喔,另一條留著改天再走吧∕其實我明白,路是無盡地延續∕豈容有回頭機會∕或許多年之後,在某處∕我會輕嘆一聲說∕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較少的那條∕使得一切變得如此不同。」
以前,在談到我為什麼會棄醫從文,走上一條「罕有人跡」的路時,我總喜歡舉佛洛斯特的這首詩。人生總是會面臨或此或彼的選擇,不管你「為什麼」選擇踏上某條路,結果都會截然不同。但我並不認為某一條路就一定比另一條路來得好,只是在不同的路上你會看到不同的風景、有不一樣的感受。我在讀小學時,就有過一次「走不一樣的路」的特殊經驗:
小學四年級時,班上來了一個塊頭很大的留級生。第一次看到留級生的具體形貌,令我相當好奇,而他似乎也對我這個模範生相當好奇。
有一天上下午課,他十二點鐘未到就背著書包出現在我家門口,支吾地說想跟我一道去上學。「我媽媽說的」,他不好意思地望著我,似乎身不由己。我惶惑地問我媽媽怎麼辦?母親說;「你就跟他去吧!」於是我趕快吃完飯,跟他一起上路。
一路上我們很少說話,走到軍眷區時,他指著一條巷子說他家就住在裡面,我隨意望了一眼,心想:「他先到我家再到學校不是更遠了嗎?」但卻不敢問他「為什麼」。
以後遇到上下午課的那個星期,他總是先到我家來等我。我慢慢跟他熟了,覺得留級生也是蠻可愛的,而且他一直對我很「恭敬」,我不再像原先那樣緊張,兩個人很快地建立了少年友誼,但我還是不敢問他「為什麼」會留級。
有一天,當我們走出雜亂的軍眷區時,他指著右側的一條小路說:「從這裡走也可以到學校。」我望過去,只看到小路夾在一望無際的金黃稻穗中,似乎通往天邊。
他說:「我以前都走這邊。」也許是基於少年的好奇,我遂跟他偏離一向走慣的正途,而走入田間的小徑。正午的烈日當空,一棵大樹屹立在田埂上。他說:「有一個眷村的女人晚上跑到這裡來上吊,舌頭伸出來這麼長!」說著用手在下巴一比,做出可怕的模樣。我如臨深淵地走過那棵大樹的陰影,不敢再回頭,怕一回頭就會看到樹上有一吊死的女鬼在那裡幌動。
我們更深入田間,竟然走到有一間破茅屋和一口古井的空地上。一個阿兵哥在井邊穿好衣服正欲離去;我好奇地往井裡一望,井並不深,裡面的水還相當清澈,阿兵哥顯然是剛剛在裡面洗過澡。
「這裡不錯吧?」我同學放下書包,問:「你會不會游泳?」我連忙搖頭,心裡還在摹想樹上吊死鬼的形影,這井裡總不會也有個溺死鬼吧?他一邊脫衣服一邊說:「要不要我教你游泳?」我連忙又搖搖頭,於是他自個兒脫得光溜溜的跳到井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