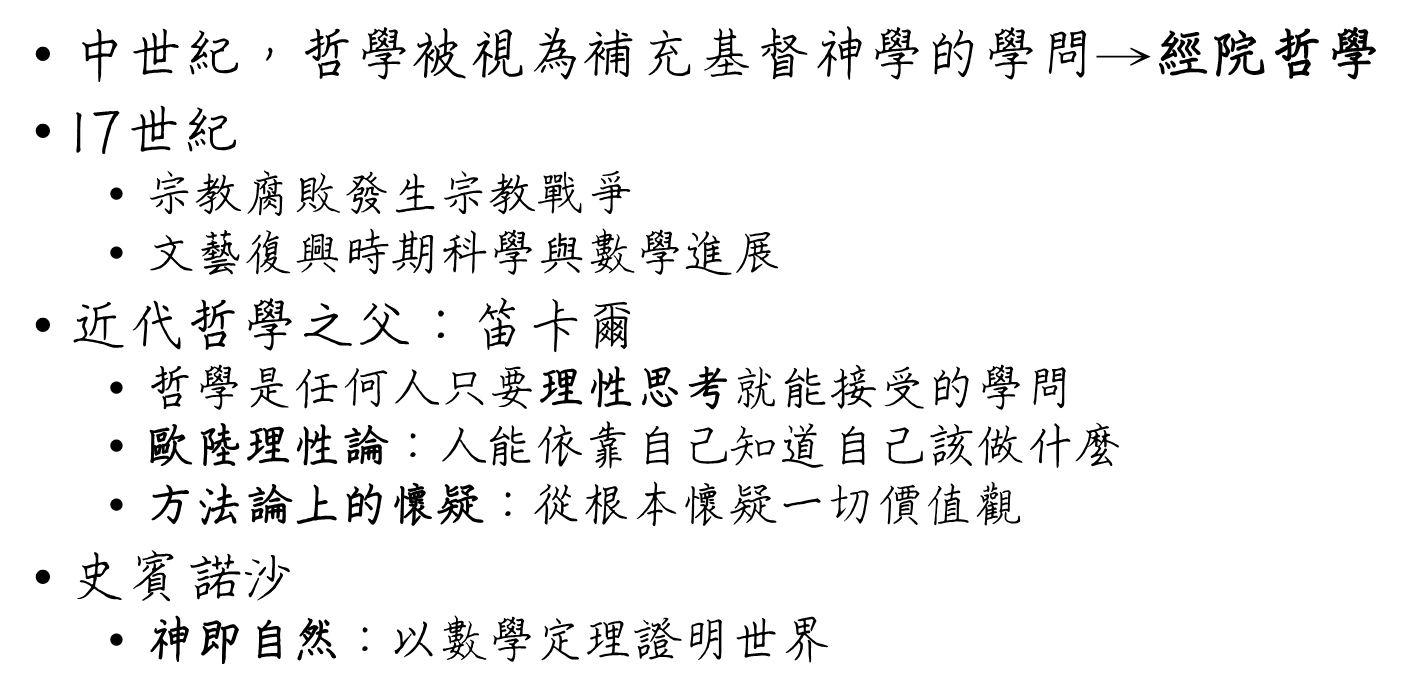至少在兩千多年以前我們就已經能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發現一種對政治的「超越性」想像,這種想像訴諸的不是現成的律法或習慣,而是去追問怎樣的政治才是真正好的政治,人類也因為這樣的追問從現實的動物演化成理想的動物。然而,隨著人類在不同的處境中演化,那所謂的「理想國」也不再是柏拉圖在作品中所揭示的樣態,人們會因為在現實中遭遇到的困境而改變理想的圖像,正如同早期社會的官僚共產制度也有可能在二十世紀因人們遭遇極權主義的暴政反而轉向追求一種由社區自然演化秩序、反對由國家政治代表的人類社群制度。不論人類的理想在歷史過程中是如何變來變去,那理想卻總是存在的,因為只要可能性還在人類就不可能放棄生存與追求幸福的本能,而這種追求生存與幸福的至善過程也會被每個當下嘗試追求的人們加以神聖化、理想化,成為一種具有方向性的精神動力。
在奧古斯都的《上帝之城》中有一種倫理觀念很完美的表述了人類追求至善的精神動力過程:人類處在一個受到地上有限、不斷腐敗的國度所制約,基督徒做為世界的光、人類中的鹽,必須力求自己脫離地上之城的束縛,向著上帝之城的方向走去,他們生命的過程已就是不斷分別、不斷做聖的的過程,唯有堅持這樣的倫理心志才能讓基督徒確信自己才是那駱駝穿針、能蒙主恩的少數,在塵世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這種倫理心志結合了柏拉圖理想國的政治觀念後遂產生出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有重要的政治運動場合中都能觀察到的心靈–行動倫理。現代的政治行動往往具備一種彌賽亞式的歷史敘事,它許諾任何抱持著某一政治世界觀的人們只要能循著那個至善的終極圖像,便有可能在一個時間過程的末端得到彌補當下政治所造成的缺憾的救贖。這種政治倫理觀並不限於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民族主義,甚至到二十世紀後期流行的全球化普世主義、進步主義、個人自由主義。它們無不要求政治行動著們遵循的一個被許諾的圖像的滿足行為的動力和正當性的判斷。這樣一種倫理態度會要求行動者必須要放棄當下讓自己感到匱乏的政治環境,轉而向能夠彌補這些匱乏的政治方向或總體圖像。即使是那些以為自己是就事論事的人也是沉浸在一種「這一件事非這麼做不可」的心靈動力當中,於是「這一件事」也就被加以神聖化、正當化為同往至善的必須過程:必須做這一件事,所則無法脫離當下的困窘處境。
二十世紀隨著大眾民主的發展,所謂的政治不再只是中世紀王公貴族的「家政」遊戲,而是總體的人們在變化萬千的世界中要求把握自身幸福的意志體現,這種意志不再是日常互動中平易近人的合作、衝突、交易與對話,而是一次次為了追求自身各種救贖而不斷與世界對抗的過程,任何的行動都是為了通向彼岸,通向時間的終點,通向那個讓自己感到救贖的國度。也因此,二十世紀的大眾民主政治並非只是個人與個人間的交錯連橫,而是信仰與信仰的對決,是我方與敵方的對決,是理想與現實的對決。這種集體心志的作用過程所造成的巨大推動力和破壞力,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史中已經有了許多的見證。但是,不論身處在這個時代的個人們喜不喜歡這種政治模式,它都不可能與我們現在所仰賴的這種文明生活脫離,這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得不面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