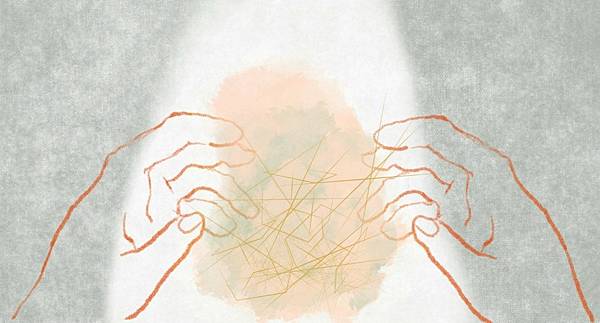文/謝宜恩(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志工)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自110年來,舉辦不同身分別的家屬聚會。本文由聚會帶領工作人員整理,試圖描繪精神疾病子女的樣貌。
一、情緒的強度與複雜性
如何理解/想像精神疾病子女的經驗,比較或許是一種方法。
在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最主要的三大服務群體:父母、手足,以及子女中,若以情緒的強度與複雜度來看,父母多半屬於高強度、低複雜;手足呈現低強度、高複雜;而子女則是高強度、高複雜。
跟精神疾病子女工作的這幾年中,我們歸納出在他們生命中幾種最常見的情緒:憤怒、孤獨,以及恐懼。沒有這樣經驗的人或許很難想像,特別是對從小、甚至是出生前父母就生病的子女來說,他們所經歷的童年,與多數人都不同,可能會思考「我可以帶同學回家玩嗎?」:同學遇見生病的爸媽,之後會用異樣的方式對待我嗎?「應該要照顧我的爸媽卻變成我要照顧」:親子角色的易位,自小就要背負與人不同的責任,諸如此類,對於自己的家庭感到懷疑、對父母的病感到憤怒;但同時,這又是一個不能講的「秘密」,我與他人不同,但我不知從何學到這是無法言說的,在這個辛苦的狀態,無法分享,產生了很強烈的孤獨感;最後對於未知的恐懼、自己是否也會生病的恐懼、對於自己越來越像「那樣的」父母的恐懼,種種情緒複雜之高、強度之大,使得身為精神疾病子女的經驗這麼的獨特與受苦,更詳細的說明,我們將在下篇文章中再述。
二、精神疾病子女的性別
從我們專線的來電中,接觸到的照顧者與家屬以女性為主(約占七成),舉辦的家屬聚會,以手足為例,50位手足中僅有5位男性,可見在服務的現場,男性時常隱身或缺席。然而,我們這幾次帶領的子女團體與聚會中,有將近1/3到1/2左右的男性,男性比例相對偏高,令我們感到很好奇,是甚麼讓這群「兒子」受到陪病所苦後,願意出來尋求協助,這些男性子女與其他男性家屬/照顧者又有甚麼不同,為什麼他們得以現身?這是我們目前仍然沒有答案,卻持續想要關注的面向。
三、受苦的特質
如上方所述,如果從小父母就生病,這群子女會展現出一些受苦的特質,包含:早熟、敏感、體貼、察言觀色,以及親子關係糾葛 。
若是從小就需要懂事,甚或需要擔任照顧者的角色,「早熟」特質或許是必然,被迫提早面對成年後才需要面對的課題,這群子女的受苦,來自於不一般的童年。相比之下,精神疾病父母或手足的狀態與子女就很不同,反而更常見的是「失落感」,那個生病的家人變得跟以前不同的失落,但精神疾病子女較少經歷這個「轉變的適應」,因為他們從小面臨的就是已經在病中的父母親。
隨著早熟而來的,多數子女也都會擁有敏感、體貼以及察言觀色的特質,這些看起來正面的特質,其實都令人感到心疼,子女像是一群帶著4K畫質在觀看世界的人,能看見與感受很多細微的情緒,同時也時常因為資訊量過大而回頭導致情緒與生活的負擔,這些都是從小陪病中練習或學習而來。我們同時也能明顯的感受到帶領子女聚會與其他聚會的差異,很多時候子女的經驗分享會讓人感到沉重與緊繃,我想那就是他們受苦的生命厚度所帶來的氛圍。
親子關係糾葛則是會展現在對於父母的又愛又恨,也有許多子女處於與父母的矛盾依附關係中,好像這個生養我的人,我需要愛他,但我又擁有太多說不出來的痛苦,好像找不到正當性或立場去「恨」。這些複雜的關係與情感,是身為子女的苦楚與困難。
四、總結
精神疾病子女少在精神衛生系統與服務中被關切,然而,這個群體走過的路,我們都能看見受苦的痕跡,若是有機會多談一點、多聊一點,讓我們對於子女的認識與想像更多元,或許我們能夠更支持到這群受苦的孤獨者。
系列文章參考:
【誰是精神疾病手足】─手足樣貌圖像I:精神疾病手足家屬聚會經驗整理https://vocus.cc/article/635f751ffd8978000183c0ed
【當我成為照顧者】─手足樣貌圖像II
https://vocus.cc/article/63f3286ffd89780001b29a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