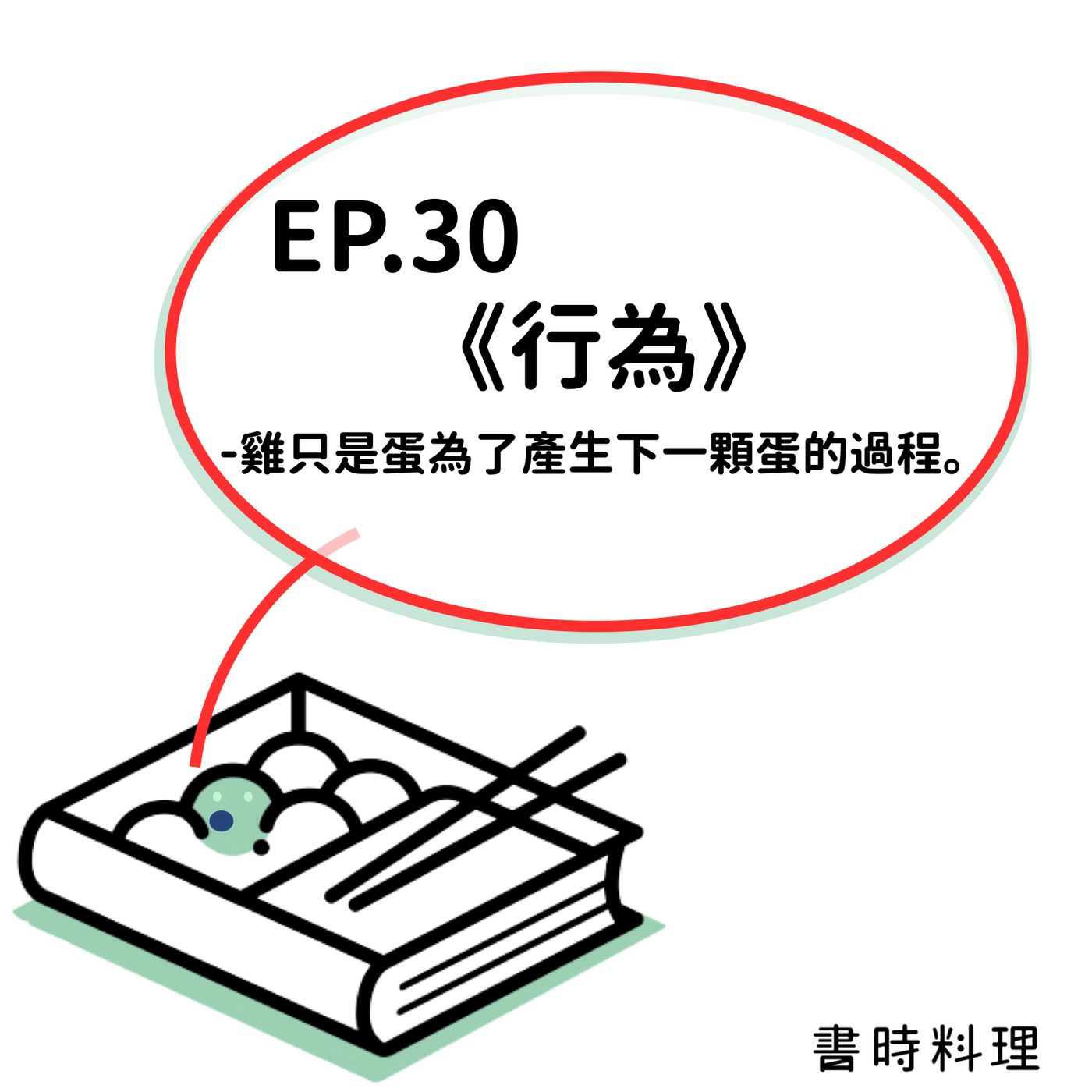「在摸索中不要追求能夠完全像動物,那是陷阱。」老師說。
開始模仿的時候,都是陷阱。就像總有些時刻不得不問自己是誰,而又類似誰或永遠,不會成為誰。生物為了擬似另一個種類或物質,是為了隱蔽或獵捕,混淆視覺,減少暴露的危險以及利於寄生。
枯葉蝶的翅膀疑似枯葉,竹節蟲的身體和四肢模仿樹枝,土螢為了捕食另一種土螢而拷貝發光的特性,花螳螂酷似花朵,吸引獵物靠近。黑隱翅蟲學習螞蟻的動作,杜鵑鳥讓雛鳥的羽色和另一種鳥類相近,可以不著痕跡地將自己的孩子寄育給牠們,不費力的奪取資源。瓢蟲讓自己鮮豔,斑蝶分泌難聞的氣味,擬裝代表毒性危險的顏色和不舒服的氣味,降低被捕獵的風險。生物模仿,都為了建立不用面對太多臨危岔路的守則,沒有餘地的用深入骨髓的方式求生。
而人模仿,是因為想要,想要看起來像別的,喪失了嬰孩純粹的習性,時常誤判本性根深的限制,變形原有的樣子,窄縮了路,所以變的處處,都是肉眼無法察覺的冰隙,一路上滿佈陷阱。
為了避開陷阱,僅能短時間的擷取局部寫實來模仿。大到一整片肩胛,脊椎的划動,小到一個指尖,一個念頭,穿過髮絲的手指,指骨滑順如蛇身,甲片是蛇鱗,都能招喚動物,在局部現身。
十個腳球貼緊地面,只是這樣,就足以抬起胯骨,四肢趴地的用和身為人完全不同的方式移動,體會到自己和動物之間構造設計的懸殊差異,遭遇的困難就像只是使用動物的特徵將自己重新組裝。
而動物面對的生存實境,全然裸裎不留餘地,所以牠們無論在躲避或捕獵之前,都會將重心壓低,蓄勢發動奔跑或跳躍,每一次發動,都是投入所有優勢的機率壓注,必須遵循最省力的方式替自己引路,容許不了些微的躊躇和失足,用生死競技。
我們也有重心,也是動物,視覺,聽辯,嗅聞,咬合和觸覺的齊全感官,替我們取捨蒐集真正重要的訊息,也可以肩負遭遇每個不同境況時,帶來的重。偶爾只能順從,或敏銳的察覺在直覺裡,如細小的電流竄發的危險警示,盡全力防禦,也會繁衍,哺乳,讓下一代繼承自己吸取的基本生存經驗,擁有最初最原始的恐懼,是一切本能的發源處。
雷馬克在《西線無戰事》裡提到本能:「你長時間訓練一隻狗只吃馬鈴薯,之後再給他一塊肉,牠還是一樣會大口咬下。這是他的本性嘛,你給人一些權力,他一樣會大口咬下。」
我什麼時候會順著本性,毫不遲疑地大口咬下?僅為了掠奪跟保全自我?刺探我何時會露爪出為了生存深植的動物性?
老師要我們在遊戲中模仿雞跟老虎走路的樣態,雞的拍翅,頭的點動,划動的爪,老虎咧齒的吼聲,四肢連動的步伐,要我們學習這兩種特徵,隨時交替轉換。
要求我們整個過程都閉起眼睛,剛開始全部的人都是雞,由老師暗中選定的人成為唯一一隻老虎,嘶吼一聲趴地開始捕獵,只要一被捕抓就必須轉換成老虎,而被箝制的雞可以在安全範圍內奮力逃脫。
失去了視覺所有的專注都凝聚在聽覺,四周都是碎步,短促的呼吸,衣物被拉扯,喉嚨裡發出低沉的吼音,還必須在混亂中斟酌躲避的策略和方位。
兩局之後我張開眼睛,眼睛周圍和眉心的肌肉都因為過度皺緊而痠疼,這繃緊來自於本能的迫使和回應,迫使我該在四週都是人而會隨機接觸碰撞的狀況下,仰賴視覺的導引,而不是關閉它,和它對抗的代價就是這陣痠痛。
在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以分析 Google 的關鍵字搜尋大數據的《數據,謊言與真相》裡寫到,我們會在搜尋時鍵入和表露建構出來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的問題。
比如一位女性可能在和一群閨密的旅行中表現得很開心,卻在空閒時搜尋「老公不在身邊很寂寞」。或在人前稱讚自己的小孩最可愛,卻在私底下搜尋「我的小孩是不是很醜?」
在一個空格,幾個字之間,這搜尋的過程裡,我們想知道的是關於自己最真實私密問題的答案,不需要任何修飾性的展演,所以只會留下,最接近自身真相底線的字句。
而我在老師要我們選擇羚羊或獵豹來做為要從傍晚工作到晚上的動物時,我直覺的選了獵豹,就算我在社會性的群體裡,表現的樣態一直都是合群馴良的羚羊,是不是在這個選擇間,我也留下了自己的本性的證據。
而本能其實一直都沒有被社會性磨鈍,如打樁般堅牢,在每個關臨生存的時刻伴隨著不同的反應,正反兩面都被本性密合,因為生存,總要面臨困境帶來的每一波陣痛,藉由每個經驗的拼湊,產出熟練轉換獵捕與看守的規則,調整比例散發秩序和蠻野,說不中聽的話或用身體去衝撞抗爭,順從滿足所有的動物性也不放棄追問其中的理由,我們就是這樣的動物。
2018/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