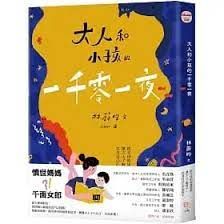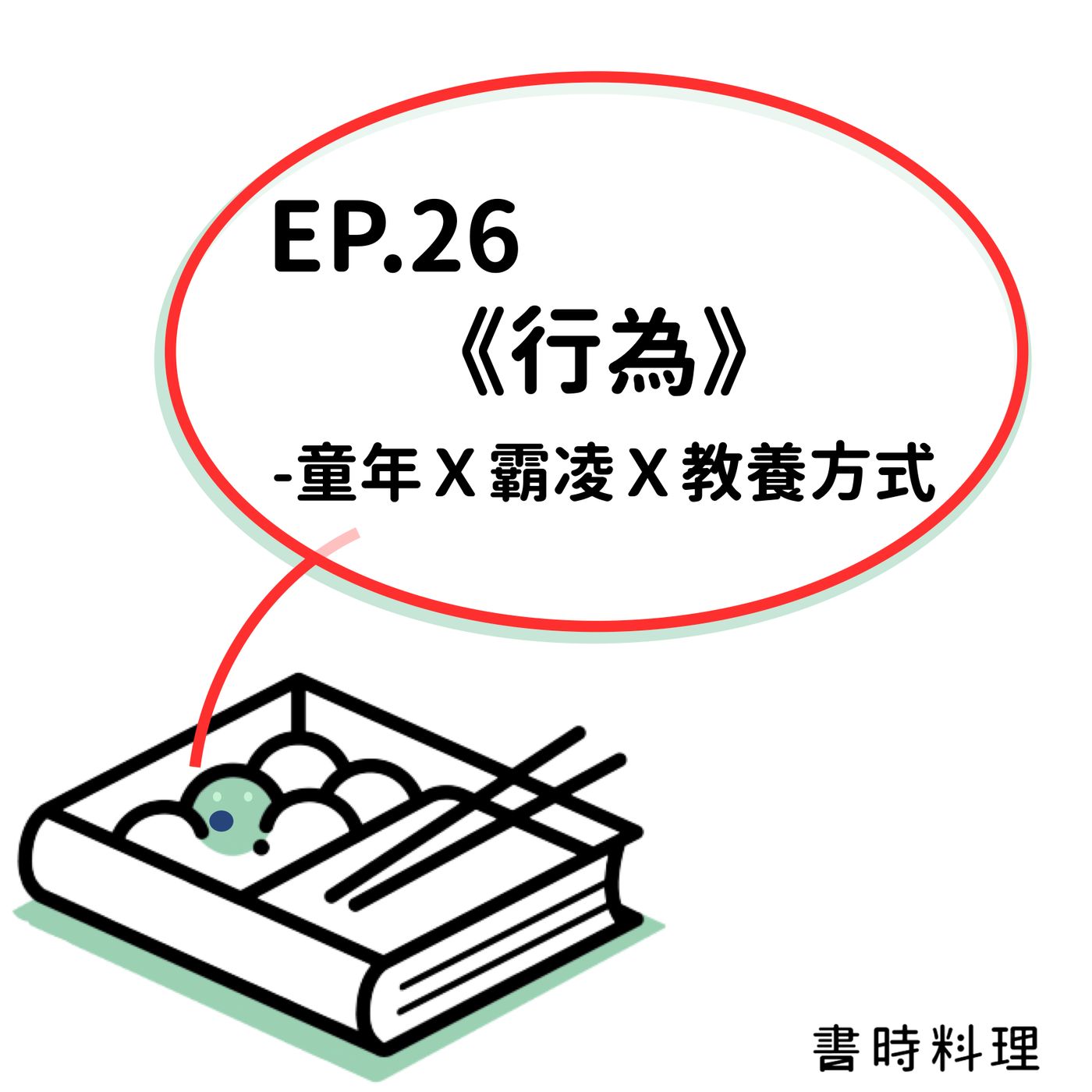從九月開始,我們合作式教育社群在竹松社大申請了一個讀書會的社團,選了幾本書共讀,一方面作為我們教育者與父母們的內部進修,一方面也開放給有興趣的朋友們。
我負責第一個月的導讀,同事們幫我選的書是溫尼・考特的《遊戲與現實》。雖然這本書我已經讀了三四遍(包括十年前我幾乎都看不太懂的那一遍),但讀書會的樂趣,就像是跟不同的友伴走進你已經熟悉的小徑裡,偶爾就會有人指出你從未注意到的某個細節。
從全能到幻滅
這禮拜讀書會的進度是《遊戲與現實》的導讀到第二章,主要的內容,在討論新生兒一出生時所擁有的全能幻覺,以及接下來的幻滅。我在這篇文章裡有介紹,在這裡節錄一段:根據溫尼考特的研究,假如一個人在嬰兒時期有一個整天24小時繞著他轉的照顧者,他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全能的。肚子餓了就有吃的,心冷了就有抱抱,無聊了就有人做怪表情逗自己笑,世界和自己彷彿是一體的。
然而隨著小孩逐漸長大,需求越來越複雜而豐富,而且照顧者大概也有點玩膩了(?),並且想起生活中還有各種不得不做的事,這時嬰兒將開始發現這個世界殘酷冷漠的一面。
溫尼考特說,照顧者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協助孩子「安全地」從這種「全能幻覺」中逐漸「幻滅」,瞭解世界不只有心想事成閃閃發亮的部分,更多的是冷漠和不回應──而那是「現實」,我們這麼形容這個世界。
過去我時常在工作坊裡介紹溫尼考特的理論,有時會有敏銳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
「如果是一出生就被遺棄的嬰兒,也會有這種幻覺嗎?」
在這禮拜之前,我認為這些新生兒很有可能沒有這樣的幻覺。既然這些孩子從來不曾被無微不至地照護過,那就不會有全能幻覺,也就不會有「逐漸幻滅」的機會。我認為這表示溫尼考特的理論不能延伸到這些人身上。
不過,這禮拜的讀書會給了我新的想法。

最早的悲劇,最早的幻滅
也許是因為男性把持的學術圈一貫漠視或貶抑女性主體經驗,也可能只是因為生理男性經驗上的侷限,溫尼考特的理論只描述出生之後的嬰兒,而沒有擴及到懷孕及生產過程。
老實說,我在讀《遊戲與現實》的時候,也完全沒有考慮到新生兒在懷孕及生產過程的經驗。所以當我在這次的讀書會裡問出「你最早的幻滅經驗」這個問題時,完全沒有料到有人會追朔到(被)生產經驗。
不過,還好我雖然經驗缺乏(而且我根本就不可能有啊啊啊),但我有讀過書。我立刻就想起《溫柔的誕生》(最早出版於1974年)裡面,費德里克・勒博耶對現代醫學生產環境令人不安的描述。
「這難道不是悲劇?」

在工作坊之後,我重讀了《溫柔的誕生》。費德里克・勒博耶在書裡放了這張照片(以及其他幾張新生兒扭曲的臉孔),試圖指出新生兒所經歷的「無人能敵的痛苦」,以及環繞著新生兒的眾多相關成人,對於新生兒痛苦視而不見的態度。
以我家的生產經驗來說,我們從來沒有從新生兒的角度去思考過生產過程──畢竟我們也是第一次,緊張得半死。於是當我讀到費德里克・勒博耶從新生兒的角度設想的描述時,讓我覺得「也太有想像力了吧!」,同時也讓我第一次關注到生產過程中的新生兒經驗:
【視覺】
當嬰兒的頭探出來,他張開眼睛。
還困在媽媽身體裡的他,快速閉上眼,小臉寫滿了無法言喻的痛苦。
【聽覺】
一旦嬰兒衝破保護層(羊水),外界喧囂地難以承受。
人生、哭聲,種種細小的聲音扎著這不快樂的孩子。
【觸覺】
粗糙的毛巾、粗糙的表面,甚至是刷子。
喔,如遇荊棘。
這小東西被放進冰冷的金屬器皿裡,當然嚎啕大哭。
而我們,開心地大笑。
【呼吸】
灼傷的感覺愈強烈,愈需要吸進更多新的空氣!這也許就是嬰兒西進第一口空氣的感受。
火焰,比什麼都還要可怕的火焰。
孩子大聲哭喊,拼命想在這惡毒的火焰中,殺出一條生路,吐納呼吸。
生命初始,孩子大聲哭喊著:「不!」
【重力】
嬰兒脫出母體的瞬間,他的腳踝被抓著倒掛在空中!小小的身體裹著溼滑的白色油脂。這樣一抓,老實說,可能會手滑、脫逃、掉落。
所以得緊緊抓牢才好。
好……對誰好?
也許我們看來合理,但孩子呢?
把他吊掛在空中,真的好嗎?
他感覺到無來由的暈眩,像是在惡夢裡,坐著電梯突然從六層樓高的地方,掉落地面。
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令人不安的描述有幾分真實性,並且其中有些作法已經不再使用(比方說把孩子倒吊起來拍打屁股),但考慮到子宮「全面照護」胎兒的能力,即使勒博耶終究過於誇大,但對我來說,光是從溫暖安全舒適的子宮離開來到這個世界,對我的想像力來說就足夠殘酷。
費德里克・勒博耶說:「生命被狠狠拒絕,在生命初始之時。」
我被勒博耶說服,同意了(被)生產的經驗可能是每個人人生中的第一次幻滅經驗,於是溫尼考特的理論也許得以延伸到每一個人身上。
溫柔的生產,逐漸的幻滅
大概是從電視劇來的刻板印象,對於生產,我也有「把小孩倒吊起來打屁股,讓小孩大哭出來」的畫面。
回想我家小孩的生產過程,護理人員應該是沒有把小孩倒吊過來,包巾應該也是盡可能柔軟的產品,但跟子宮比起來,必然也是相形失色,更別提光線、聲音,以及生產過程中各種必然或不見得必要的刺激。無論如何,我從來沒有如勒博耶那般,從新生兒的角度去考慮過。
在我家小孩出生兩三年之後,我才接觸到溫柔生產的社群,認識了幾個推廣溫柔生產的朋友,以及幾個在家生產的家庭。在我的印象中,他們從女性與新生兒的角度與經驗出發,重新建構溫柔生產的環境。
然而,當我為了寫這篇文章去詳細閱讀網路上溫柔生產的文章時,卻發現大多數的介紹都著重在女人身體的自主權上,而鮮少提到新生兒的權益與(可能的)經驗。
我覺得奇怪,便寫訊息去請教在推廣溫柔生產的朋友(這位朋友也同時推廣兒童人權),她向我解釋,台灣目前在溫柔生產的推廣狀況,連女人的身體自主權都十分艱辛。如果連媽媽都難以決定自己的生產過程,那麼更加弱勢、無法為自己表達意見的新生兒,就更不會被考慮到了。不過,朋友也提到,在國外已經有許多研究與文獻考慮到新生兒的經驗了。
即使如此,溫柔生產的生產環境對新生兒來說無疑是更加友善的。像是盡可能採用柔和舒適的光線、減少不必要的聲響、讓新生兒盡可能多接觸母親,以及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行為。我知道一個朋友選擇不為女兒剪臍帶,讓她的胎盤掛在身上三四天才自然脫落(朋友把胎盤比喻為「行動電源」)。
因為我們不太關心新生兒的經驗,使得我們對新生兒的理解很少,少到我們不太知道新生兒的經驗到底是不是糟糕的,或者到底有多糟。因為那麼缺乏理解,對我來說,接納勒博耶的想像就不是什麼壞事──
假如我們可以減少新生兒可能有的痛苦與恐懼感,為什麼我們不試試看呢?
因為費德里克・勒博耶和許多人的倡議與實踐,將會有越來越多新生兒得以被溫柔地陪伴,好好地度過人生的第一個幻滅經驗。溫尼考特爺爺要是知道了,應該也會覺得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