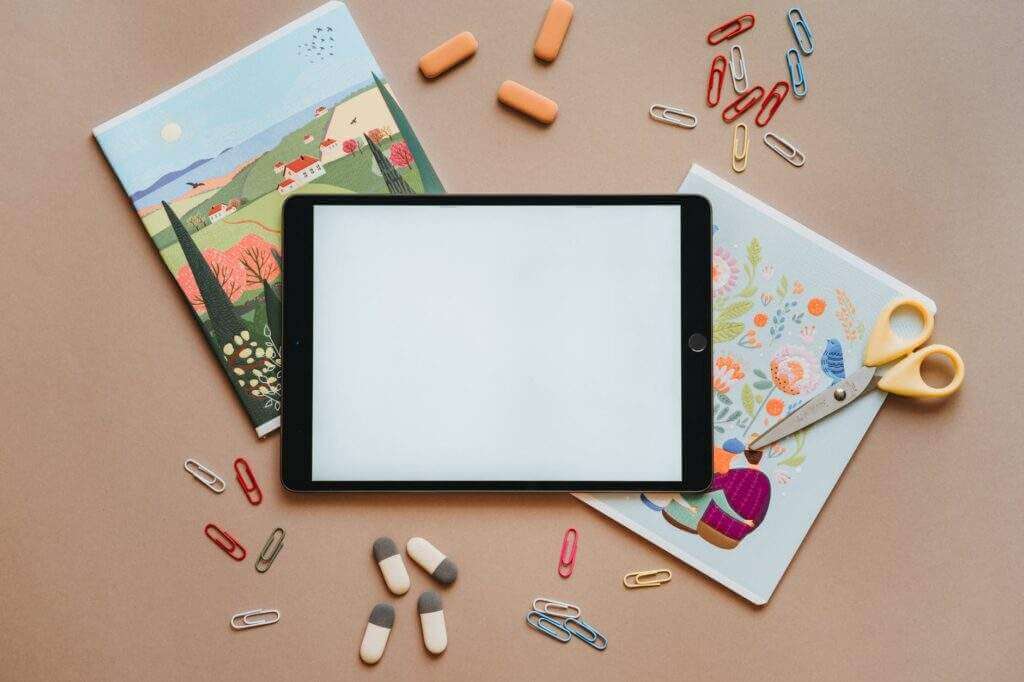「他們的頭腦和我們的不再相同。」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這位法國哲學老爺爺,在《拇指姑娘》這本書裡這樣說。
老爺爺注意到,新一代孩子們的專注力「被成人播放的媒體細心摧毀」,孩子們接觸到的訊息越來越短暫而破碎,書裡提到:「根據官方數據,媒體將畫面縮減至七秒,將回答問題的時間縮減至十五秒。」這是從YouTube、FB面世以來,成人世界就有的擔心,而小孩們現在已經群聚在訊息更破碎短暫的抖音,他們說「FB是老人在用的東西」。
然而,老爺爺也注意到,這些孩子將要面對的世界跟父祖輩的世界截然不同:「1900年,地球上大多數人的工作都是農耕和放牧;2011年,法國和其他情況相似國家一樣,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是農民。」書裡也提到《法蘭西學院辭典》的例子,在20世紀前,辭典的兩個版本間差異並不大,但目前仍持續更新的最新版本(第9版),會比前一版多上約28,000個新詞──而預定收錄的全部詞彙也才60,000個左右──換句話說,這部辭典有將近一半的字辭都是過去沒有的。
我要在這裡說一句廢話:這是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
除此之外,這位鼎鼎大名的認識論老哲學家爺爺更基進地表示:「我不再自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今天,所有人都(能夠透過網路與自學)成了認識論的專家。」
我沒有老爺爺這麼豁達樂觀,並不認為小孩只要透過網路跟自學,就可以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不過,老爺爺對未知的謙遜態度,我則是十分欣賞。於是對於孩子們打電動、看YouTube、使用抖音(的國際版TikTok),我打算透過教育現場的實驗與觀察去理解,小孩在這些時候,是在什麼樣的狀態裡。

實驗條件
我們在去年成立的自學社群「黑龍騎士團」,對於小孩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的方針(以下統稱為「使用設備」),是採取少管制多觀察的方式。
每週三,孩子們會帶著各自的電腦、手機或平板來到基地,在這裡沒有限制使用的規則,孩子們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來使用設備。除了我之外,現場的教育者和觀察員也不會試圖介入小孩使用設備的狀態。
除此之外,我們也知道教育現場外的條件會干擾教育現場裡孩子的狀態。比方說,如果有一個小孩在家裡完全不能使用設備,那麼這個孩子在不受管制的時候,將會有極高的使用設備的慾望。
於是我們要求孩子的親屬們,在家裡要盡可能減少對使用設備的管制,讓孩子們對使用設備的慾望降低到不受管制的狀態。
四五六年級的孩子被要求輪流準備一件他們正在投入的事物,介紹給其他孩子認識。畫插圖的孩子會將畫插圖的過程投影出來,讓其他孩子看見;研究程式的孩子,則會教其他有興趣的孩子寫程式;正在進行西點研修的孩子,則會在這裡製作點心。
在現場有一位教育者,會被期待帶來一些有趣的事情,目前比較常見的是繪畫跟逐格動畫。
以上活動的目的,是要跟使用設備一同競爭孩子們的注意力,希望孩子們可以從使用設備這件事情上,自願離開,並且投入其他感興趣的活動。
最後並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條件,是這些孩子們在其他的時間裡,也幾乎沒有參加非自願的活動或課程。
除了年紀、過往經驗的差別之外,在大約半年的時間裡,小孩加入的時間點也有所不同,小孩之間也有接觸實驗時間長短的差異。
使用設備的三種類型
經過半年的觀察,我認為我們這裡的小孩在使用設備的狀態上,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抗拒型、創造型及逃避型。
抗拒型
抗拒型的孩子,通常是最初加入這個實驗的成員。他們過去被嚴格管制使用時間,這讓他們對於使用設備有極高的內在動力。有些成員的狀況會集中到「在旁邊講話聽不見」的程度,而有些成員當你想要跟他談話時,他會下意識地回答「再等一下(就停止使用設備)。」
如果家庭裡配合取消對使用設備的管制,他們使用設備的動力會逐漸下降。最好的檢驗指標,就是他會不會為一些明顯新奇有趣的事情從設備上抬起頭來,甚至起身投入。
比方說,有一位孩子剛來的時候,連出門去玩鬼抓人都不想去;當空間裡發出驚嘆或歡呼時,他仍然頭都不抬地在自己的螢幕上。經過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他目前已經可以投入一些他感興趣的活動。
另外一位孩子來得更久,他從完全不能放下平板的狀態,到現在幾乎很少拿起平板;取而代之的是到處去跟人建立連結,看其他人在從事什麼活動。
而在我們團體裡,有兩位我知道幾乎從來沒有被管制過的孩子,這兩位孩子雖然年紀比較小,卻完全沒有經歷過抗拒型的過程。
我認為這組對比可能告訴我們,管制孩子使用設備,反而會對孩子形成相反作用的吸引力,讓小孩在不受管制的時候──比方說剛離開家的那幾年,或者成人再也管不動的時候──更加無法控制地使用設備。
反過來不做管制的話,孩子就可能不會經歷這樣的過程。

創造型
在我們團體裡,四五六年級的孩子會開始寫程式、製作劇情影片、寫社會課報告、查資料等等。這在大人看來應該毫無疑問是創造性的。
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寬容地看待創造性使用設備的範圍。我會將娛樂、生產和學習都放在創造型裡,這是因為,對孩子們來說,娛樂、生產跟學習往往是同一件事。比方說,有個孩子在看蠟筆小新時,他學到了流水涼麵的製作方法,於是他關掉電腦後,就開始找朋友一起製作流水涼麵。
小孩看完YouTube之後,模仿YouTuber去電玩遊戲裡嘗試新的遊戲、技能或關卡,我認為這也是創造性地在使用設備。當然,有許多大人並不覺得這是在學習,但這不過是跟老一輩人認為「看漫畫不是學習」同樣程度的偏見。
說起來,我認為這個對創造性使用設備的定義,其實也適用在成人身上。當我在看動畫的時候,心情愉悅的同時,往往也得到許多知識或啟發。
然而,我們也看到,有許多小孩──或者應該說,我們自己有的時候──在使用設備時並不那麼感到自己是愉悅並且有創造力的,我們並不真的那麼享受那些影音。如果你四十歲以上的話,這其實並不是什麼新的狀態,在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在這種狀態裡的人不是拿著手機,而是拿著遙控器在電視前度過一整晚。我將這種狀態孩子,分類在逃避型。
逃避型
逃避型我認為又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逃避事情,一種是逃避人生。
無論大人或小孩,有一種狀態會將「想做的事」跟「應該做的事」混淆,出於某種人生經歷,他會想要去對抗應該做的事。有這種個性的人,當想做的事情就是應該做的事情時,他會無意識地去對抗,逃避去面對這件事情。
以一個孩子的例子來說,他會興致勃勃地答應一個工作,並且朝氣十足地開工。但在他回家之後,情境轉換了,工作裡「應該做」的成分會佔據他的感受,當他要打開電腦面對這件事情時,他會生出一種抗拒感,於是無意識地打開YouTube或其他影音程式,一個接一個看下去。
這種使用設備的狀態就是逃避事情。而且在進行這種逃避時,沒有去做應該做的事情的罪惡感會逐漸升高,但抗拒的心情也同時升高。於是當事人在使用設備的時候,從旁邊看起來會是一種煩躁或鬱悶的狀態,和創造型的使用狀態截然不同。
另外一種逃避的類型,則是無意識地拿起手機,從我們的小孩看來,我認為他們是在逃避面對人生。
這種情況較常發生在成長經驗大多是「被安排好」的小孩身上,他們也許被大人安排了許多行程或活動,於是他們很少有機會問自己「我現在要幹什麼」。
當孩子小的時候,這樣的安排大都不會遭致小孩的反對,因為大多數事情對小小孩子來說都很新鮮,只要不要太糟糕,他們都可以找到樂趣。但隨著孩子逐漸長大,許多事情都不再新奇,當他們需要更複雜、更精巧的學習與探索時,他們自身卻失去了尋找新鮮事物的原初動機。
再加上許多年來因為被妥善安排的緣故,也沒有培養出相應的探索技術,比方說約朋友的能力與管道、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知識與膽量、透過Google延伸好奇心的方法,這使得他們不止在動機上習慣於依賴成人的安排,能力上也無法做出自主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索。
在這種狀態裡,成人的安排如果不夠新奇精緻,小孩便輕易失去興致。此時,在百無聊賴的環境裡,如何度過時間成為一個困難的問題,而這個時代最方便的作法,便是拿起手機,投入門檻最低的社交或資訊的刺激。
在我看來,這是在逃避回答「你要怎麼使用時間?」這個問題,而這種逃避往往是無意識的。
我們的介入方法
首先,我們接受創造、逃避跟抗拒都是人可以有的狀態,即使再怎麼聰明、自主、心智堅定如鐵的人,也難免會有這些狀態。身為教育者或養育者,我們要做的是讓小孩協助小孩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做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
在面對不同類型的孩子時,我們採取相同的介入方法:協助小孩覺察自己的狀態、協助小孩列出選項並做出選擇、尊重小孩的選擇。

覺察自己的狀態
對於抗拒型或逃避型的小孩來說,將小孩的狀態正確地反映給小孩,會是首先要做的。
面對拒絕接受反映的孩子,我有時會視情況強硬要求他們接受我的回饋。我最後的優勢,就是他們對我以及這個教育場域的信任。當我判斷小孩的狀況可以接受回饋,但他們出於逃避的慣性拒絕談話時,我會設下合作的條件:「你如果希望之後繼續來這裡,你現在要放下平板跟我對話。」
接著,我會回饋小孩的狀態給他,比方說:「你這一個月來,每天來這裡幾乎全都在使用設備,發生什麼事情你全都不曉得。是這樣嗎?」
當我跟小孩還沒有充分信任感時,小孩會展開辯論模式:「我沒有,我還有看到OO或XX。」但如果小孩相信我是來幫忙的,他會停下這些辯論,正確理解我的意思,而不跟我爭辯一些枝節。
接著,我會跟孩子確認,這是否是他們真正的願望:「這是你想要的嗎?使用設備一整天,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雖然抗拒型的孩子會說「對,我就想要打一整天」,但這是他對我信任還不夠充分的緣故,他還是把我當成想要來管制他的人。但當他選擇要打一整天,他就真的打了一整天不被我管制時,他開始相信我並不是要管制的人,真誠的談話就有了機會。
在我想來,抗拒型跟逃避型的孩子,身處於一種不自由的狀態,這違反了人想要追求自主決定的內在需求。
在我們的現場裡,所有的孩子都想要投入其他的創造性活動裡。
不過,想要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則是另一回事。
列出選項
當孩子們覺察到自己的狀態與意願時,他們會想要知道還有什麼選項。這時,小孩有多少能力、環境裡有沒有充分的選擇,就是小孩會不會脫離逃避或抗拒狀態的關鍵因素。
大多數沉迷於使用設備的小孩,在南方澳的大海面前,都會放下設備。當環境過於無趣,缺乏探索能力的孩子會逃進網路裡,好避免回答「我要怎麼使用時間」這個亙古的人生難題。但我也見過一個即使在大海前仍然要使用設備的孩子,而這個孩子在家庭逐漸放鬆管制,並且增加環境刺激之後,也逐漸走出抗拒型的狀態。
以我們的教育現場來說,大孩子們會帶來他們正在研究的事物,由於是與自己年齡相近的人所帶來的成果,對孩子來說比較接近「我想要的話,應該也可以做到」的程度。而教育者除了自身的專長之外,也會安排具有不同專長的「職人」來現場,增加孩子們能夠有的選項。
另一方面,我們也試著培養孩子們自主探索的能力,比方說由孩子們互相傳授技術或知識,培養孩子們自行搭車、自行報名參加外部活動的技能與膽量等等,來增加孩子們的選項。
尊重孩子的選擇
即使做了這麼多努力,孩子們仍然有可能會選擇抗拒型地使用設備。這時,如果我們接受孩子的抗拒,孩子就會相信我們在前面所做的談話,是為了協助他而不是為了控制他。那麼,在下一次談話與選擇時,他就會更願意和我們合作。再加上解除管制、增加刺激、培養探索能力的作法,此消彼長之下,至少在我們的現場裡,孩子們都逐漸減少抗拒型使用設備的時間。
而逃避型的孩子,則是在每一個情境轉換的時候,會無意識地投入設備之中,就像許多成人那樣。在他們有充分的意識之後,他們需要的是適量的提醒,而過量的提醒將會看起來更像是管制。除此之外,豐富的刺激以及能力的培養也同樣重要。當外在刺激不足或孩子能力尚未充分發展時,我們也要接受孩子們選擇逃避的狀態,以免從逃避型轉成更為退化的抗拒型。
在我們的經驗裡,小孩比較明確出現轉變的時間點,最短是在加入團體兩個月後,有些則是大約半年後。這其中因素有許多,比方說小孩的成長經驗、教育者的成熟度、教育現場不同時期擁有的資源量,以及其他很多可能的因素,都會有所影響。
但總的來說,協助孩子覺察自己、協助孩子做出決定、尊重孩子的決定,這樣的原則是一致的。
我們不管他們的腦袋
「他們的頭腦和我們的不再相同。」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這位法國哲學老爺爺這麼說。對許多成人來說,這似乎是個嚴重的問題。
但對我們這些教育者來說,其實還好。
「他們的頭腦和我們的不再相同。」
「沒關係,我們本來就沒有要他們的頭腦,跟我們的一樣。我們在乎的是,他能不能往他想要的地方前進。」
最後要特別強調的是,以上提到過的原則,並不是讓小孩獨自去面對自己的困境。當有一個孩子想要離開逃避的狀態,他可能需要一個明確的規則,以及與規則相應的提醒。在這些時候,規則是用來幫助人去做到想做的事。
以我們家孩子來說,我們有個規則是十點之後、五點之前不使用設備來娛樂,試著將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事情上。由於這個規則是我們家孩子自己認同並且參與制訂的,在遵守上就不致發生衝突。而小孩偶爾不願意遵守時,我們也絕對尊重當事人的當下的意願。
雖然無法證明,但我認為,正是因為孩子知道我們不會強迫他遵守他自己的規則,他就更有遵守規則的理由。畢竟,在最單純的情況下,人沒有理由反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