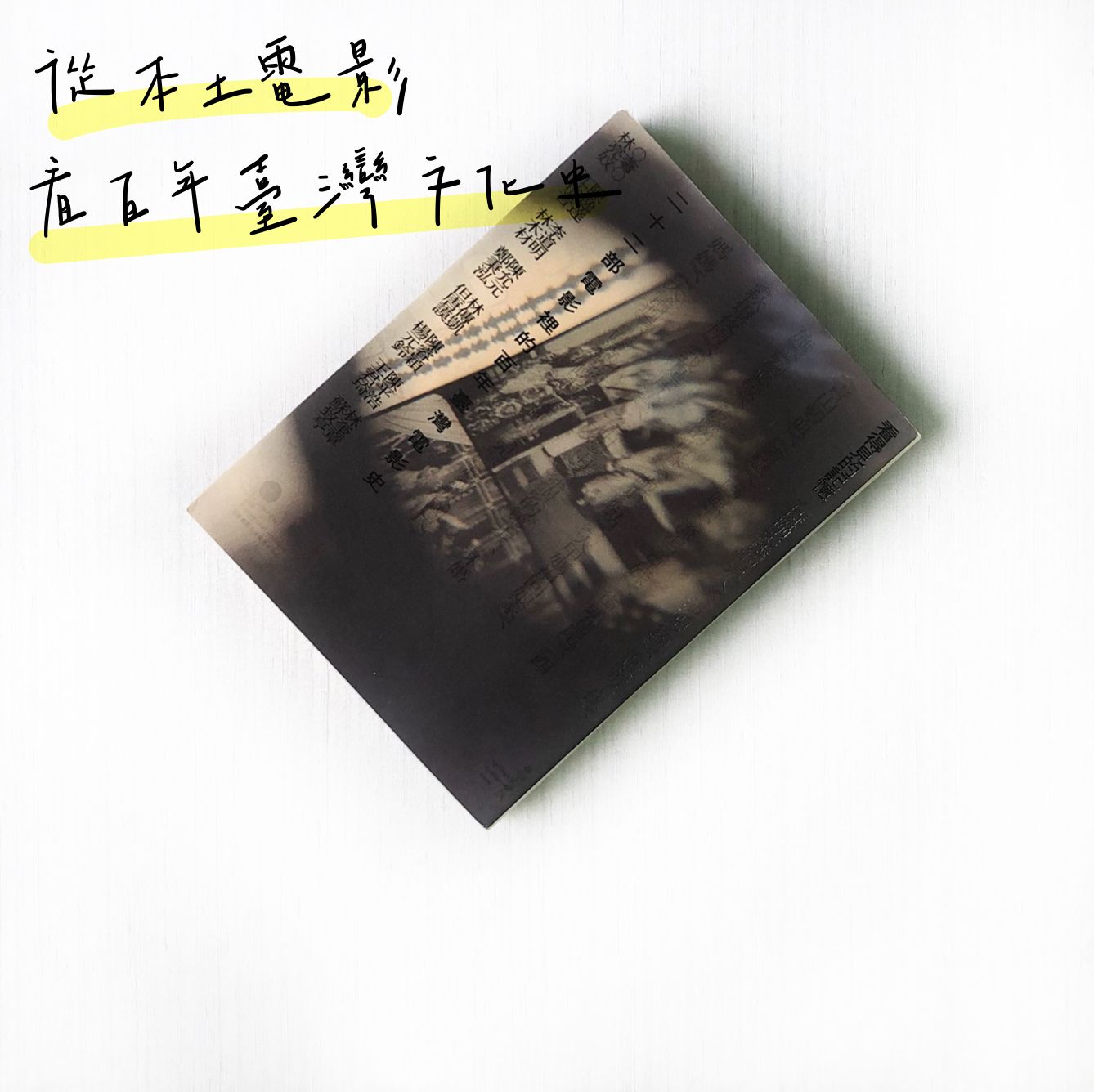2021台北電影節頗具特色的國際新導演競賽,入選的兩部臺灣代表《綠色牢籠》與《徘徊年代》,雖說一為紀錄片、一為劇情片,卻不約而同涉及個人與國家歷史,兩部佳作非常適合對照閱讀,或許這也是台北電影節選片人的巧思?
《綠色牢籠》先以片頭字幕解釋在1886至1945年,幾批外地人到西表島上開採礦坑,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人和臺灣人也曾被會社徵募,主角橋間良子是當地僅存的臺灣人,紀錄片便追隨著她一步步揭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徘徊年代》則是藉由鋪陳兩位新住民主角的際遇,展現不同年代下的新住民樣貌,再提煉並揭露片中小人物的動能與遭遇,其實與政治和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就是說,《綠色牢籠》從大歷史轉向個人史、以個人(家族)史作為西表礦坑的案例,與《徘徊年代》從關注角色本身、以臺灣為載體淡化臺越國籍邊界、最終回應國家歷史的過程,兩部作品處理的國籍、歷史問題頗為相似,只是走的是相反路徑。
而《綠色牢籠》中的美國人路易斯放棄美籍來到西表島,後來「為了體驗真正的日本」移居日本本島,與橋間良子的遭遇恰成對比;橋間從來都沒得選,沒得選父母、沒得選丈夫、沒得選職業,她身上遺留最強烈的臺灣符號:口中的臺語,總是帶著日本語尾:だよ。橋間成為不了真正的日本人,也成為不了真正的臺灣人;再回到路易斯,他看似比過去的時代更有得選擇,但他並不執著成為哪一國人,只要有異國體驗的機會,他都想嘗試。
國家的邊界就這樣被消解了。畢竟在成為哪國人之前,我們先是做為一個人被生下來的。
如果說《綠色牢籠》是以大量西表島的景色還原和追尋歷史,《徘徊年代》鏡頭所停留的臺灣風景就是它消解國籍邊界的手法。在《徘徊年代》裡感受不太到新住民的「特殊性」,所有人物被自然地鑲嵌在片中臺灣每一個場域之中,不管嘴巴說的是華語、台語或越語,生存在這個島上的,都叫臺灣人。──這裡的臺灣人並非護照定義,而是基於人道與人情。
到頭來,細究《綠色牢籠》與《徘徊年代》的歷史探問,出發點依舊是臺灣,不管是解放或再定義,黃胤毓和張騰元兩位導演的溫柔,都讓觀眾對於「國家」和「民族主義」有了更豐富、更深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