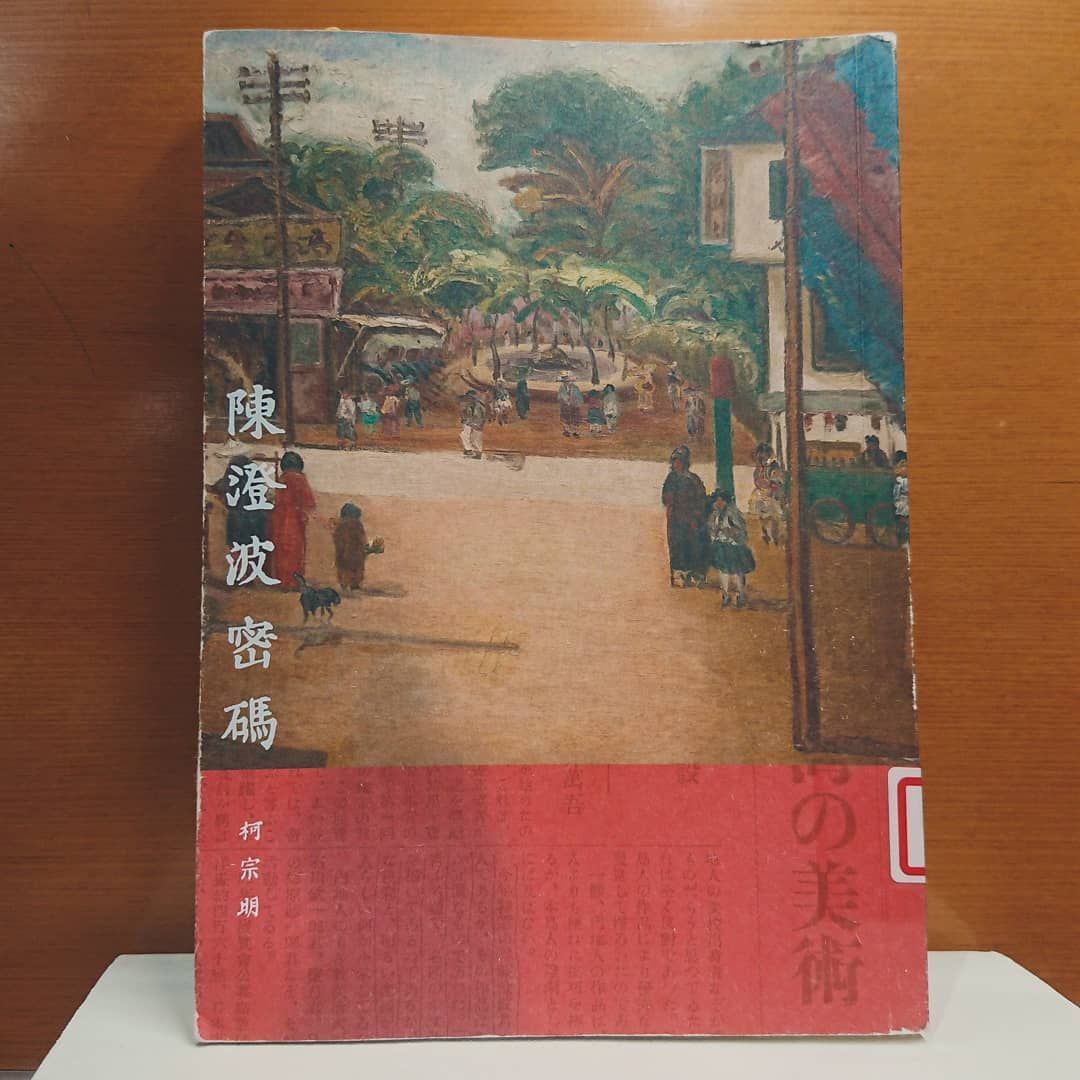趁展期最後一天跟朋友去看畫展,心靈大受震撼,還好沒錯過。
作為一介宅女,要我冒著展期最後一天人擠人的風險(所幸實際上沒有),也要去看的畫展肯定擁有無窮魅力──事實上,先後有三個人向我推荐這場畫展,他們分別是藝術版主編、美術老師、資深出版人,於是打動我的心,讓我覺得非去不可。去時幸運遇上導覽,讓我這個大外行對山水畫的美好,也能領略一二。
我驚訝地發現,原來畫作表現也有和文學寫作相似之處。若能將畫作「取景」的功力應用在寫作上,或許能「另闢蹊徑」,用更出眾的描摹技巧寫普遍的主題,創作出新的東西(個人認為,與其找新主題,不如找新視角,比較實際)。
這篇心得將簡單梳理我的收獲。
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
「我的領域是水墨創作,我從傳統步入當代的繪畫領域,就像人的成長隨著時代轉變而演進一樣的自然。」──李義弘
李老師生於一九四一年,是臺灣戰後第一代水墨藝術家。
臺灣水墨畫在一九五○年代以降,主要繼承並延續中國藝術史的傳統。李老師於一九六○年代前期進入學院,正處於以「國畫」為「國粹」的年代。
李老師一方面在傳統山水的範式基礎上,融入個人想像,作為造景依據;另一方面也遊歷四方,足跡遍及臺灣南北、離島各地,採集實景作為自創景觀的發想。他在傳統山水和如史實風景之間,揉合想像並再現景觀,造景和寫景相輔相成,鋪奠出別開生面的雙重創作途徑。
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興起,藝術界也掀起回歸鄉土的熱潮,李老師更常態地根據實景作畫,將鄉土景致繪於畫中。
一九八○年代後期,隨著臺灣社會民主化和自由開放,李老師有更多遊歷海外名勝的機會,像印度北部、喀什米爾、尼泊爾(「喜馬拉雅山」成為當時創作的核心主題),還有中國南北,乃至瑞士和美國……。
上述是我整理自導覽書的內容。
實地欣賞畫作,這些介紹連我心中十分之一的感動也無法捕捉,它們卻是相當重要的背景脈絡,直指「回顧展」的意義──藝術家畢生之作,同時聚集在某個空間,而策展人用心梳理脈絡,帶領觀眾一窺個人生命史,也乘著時代的脈絡遊歷畫家經驗過的山川風土。
有個人也有時代,有傳統也有現代,有時間也有空間,在在讓我覺得美極了。因此,李老師的作品才形成「活」的藝術,能夠感動人心。
加倍迷人的,是這般「時空的互文」不只發生於美術館展廳,更表現在畫作中。我試舉一些印象深刻的表現方式或作品。
以「空間」來說,畫家想表現崇山峻嶺何其高,與其畫出奇岩絕壁,不如以雲煙繚繞表現,使山嵐遮掩處留下無窮的想像空間,讓景無限延伸。
這就好比作家寫一個魅力十足的人物,不正面寫他有多迷人,而是藉由其他角色的反應凸顯其特殊之處;這也猶如杜甫在〈春夜喜雨〉寫「曉看紅溼處」的筆法,不把主題寫盡寫明,卻用更高明的方式淋漓達意。
再說「時間」,所有藉景物變化描繪季節遞嬗的畫作都是這麼回事,不及備載。其中,李老師以古典文學為創作發想,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王禹偁〈黃岡竹樓記〉、歐陽修〈醉翁亭記〉〈秋聲賦〉、韓偓〈冬日〉、陶淵明〈桃花源記〉等,畫出自己的四季,畫裡畫外都是時空的交織,美而又美。


此外,〈臺南孔廟〉(1978)地點雖為古蹟,李老師卻刻意讓畫中人物穿上現代穿著;還有用水墨技法畫〈瑞士山居圖〉(1983)、《鄉野偶掬》(1987),以非傳統山水畫主題的景物為題,也是同理。




在「時空」的描繪上,最讓我震撼的非〈玉山行〉莫屬;此畫若說是李老師的代表作,我認為當之無愧。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高山」是「縱」的概念,然而〈玉山行〉長達二十五公尺,畫作是「橫」的構圖。李老師採用這種表現方式,我想不只有實際展示空間的考慮,像這樣「時間/空間互相表現」的手法更讓人拍案叫絕。
我觀賞畫作時,隨著長卷畫面的推展自然挪動腳步,彷彿親身跟著李老師攀爬玉山,目睹未曾見過的高山風景。藉由植被的變化感受高度的變化;再隨著高度上升,畫中一下子有山煙彌漫,一下子有遠處殘雪的山峰,接著又有遒勁的玉山圓柏和嬌媚的玉山杜鵑……觀眾即知快要攻頂,再見綴有金色顏料的山脈,彷彿朝陽的恩慈,預示著旭日的東昇──果不其然,畫作最後,是美不勝收的日出。

我想,無論「以時間表現空間」「以空間表現時間」,都非常有趣;再想起近期寫完的小說,我不知不覺這麼「玩」起來,實在很過癮。
不過,這也要考慮創作形式的種類,無論是畫作、電影、文字、漫畫、舞臺劇……每種形式有其表現的局限,但也有表現的長處。
任何領域的創作者,形式與作品內涵一起考慮,大概算是基本素養吧。
寫景與造景‧再現與想像
作畫像寫作,就算實地取景,實際上描繪下來,已經成為「翻譯」,是一種「再創造」,這也是畫作何以不等同攝影的「寫真」。
所以,對我來說,「寫景/造景」「再現/想像」是密不可分的,取決於創作者如何詮釋,採取何種角度,又以何種心境下筆。既然創作的過程如此,那麼作品之於觀眾/讀者的影響,不只是直接的「美」的感受,更從中汲取了看待世間萬物的「觀點」。
比如我看李老師的筆下的鄉土風景,我發現我獲得了新的眼光,好回頭去看彰化老家的古厝和三合院;我看稻田和果樹的視角也變得不同了,分明是尋常之景,從小看得都膩了,現在卻因為藝術家的畫家,催生出「鄉土之美」的感受,多麼神奇呀!
還有,在〈燁燁四月〉(1988)中,畫家不用灰色表現屋瓦下的陰影,而是選用藍色,好和樹梢的紅色對比,讓白牆更顯白,也讓我著迷不已(看吧,畫畫不只是單純「寫景」而已)。這「招」用在文學創作上,肯定是十分讓人印象深刻的「映襯/對比」。

這場畫展帶給我的感動和啟發還有很多,但我最好就此擱筆,學習山水畫「留白」的精神,讓其餘的「盡在不言中」。
欣賞水墨名家李義弘老師的作品,這篇心得卻盡談寫作之事,把大師的大作做為己用,實在不好意思。只是論畫作鑑賞,我肯定不及行家,與其班門弄斧,不如以個人經驗跟這場畫展締造更獨一無二的連結。
這麼一來,當我寫作,我將恆常銘記這些畫作對我的啟發。儘管展期結束,它們依然存於我心中的美術館,光彩奪目,不墜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