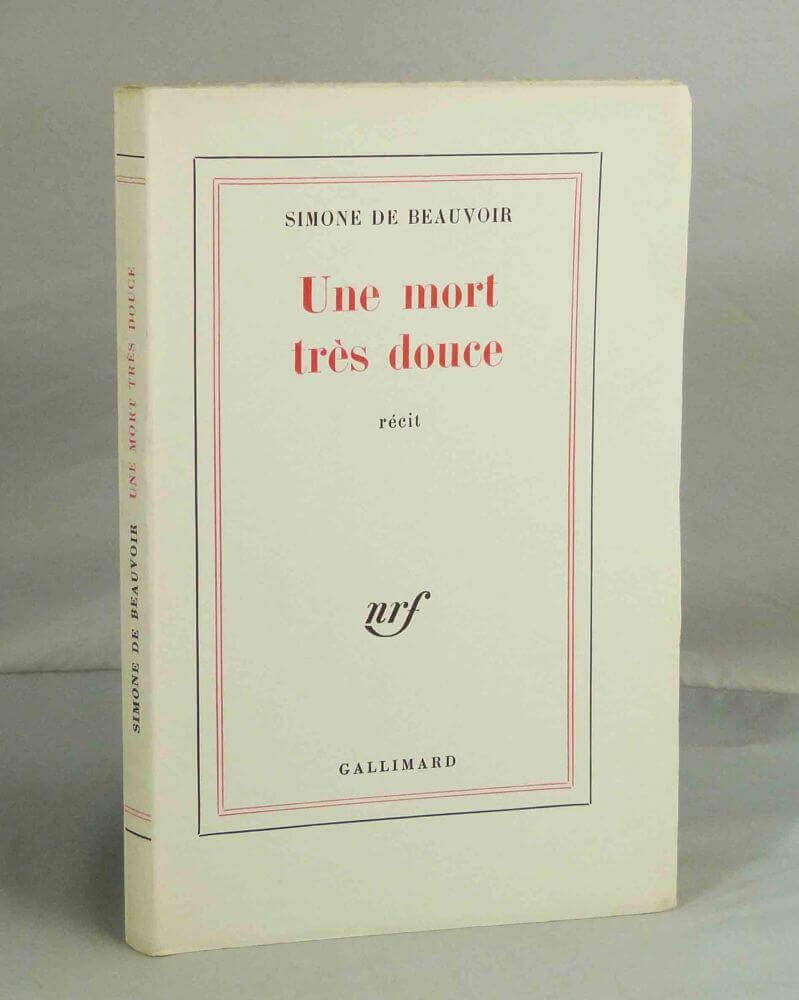一直認為傳記是很特別的創作體裁,若作者是自己,剪輯和挪用、編織記憶去完成一本回憶錄有其需要注意的盲點,一如《滅頂與生還》所提,「記憶作為工具並不可靠」,它所面臨的考驗便來自於記憶有可能湮滅消散、僵固硬化,或者根本依據自身利益重塑另一個虛構現實;若是替別人做傳,作者要如何把持與傳主間的心理距離,不過度代言藍色窗簾,亦非全然鬆散臆測,更重要的是將傳主生命視為有機自主的軌跡,而非故事或意義的變相勒索。無論是哪種途徑,書寫傳記皆非易事,特別當剖析的是哲學、藝文界擲地有聲的名字──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所著的《成為西蒙波娃》(Becoming BEAUVOIR: A Life)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於前言時便提及避免將人作為故事的載體,修正倒果為因的化約式(Reductivist)解讀,生命不僅僅是困於自身存在階層的被動客體,反而因各種經驗刺激、他人影響而持續變動,書名中的「成為」便緊扣著波娃始終相信的核心概念:「自我存有是一段不可逆的『成為』(becoming)的過程,涉及自身永不休止的改變,也涉及他人的改變。」綜觀全書,讀者的確也可從中發現波娃思想的持續生長及剝落,包括摯友莎莎的婚姻失利和逝世、與沙特非典型關係之中的其他偶然戀人,以及目睹第三世界的困境之後對痛苦有了更深沉的定義。凡此種種,皆讓波娃在後世解讀中添增歧義性,就像她常被問到能否用一句話解釋存在主義,你同樣也沒辦法對於西蒙‧波娃一言以蔽之。
女性,是眾人看見西蒙‧波娃的第一個面向。因為是女性,所以父親稱讚她聰穎的方式是說「她以男人的方式思考」;因為是女性,所以《紐約客》介紹她時所寫下的文句是「你所見過最漂亮的存在主義者」:也因為是女性,關於她的敘述都圍繞著沙特(Jean-Paul Sartre)旋轉,沙特的伴侶、沙特身旁的另一個人,如行星似陰影的附屬品。盡管她仍如此珍視沙特,外界對這段關係的態度從來都是八卦渲染大過於實際釐清,比起彼此砥礪誕生出哲學鉅著的佳話益談,人們顯然更在乎他們和各自偶然情人間的流言臆測,波娃在此的面貌又顯得更加模糊──沙特身旁的女性摯友,成為波娃一生持續對質、思索並且最終擁抱的身分。對比於先前曾出版的相關傳記,《成為西蒙波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消化了先前未公開的日記,得以一窺在遇見沙特前的波娃少女時期主要在煩惱什麼。十八歲的她觀察到自我具有二元對項的特質,「由內部看到的自我面向,由外部看到的自我面向」,此種雙面性滲透進她往後思索議題的各個角落。譬若思考和賈克間的愛情,浪漫因素很快煙消雲散,她更執著從道德層面切入,怎麼樣才是對雙方都平等互饋、而非消磨自己去成就對方的關係?怎麼樣才是真實自我所選擇踏入的道路?會從此種角度切入,或許影響自母親芳絲瓦──她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時常展現出對家庭的犧牲,而那些自我奉獻並沒有讓美好願景實現,年輕的波娃從中理解了宗教可能有的破口,上帝不一定能解釋所有事情,祂甚至避不現身,這些促使她走向了另一條名為知識的追索旅途。在此解說僅止約略,實際上波娃選擇不那麼相信上帝的過程更多曲折,這過程中的疑惑與不安並沒有少過,她花了不少經驗和心力將祂請下台階,誰會取代波娃心中空下來的重要他人?我們都知道那個名字。
波娃與沙特之間的初識沒有什麼浪漫要素,波娃最早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看見的也不是沙特,而是馬厄(René Maheu);書中也未過份聚焦那經典的、被傳誦為兩人間最高信任的開放式關係之約,然持續閱讀下去,會發現這對必然戀人的浪漫關係非常奇特:情場浪子沙特到每個國家都會陷入戀曲,偶然情人多到需要一周時間切分給好幾個伴侶,在波娃摯友莎莎的葬禮上,他也未能妥善接住波娃的情感以至於爆發爭執;同樣地,波娃自己也有多方對象,曾在日記裡寫下與自己教過的學生奧爾嘉(Olga Kosakiewicz)發生親密關係,甚至後來沙特也戀慕於奧爾嘉,關係發展成特異的三人行。
乍看之下,這並非典型愛情,不是現代神話中嚮往的那種典型忠誠。然盡管沙特與波娃處處留情,回過頭來,他們仍會說彼此是思想上最無法取代的摯友。依據旁人觀察,沙特與波娃的相處模式就是不停地說話,不間斷地溝通、闡述與反駁。的確,大量對話之所以成立,來自於雙方互持對立看法,譬若哲學概念上,沙特偏向驅除情感,認為自由之人必須克服生理性的慾望及慣性,而波娃更相信人的外在處境有其重要性,透過各種文學體裁發展存在主義中的倫理學。這些用言語相互抗辯和詮釋的過程中,誕生了他們二人的精華著作:《嘔吐》、《女賓》、《存在與虛無》……若沒有對方批評或砥礪,這些書頁內容或許就會不同。對將思考放於生命前位的人文學者而言,對話上的持續交鋒,成為他們愛情最浪漫的形式。
更廣義地說,作品脫胎自創作者的生命經驗,正因為沙特與波娃如此密切,許多作品所聚焦的主題或許正來自於此。如同波娃的哲學論文《皮洛士與齊納斯》,探討他人行動如何對自身造成影響,以道德層面去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而去解釋人為什麼要行動。如此問題脈絡,會不會來自於和沙特的非典型關係意外傷害了三角關係中的另一人?「無論如何,只有你能創造或維持你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此時期之後,波娃的視角越從個人走向社會與政治,因為無可避免,你的行動會創造、影響他人,同樣地,他人行動也創造了自身存在的處境。
人的處境可以影響他人,那它無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波娃目光最終轉向了自身性別,那麼女性的處境(Situation)又是如何被創造出來呢?雖說波娃將功勞歸於沙特的提醒,但她自小或隱或顯察覺到的、自身與男性主流觀點的差異仍成為寫就《第二性》的根本動機,著名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便出自於此。書中批判永恆女性的假象,要求女性不僅是生理上符合女性,更在社會制約、家庭分工和自我追求上像個「女人」,以至於對愛,男女雙方也都擁有不同解釋。對前者來說,愛更接近於佔有,他們保有主權主體(Sovereign subjects),可以同時追求人生中的其他成就;可對女性而言,愛被形塑成枷鎖,它限制住其他發展的可能性,愛,成為女性價值的唯一來源。
讀來何其熟悉的呼籲依舊不退流行,因為這些宣言對今日仍然有效,和女權自助餐的罵聲相同,當時波娃也因此蒙受了各種批評,從行文模式太過菁英、蔑視母職重要性到批判她就是個女性,各種立基於性別的冷嘲熱諷從沒少過,但這無法阻止波娃於創作之外更進一步協助女性的生活處境。變化既有社會結構始終是困難的,那非優雅在咖啡廳搖動筆桿一蹴可及,而是對抗且回應外界聲浪。當波娃成為名人之後,作者花上更多篇幅處理自波娃引發出的反響和回饋,那些是我們得以看見的波娃,亦是公共知識份子必須擔負的責任。她聲援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她協助推動墮胎合法化、她支持母職在社會價值上的改寫、她寫了《論老年》剖析老年議題……
可同樣也是波娃,面對這些所謂重要公共性事務時,也會展現她屬於個人情感上的低落。她難過於為什麼同樣是法國民族,卻可以對殖民流血抗爭的事實視而不見?她焦慮於日復一日且無法遏止的老去,有時甚會如朗茲曼(Claude Lanzmann)所目睹的那樣突然激烈啜泣起來。西蒙‧波娃此時不是女性主義的品牌幻象,也非追求公平正義的連署姓名,她就只是一個人,有人終將體會到的脆弱與悲傷。
嚴格說起來,波娃並不算是精確定義下的系統哲學家,她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系統學說,解釋人的理性與作為會依靠什麼理論運作。可這樣說也不夠精準,波娃將她的人生活得很哲學,她努力思索自身的過往經驗,並用她的語言嘗試給予解答。正因為沒有那宿命式的牽引,波娃也不免走偏而對於過往感到後悔,這是她先前所有行動累積下來的處境,「在人生中,那個所有人生片刻都能彼此和解的時間點並不存在」,各個時間點的「我」都不是同一人,珍惜與執著的意義也都迥然相異,既如此,她只能在這樣的基礎下,持續在動態中填寫對自我的定義。
關於波娃的資料浩如煙海,要能整理消化,編織成流暢易讀、不顯混亂的傳記實屬不易。雖然看來有些厚度,然本書敘事讀來就如同縝密小說,妥善交代波娃之所以成為波娃的數條脈絡,對於入門讀者或更進一步研究者皆有所得。我很喜歡貫穿書中的「成為」詞彙,傳記之所以迷人,就在於它看的到第四維度中的延伸與壓縮,對錯得失都僅是一隅投影,轉向之後,都可以是一條通往遠方的線,一如前言,波娃在世之時也不斷擴展自身的可能性,以至於沒辦法簡單用名字概括始終用思考對抗世界的心靈,那些曾陪伴身側的偶然戀人、無人可比擬的摯友沙特,以及理解、拆解並化解第二性的困境,此時此刻,都促使我們走在成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