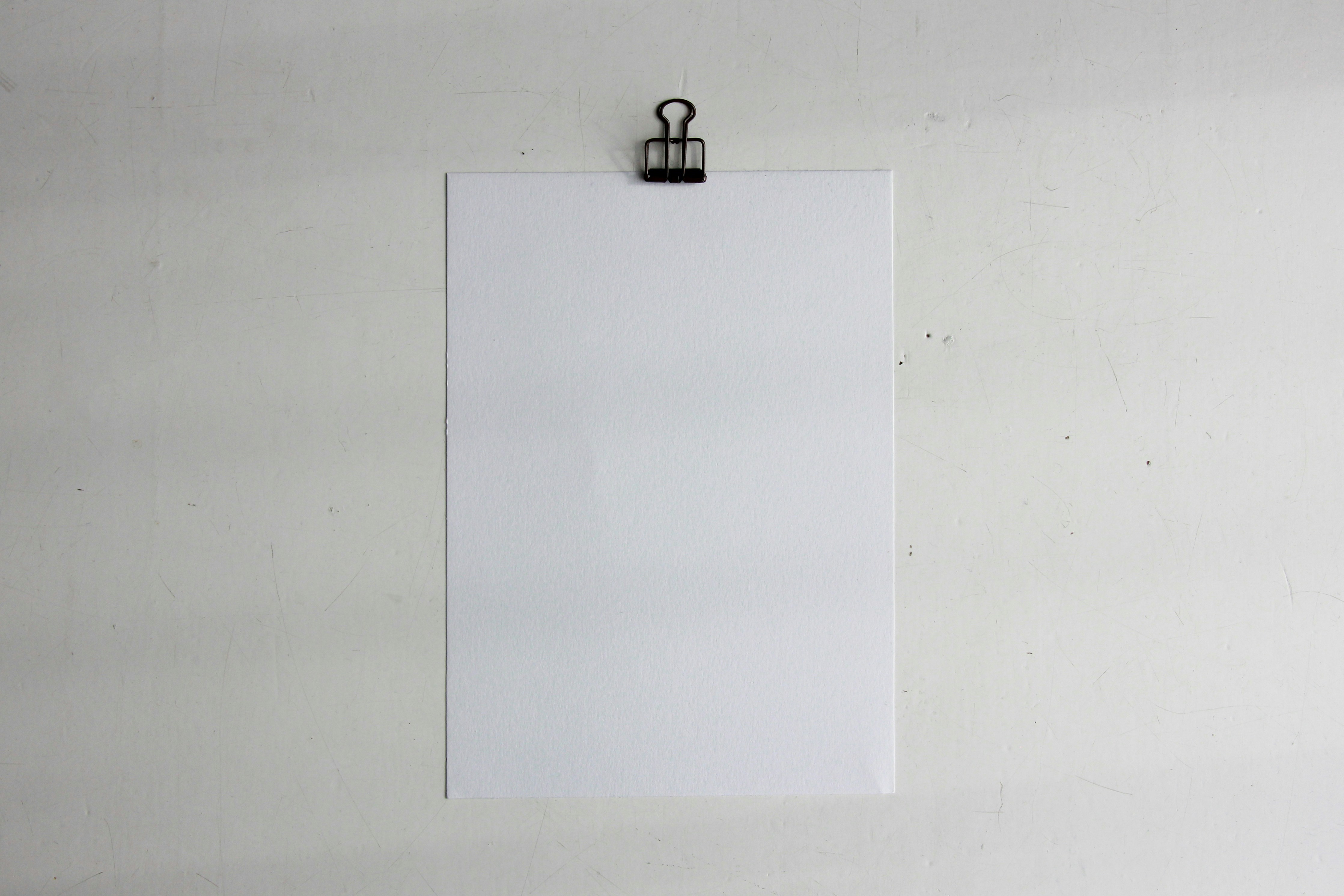生活雜記 | 有關跑步的事01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二零二二的上半年,兩場馬拉松遭延期和取消。數了數,上一個半馬已經是 2020 年夏天的事。
彷彿沒有賽事就沒有練跑的理由,那雙跑鞋將近兩年沒有拿出來了,至今還掛著上一場賽事的晶片。它被我塞在左邊櫃門的最下方,一個永遠不會打開也很難照進光的角落。
塵土像脫體的皮屑黏著在鞋面,暗啞的表層再也無法追思它的青春,滯留於鞋頭的時光我只能見證,見證它像開出的列車般,一去不復返地老去。
鞋子為我展示了它悄然老去的樣貌,在褪色的紋路中,藏著那麼多碎裂的指針。
曾經,跑步是我抗衡一切的依託。
在我印象中,體育課上同學都能輕鬆完成 800 米、1000 米練習,自己卻總是跑得特別慢,還特別容易就喘氣。那時候目標只是運動會的1500 米,小小的數字,卻需要無數個凌晨五點去練習。九龍灣距離北區的車程,最少需要六十分鐘;六點四十分是我出門的死線,半小時三公里是練習的最低限度。
當然現在來看,這些數字與要求都好微弱,好簡單,當時的我卻瘋狂地追求著別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標準。我媽總說,DSE 都無法讓我凌晨起身溫書,跑步卻讓我在凌晨五點自然醒,我這是腦袋破洞又走偏了路,對數字的追求放錯了地方。
有一段時間的確盲目地追求著 app 中累積的里程數和排行榜,跑步成了一種日常作業,一星期七天都在練跑,可每次也只是四十分鐘六公里的成績,沒有特別優秀,也沒有剛開始來得爛。
可這些數字總歸讓里程有了實質增長,且具象地讓我觸摸並意識到自己身體的極限,並逐點鑿開它。
至今為止,所謂「天道酬勤」我也只認同練跑這件事。
很多人都認為長跑苦悶且無趣,沒有一來一往的對話,也沒有變化度高的招式,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音樂世界,看進眼睛的每一幀風景注定無法準確地傳遞給不在場的第二人。
也許長跑更像一場孤獨的享受,那些晨曦的九龍灣、拉薩市、台北市,沒有顯影在底片之上,卻一幀幀記檔在腦海的深處,翻閱這些相片,是微風、陽光、雨水、泥土、玉蘭花、鐵路和經文。
這一刻,我不用尋找,也不用等待,只需要往前奔赴,別無他想。
date: 2022-03-24 22:39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