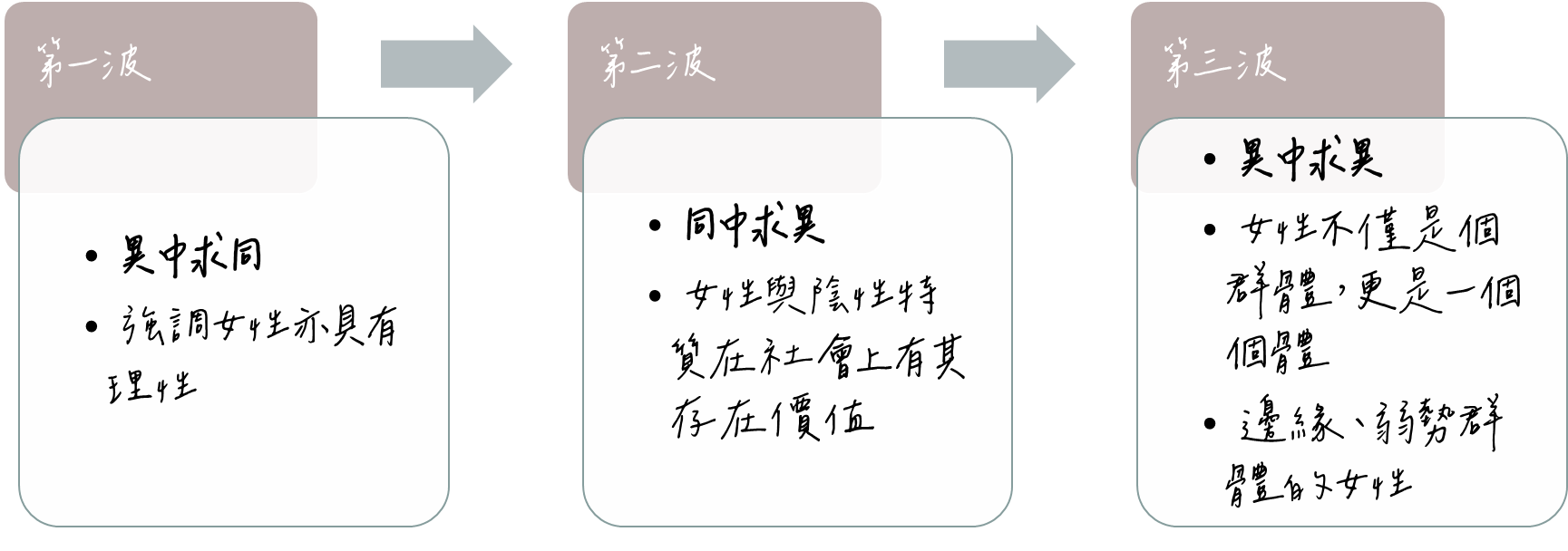當代文學史的自我經驗--讀《文藝春秋》
《文藝春秋》引起共鳴與同感並不意外。而且這種共鳴,所招喚起的情懷,在很大的程度上屬於「同代人」。就算不是標準文青——其中作者展現出一種承襲前代的廢材氣息(例如駱以軍?),卻也正是是這種「廢材」與「偏差」散出的寂寞氣息,形塑起這一代,甚至前溯與後推鄰近世代文青臉譜——,在接觸「漢聲小百科」、「林強」、「迪克森片語」、「楊德昌」等關鍵字,也難以抗拒,在作者誠心以純熟技藝召喚下(從戒嚴特務到未來電影博物館,甚至到火星,不同的風格操演,彷彿宣示著要為「每一份記憶創造出一個獨屬於此的『說話主體』」),拿出自己的記憶比對,重新閱讀自己內在的「記憶之書」。
引起共鳴自然是創作者的美夢、成功的創作實踐。同時卻是成熟創作者該警惕的。勾起懷舊情緒之後,恍然面對現世,轉瞬發現「情懷」不僅不合時宜甚至貶損(或廉價),而略感尷尬。那麼作為專注於這個小說世界創作者,在途中所承受的困惑,必然是多上好幾倍,而且是在創作間就出現了。最容易產生的疑慮,正是「消費」。這是年輕作者對偉大創作者們的消費嗎?弔詭在於,作者幾乎完美化解疑慮,在貫串諸篇的「靜觀之眼」(是否有點站得略遠些?)所呈現的視野,反倒證成,令人眷戀的人事物,不論是私人的、甚或世代、集體的價值,其實都「無法消費」。
也許正在於創作者的自覺裡,對於「材料」的審慎,小說的基調中,沒有讓情懷凌駕於「對象」本身(譬如某些骨灰級玩家,玩起數十年前畫面尚粗糙的古老遊戲時,會淡淡對地說:「哥玩的不是遊戲,是回憶本身。」),反倒使讀者面對起種種「主題」時(經常是第一人稱的、我們得面對這些人物話語與意識,譬如開篇的廢文青開啟、爾後潛伏在各篇裡低吟的話語),無法不察覺當中的尷尬。彷彿尷尬感是一路上留下的線索,看起小說,不論閱讀怎樣時空與角色(譬如令人眼睛一亮的阿桃),尷尬在哪,創作者心緒本身就藏在哪。
作者清醒著:在擁有越來越成熟的技巧後,作者並不必要去窩匿自己,尤其不易面對的部分。這並不容易。如同一個純熟的面具製作師,如何抵禦就此戴上各種面孔,再也不必面對自己真正的面孔的誘惑。不躲、不藏,但同時也不自戀與不自溺,創作者在此思考,不斷地誕生自己。若說《文藝春秋》首先讓閱讀感到慰藉,是因為創作者與其話語,已經找到一個地方得以共處。作者與他的作品未必不尷尬,然而在此,已經可以面對尷尬時安然而不尷尬了。即使這平衡可能不是永久的。只是在踏向下一步前,總還算有暫時借取來的幸福時光。
我們能夠揣想,用各種不同的聲音說話(已有若干讀者指出其中不少第一人稱的使用產生的效果如何),背後真正的動機,還真的可能單純無比:想找到自己的面孔,與自己的聲音,說自己的故事。所以,也或許我們能夠理解,這些偽裝背後,我們所讀到的,可能仍是那個最初受文學感動的卻懞懂無自信的,那個蒼白文青。因此首章與末章的安排,廢材文青面對令他嚮往又同時惶恐的文學世界,那份貫串整本書的倉皇失措,尤其最後複寫上的「這樣也挺好的」,終將默默認份起擁抱書寫的命運:不論如何,作為「這份文學史」當中,即使只是小小的塵埃,也未必不幸福。
同理,本書的諸篇跨度,不光是時空場景,甚至包括語言風格,一再的展演下來,卻準確地讓這本書定位了(如果有注意過作者過去對於定位的思考與焦慮的話)。如同前述的面孔,這樣銘刻出的,是一個「此時此地、屬於這個世代」才能誕生的作品。如果後來我們承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當然,所有的文學史,也就只能是當代的文學史了。顯明的,作者擁有的野心,還是書寫起我們的當代。但,真的只是如此嗎?小說既是虛構的力場,就不可能無視,被書寫的、以及書寫者本身都在這種力量中。或以羅蘭巴特的觀點,小說的寫作,是在主動與被動(作用與非作用)之外的,它屬於「中動式」。簡而言之,就是「透過寫作當中,對寫作本身作用」。關於此,《文藝春秋》(書評已有「史」意)裡,以各種不可能出現在文學史當中的話語(尤其第一人稱的使用),所隱然寫出的「文學當代史」(而且甚至是史學上的「個人史」),其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對自身產生作用。換句話說,修正了、甚至可能消解了這個一次存在的歷史(即「在此的」文學當代史)。於是懸置在虛構與對虛構的否定上,當代與對當代的否定上,履踏在輕盈與沈重、空虛與充實間。虛構文學史,亦即虛構文學當代史,完成在「文藝春秋」名字下,對於自己經驗的虛構。
所謂經驗是什麼呢?即文學經驗。不斷爬梳資料,指向的是內心文學經驗心靈史。經驗,如阿甘本所說:「如今要探討經驗的問題首先必須承認我們再也無法得到它。任何想在今天恢復傳統經驗的人都將面臨自相矛盾的境地。」無法再得到了,重複地去觀看,譬如瑞蒙卡佛、聶華苓、黃靈芝、袁哲生。對於他們的人生,我們都無法再多做什麼,甚至遺憾的,對於他們的「文學經驗」,能否藉此多瞭解一些,我們都得保守以對。但最終,我們仍可藉由反覆閱讀,去取捨形塑記憶,以及,繼續寫下去,於是我們有了這個作者與這本書。
回過頭來,《文藝春秋》執著的「創作者意識」,若讀者願意在閱讀後多停留一些,不難遇上同樣一堵牆:作為創作者,或更窄仄一些,台灣的創作者,宿命地遭遇各種挫折與貧脊環境,卻又因此開出的美麗花朵。但問題在於,以各種構思,重述了這些「牆」與在此緣邊掙扎、擠迫、拗折、頑強、遺憾的身影,進而感知到小說的說話主體自身在碰觸材料時所碰到的「牆」,那麼,這本書,想說的還有什麼呢?意思是,無論多次重述了各個作者珍視的創作者的牆,或是最終整本書構成了作者的牆(一種萬里長城?),有沒有之外的,關於可能性的存在,在如此細膩巧思的展現各種不可能之後?
我們或許就能去期待,末尾借取的「這樣滿好的」,投射在將來不得不繼續的書寫畫布上,會有什麼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