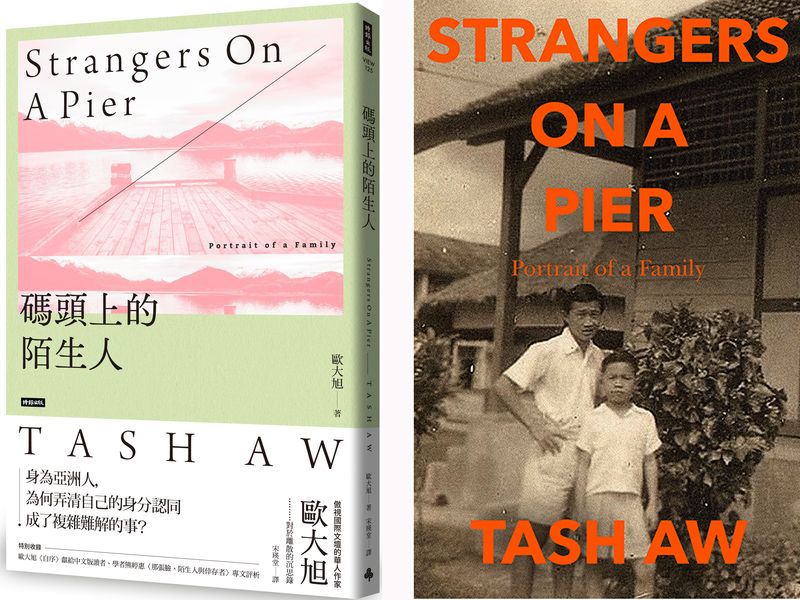1999年10月,在加拿大的一間購物商場外,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男子攻擊22歲素昧平生的女性,全身共六處刀傷,緊急送院,所幸最後性命無礙。男子沒有逃走,而是安靜待在現場,直到警察將人逮捕。《沒有刑責的罪犯》就是以這個背景,記錄男子逐漸穩定,走入社會,以及向女子及家屬道歉的經過。

劇照。
紀錄片以男子西恩為主要視角,難免會有「美化」犯罪經過之嫌:攻擊只是忽如起來的舉動,可能根植於過去陰影。西恩如今已很努力維持生活,定時吃藥,充滿歉意的活著。雖然影片最後,受害人讀完道歉信說她已原諒了,但從表情反應來看,似乎只是原諒了自己作為不幸之人,而不是西恩。
「我不認為他是邪惡之徒,我相信他是病人... 我接受他的道歉。只是聽到他說『這是隨機事件,不是針對你。我當時狀況不好,我生病了。』我覺得這樣就足夠了。」西恩殺人未遂的舉止,因其精神狀況而被免去刑事責任,轉到健康照護所。隨著康復狀況,慢慢允許增大活動範圍,但不允許再靠近受害人,回到社會後仍會被監控。
據說本片仍有從受害人角度出發的續集,但我還沒看。
許多國家在判定刑事責任時,會對有精神障礙的加害人做區別待遇。加拿大與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相同,判定時會考慮犯案意圖,來證明有或無刑事責任,也就是 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 on a account of a mental disorder (NCRMD) 。強制治療的時間不能比刑事懲罰時間更長,但在2014年以後,法律改為嚴重者可持續被限制行動。
與大眾印象不同的是——從媒體上或許會以為每個殺人犯都提精神抗辯——在許多國家,提出精神抗辯的比例並不高。在陪審制下,還很可能因污名化(脫罪之嫌),而讓人不敢提。加拿大很少被判處強制就醫的例子,其實一般相信,很可能只是更多被關在牢獄裡。
有的國家並不完全遵循NCR,像荷蘭(以及相似制度的德國和比利時)會分為5個級別程度(從負全責到無責任),衡量其所需負擔的刑事責任。不過,荷蘭對精神認定較為寬鬆,反社會人格障礙(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也被視為影響行為自由意志的因素。在某些國家法律(如加拿大),會認為他們只是無法從生活經驗中學習,不需要就醫。其實這也提醒我們,當大家在談精神障礙的刑事責任時,必須留意究竟是指哪些精神障礙。
比較特別的是瑞典,並無免責的選項。瑞典早期實行NCR,但在1965年反而將改為需負刑事責任,直到2008年才再次修改。瑞典法律的做法是,只要鑑定出有精神障礙,無論犯罪時是否受精神疾病影響,都一律送去就醫。算是一種以治療為目的,而不是衡量懲罰程度的做法。之前在寫相關文章時,找到一篇早期的論文,根據起訴書調查在2001年至2008年間,經精神病學調查人數:

不曉得是不是謀殺案很少才導致數量上看起來低。我好奇的是在其他國家,例如台灣,會指示為其他犯刑者進行精神鑑定嗎?
一般來說,精神障礙自殘機率遠高於殘人,但因為自殘並非刑事罪(在部分國家是罪),透過起訴書所作的統計反而看不到這點,也會間接讓人以為很具攻擊性。
其實大眾還是認可部分時候的殺人並不等於殺人。像是過失殺人、自衛和非自主(被強迫)情況。精神疾病屬於非自主一類,只是他與我們直覺理解的「強迫」不同——我們直覺想像到的強迫是「有人拿著槍指著你去殺人嗎?」——精神疾病患者卻是自己行動。只是思覺失調是基於不同的自己。
在探討精神疾病,尤其思覺失調患者的刑事責任時,偶爾我們會過度將焦點放在疾病身上,嘲諷「殺人前只要先做鑑定就可免責」,往往是把對制度的不滿,轉到精神疾病或患者身上。如何調整責任以及應對方式,在各國法律並無共識,也說明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我不認為台灣社會對精神障礙充滿惡意(但我不敢說好意),在許多地點都有能與社區共處的精障者,即便作出冒犯舉動,路人還是摸摸鼻子離開。只是牽涉到殺人,往往容易直線導入唯一死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