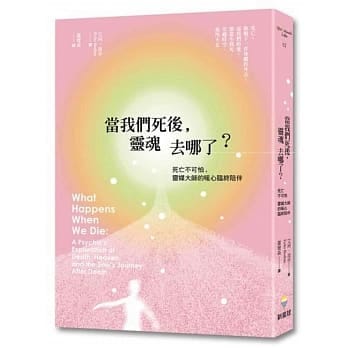規劃未來二十年的人生
請用你手邊的一張紙跟一枝筆,規劃你未來二十年的人生。
例如,我會在這張紙上寫下:結婚、讀研究所、生小孩(?)、創讀書會社群、環島、成為作家、把台南的咖啡廳都去過一輪……。不過,請等一下,你怎麼能確保你還有二十年?進一步說,你怎麼知道,死亡不會在明天來臨?但你說:「我們當然不知道死亡什麼時候來臨阿,但我們總是得為我們的生活打理、負點責任吧。你這樣杞人憂天,不是太不切實際嗎?」
沒錯,我們在這個世界活著,總是要過好生活、創造意義。然而,我們不得不去認真面對一個問題:既然我們不知道死亡何時來臨,世上汲汲營營的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另外,當你想像自己被徹底消除在人世間時,你的感覺是什麼?我們總認為,死亡永遠是別人的死亡,與自己無關。生活的庸庸碌碌,遮蔽了對死亡的體會。然而,死亡不斷地對我們呼喊,人活著不只是我們所見的世界,活著還有一個「更大的基礎」。
《生死學十四講》即是一本從死亡認識一種新的存在方式的一本書,探索這「更大的基礎」。作者余德慧教授以生死學的進路,深入分析人存在的狀態,並觀察臨終病人的各種現象,來為我們指出一條「知死知生」的道路。

活著的雙重性:OTB與默存
余德慧指出,人活著本身有「雙重性」,一個是向外發展自我,另一個是向內走向自我。向外指的是用「心智自我」對世界進行掌控、計算、結構化、意義化,思考如何運用時間,將每件事情安排妥當,朝期待的方向前進。我們以「事情」佔據我們的每一剎那,對世界操心。這種「外造化」狀態被稱作OTB(otherwise than Being),也就是「非存在本身」,是一種「非本真」狀態。例如,你會想等等要吃什麼晚餐,下個月要去哪邊玩,要怎麼跟人和好,要讀哪一個科系,要做哪一個工作。
相對地,向內指的是「默存」。默存本身就是空無、存在,它不對這個世界操心,不給出意義,不分別善惡。默存是生命的「底景」,而OTB則是「圖像」;默存不否定世界,而是支撐了世界。當一個人接近死亡時(心智自我溶解),就能越走到默存的狀態中(「本真」狀態)。我們可以說,默存是碰觸靈魂自身的空間。
生死學要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必須從這兩極間,逼出一條活著的道路。既不能執著於外在世界,因為它會遮蔽死亡,以為現在擁有的一切就是全部,當下就是永遠;但也不能只走向「默存」,退出世界,因為空無沒有辦法給出意義。
我們必須從OTB與默存這兩極間,逼出一條活著的道路。

連續性的假象,懸吊的花瓶
心智自我會給我們一個假象,即「同質地對未來展開無限投射」[1]。例如,當我對女朋友說「我永遠愛你」,這就是一個只對「當下」有意義的言語。加入時間的因素,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不太真實的。因為,我確實不知道什麼會碰到生命的極限,使得我不能「永遠」地愛她。
換言之,心智自我以一種「連續性」的假設來看待生活,認為現在的生活會永遠延續到未來,如家人安康、事業有成、信仰穩定。然而,死亡的邊界告訴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即使堅固,但本質是「易碎」,宛如懸吊的花瓶。你怎麼知道,下一秒鐘誰的身體會出狀況?原本我們以為最可以掌握的事情,卻是如此地有限、流動、難以捉摸。
將「死亡的斷裂」切入生命的連續體
因此,作者引用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的思想指出,對死亡的焦慮與害怕是「好的」。這裡的害怕,並沒有一個對象,而是陷入對「整體虛無」的恐懼。透過這種對死亡的「畏」,我們將死亡視為「自己的死亡」,破碎OTB的自我,尋得真正的「倚靠」。碰觸底線的倚靠,帶來的行動即是「願有決斷」,或稱「轉身」,指人意識到自己死亡的邊界,而願意以新的眼光看待原本的生活。這種以「存有者」見證「存在」的姿態,會意識到原來每個孤島底下都是大海,而與人產生一種共命共苦的深刻連結。
換言之,深刻地活著,即是願意以「死亡的斷裂」切入到生命的連續體中,隨時保持「畏」的狀態,對擁有的一切感恩,對執著的事物放手,對人產生更多的寬容。用臨終作我們的開始,於是,生命不能有太多的「來不及」、「早知道」。
深刻地活著,即是願意以「死亡的斷裂」切入到生命的連續體中。

感受傷口,認真的不認真
但實際上要怎麼做?余德慧指出,首先,我們不能逃避受傷的經驗,才能夠破碎OTB的自我,讓生命底層的光透出來。感受傷口,才能在「斷裂」中練習復原、深化經驗;而非急著將傷口醫治好,立刻尋找一個避難所。
再者,是將世界視為一座「遊戲場」。遊戲的本質是「認真的不認真」,我們必須認真地活在世界中,但不能把心智自我所打造的一切當作生命的全部。方法有三:第一,練習用「後設」的視角觀看自己面對事情的各種思緒。第二,不把自己當成世界的中心,以為事情會這樣發生,都是因為自己做了什麼或說了什麼。第三,保持觀看的能動性,不將眼前的問題當作問題本身。
結語:開創靈性空間
以基督教的脈絡來看,這種「在世卻不屬世」的靈命操練,為我們創造出一個「靈性空間」,不再以地位、金錢、種族劃分你我。這時甚至也沒有愛的「對象」,因為我們本身就散發著從神而來的愛,以嶄新的存在方式包容所有的人。
上帝什麼時候接走我們,真的不知道。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祂一定會接走我們。我在想,初代教會的基督徒應該是一群對死亡把握得很好的人。將「死亡的斷裂」切入到生命的連續體中,我們更願意放下自我的私慾,成全他人;放下過往的恩怨,與人和解;分享自己的所有,打造一個新的國度;相信我們最後都會「回家」。最後,他們真的什麼也沒帶走,但其信仰的掙扎、生命的領悟,卻化作故事流傳一代又一代,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叩問我們的靈魂深處,訴說著生與死的終極意義。
《生死學十四講》不是一本心理勵志書,不會用你習慣的方式教你如何「提升自我」。因為我們的活著,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而是充滿著疑問。在疑問產生的破裂與縫隙中,我們才能看出靈魂深處一湧而出的光暈。
「生有時,死有時。」(傳道書3:2)
請用你手邊的一張紙跟一枝筆,規劃你未來二十年的人生。
[1]余德慧,《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3),頁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