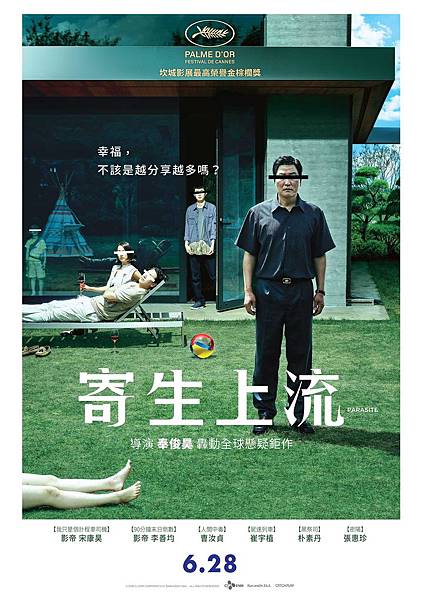電影:《扒手》1959
有個女孩剛跟我說:「你沒活在真實世界中,與別人格格不入,是個異鄉人。」

我是米歇爾,住在一間巴黎擁擠閣樓裡的男人,空間裡只塞了床、書以及滿滿的我。我得再次犯罪才行,我不喜歡緊迫的生活,可是漫不經心下偷走他人錢包,我卻很喜歡。那些人從未見過我,我卻有權力記得他們,我遠遠欣賞他們失去自信、失去身份……然後抽出錢,把皮包丟在無所謂的地方。
我能隨意想著他們。除了你們這些觀眾,世上沒人瞭解我和我的小思緒。
告訴我,我會不小心從眼神裡透露迷狂嗎?
我不只要錢,不夠滿足。我要的是更靠近受害者,感受無知的呼吸,感受他們對我的視線……我有耐心等對方分神,片刻間手指勾出,內袋就吐出錢包順著外衣滑到手裡,這一系列的畫面在布列松的凝視下,我有如巴蕾舞者。

作為最具哲學性和思辨色彩的導演之一,布列松深怕我的「表演」會毀了作品。導演只追求肢體的運動,而非情緒、風格或試圖達到某種效果的努力。因此他告訴我,我臉上的表情是觀眾給我加上的,我不曾露出破綻。布列松要求我們這種扒手不要去「表現恐懼」,就是什麼都不表現,把傳達恐懼的任務留給他的引導和你們。
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07—1999)就像布努埃爾和侯麥,他被稱為最具基督教色彩的導演。他的絕大部分影片都以各種方式和救贖有關。除了和《罪與罰》相似的《扒手》,他還拍過兩部直接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溫柔女子》(Une Femme Douce,1969)和《夢想者四夜》(Four Nights of a Dreamer,1971)。
你也許能感到我在某些方面和《罪與罰》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相似。後者也是個住在小閣樓裡的孤獨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有常人不具備的「特權」。其實像小說的人不是我,而是布列松。他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人,需要錢實現拍電影的夢想。把讓某個不起眼的製片人提供經費看成自然的事。他們的邏輯都是不道德的,但他們認為自己有特權超越善惡彼岸。我感到布列松想被逮捕,那眼神裡的東西,我知道。
與布列松的初次相遇是有次我和另外兩個同夥,在火車上來回作案,我們甚至把掏空的錢包又塞回物主口袋,給出用來空虛的理由。我們的手無論在時間掌控、優雅程度還是精確性來說皆入無人之境。然後我偷到了他的皮夾——布列松那本來就空的皮夾!他抓到我了,於是你們就在1959年有了這部《扒手》。
在他威逼下,拍好畫面。他要求我重錄對白,用以達到電影中自我思辨式的「Voice-Over」。他不相信我已經一次做到把控驚人的張力和興奮,他要緊緊控制住鏡頭下的我,也要勒著觀眾的呼吸。「我的當下」被他殺害了!

《扒手》講述了一個人有意試圖操縱外在道德的故事,這部電影都在說:我們會被審判嗎?被什麼審判?和許多罪犯一樣,這麼做有兩個矛盾的原因: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優秀,以及由於害怕比別人更糟糕而尋求懲罰。如同讓娜的善良成了我自尊的威脅,所以我躲著她。
「你承認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他們對社會不可或缺,兼具智慧、天賦與才華,所以該讓他們在特定情況下不受法律約束?」
「這很難,而且很危險。」
「我想這有利無害。」
「那誰來識別這些『超人』?」
「他們自己,他們的良知。」
「可誰不認為自己是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