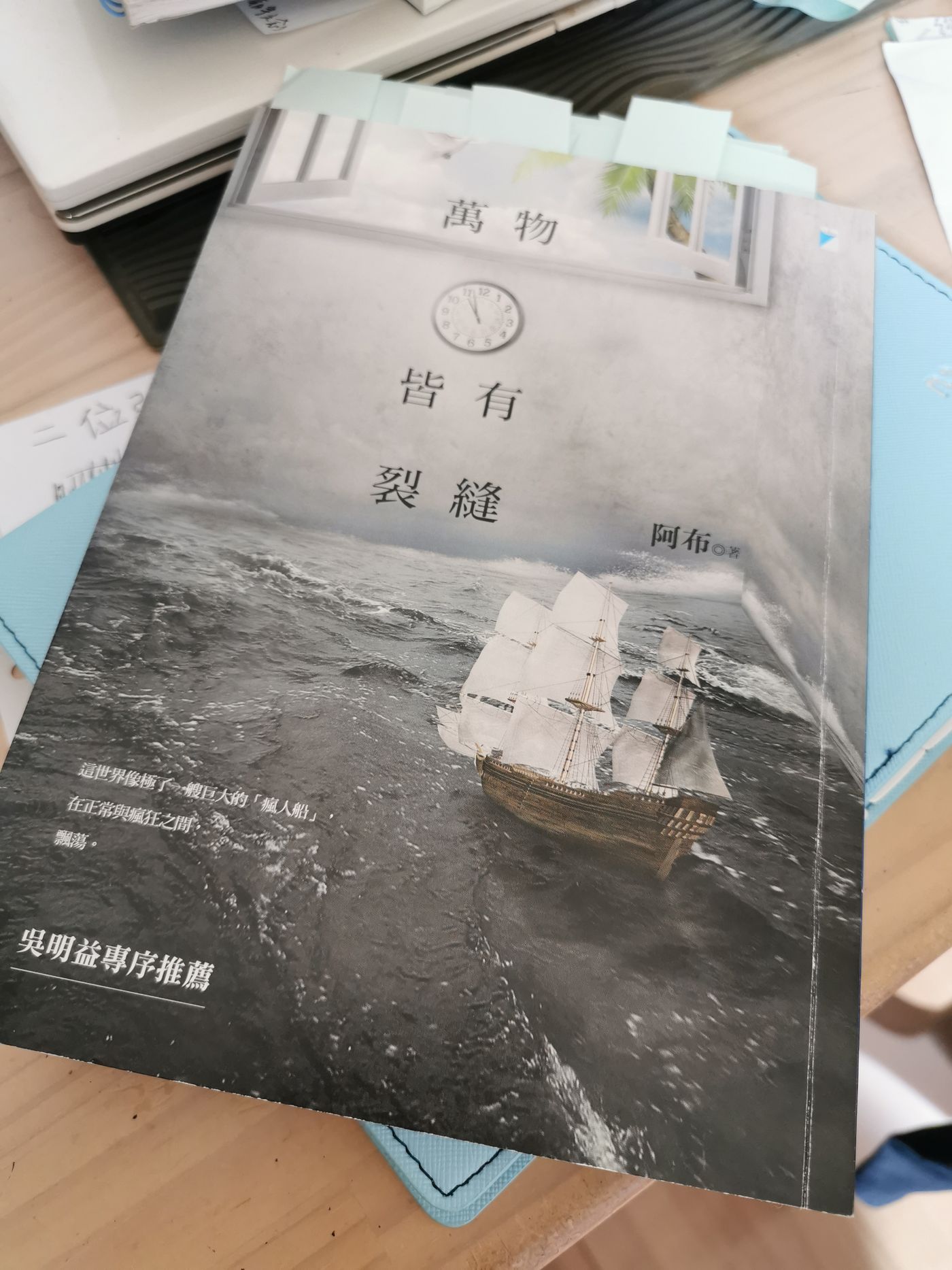萬無一失
閱讀時間約 23 分鐘
這字字句句,聲聲泣血,就算我生於皇室見慣了父子相忌,也看透了世間涼薄,也不免爲之動容。
父皇送出公主和親之時,公主之生母柔妃在宮門跪了三日。但父皇的意思不曾變更,待得公主回京,當日鳳冠霞帔風華正盛的轎輦只剩棺槨,柔妃病重,不過數月便香消玉殞。
但即便陛下仁德,也從未因此事煩憂。公主之責,金玉嬌養的尊貴,背井離鄉的悽慘。
此刻看到如此父女親情,我有些許羨慕。
若是當日,姐姐的父親有於尚書一半的舐犢情深,或許也不至悽慘如斯。
我沉默了。
於大人也靜默着。
沙漏中的細沙一刻不息地流下,我開了口,「皇室姻親,是於氏風光,怎麼,是覺着我這太子配不得大人嬌養的女兒?」
那老頭眼睛和精怪動起來的樣子一模一樣,滑滑溜溜,「殿下,臣不敢。可即便是陛下,也未曾有指定陪媵之先例!」
老狐狸收起了那副慈父做派,此言之中已有剛硬。
我心裏思忖,看來這精怪對她的父親來說,勝於權勢,勝於官途,她,被於大人放在心尖之上。
又過了兩柱香的時間,這時候,已經是各府下鑰的時候了。那個把柄不到最後我不願拿出來,那是我的底牌,可我終究不願用脅迫的方式去娶她,更不願去拿捏她的父親,愛她如性命的父親!
我坐在於家仍舊未動,窗外窸窸窣窣的聲響吵的於大人有些煩悶,竟一把推翻了几案上的茶具。
熱燙翻滾,我紋絲不動。
他嘆口氣,「容臣問問小女!」
她進來的時候,端端正正地行了禮,可門關好的那一刻,便坐在窗前,「於老大人,找我何事呀!」
我第一次見這樣隨意的父女關係。
「正經些!」他爹壓低了聲音。
我在屏風後,輕輕翹起了脣角。
「阿爹,你是要做姨娘的說客吧?」她聲音懶懶的,「我不想嫁,誰也不想。阿爹,就讓我在於家不好嗎?」
「你最近可有得罪什麼人?」於大人聲音隱含怒氣。
我拿起茶盞抿了一口,瞧這話說的。
「有啊,我最近得罪了姨娘。」
「你……」這無奈又寵溺的聲音,「照椿,如果有一日,阿爹護不住你,你會怪我嗎?」
「會呀,當然會!」聲音懶散中又有幾分認真的,「可是阿爹,這麼些年,你幾時護得住我來着,沒事沒事,如果實在不行,不必勉強!」
「太沒禮數!」
「阿爹,這些年,母親苛待我和姨娘您是知道的。我長這般大,拿用於家的少之又少,您就當少生了一個女兒,我不想嫁入公侯之家,也不想嫁給前途無量的探花郎。爹爹,求您了,好不好?」
我聽了這話,有些恐懼。
「照椿,所有人,我都能看得到他的所求,求財者,求名者,甚至求瞬息之歡愉者,可我不知你在求什麼?」於大人眼睛看着手中早已不冒熱氣的茶水,指頭卻微微顫動。
「阿爹,你真有意思,一個人生來就要有所求嗎?」
於大人深深咳嗽一聲,「再這樣說話,信不信我把於家的家法給你請來?」
「我好怕,好害怕!」
嗯,我沒有聽出她的害怕來。
於大人被她捉弄得頭疼,擺擺手讓她滾蛋,那小丫頭打開門,十分恭敬地給她爹行禮,「女兒告退,爹爹晚安。」
端莊閒雅的姿態,無可挑剔的禮儀,平靜無波的語調,恕我冒昧,真想問問我們是不是同門師兄弟,學的同一門派的裝腔作勢?
於大人嘆口氣,「殿下,您也看到了,她這樣一個表裏不一,慣會騙人的女孩子,實在不配輔佐東宮。」
但此時,我卻不想談論這些了。見到她的那一刻,我不想再去顧慮,不想再去拖延,更不想橫生任何枝節,我一定要做她的夫,讓她年年歲歲對着的那個人,必須是我。
換了任何人我都會萬蟻噬心而死!
堂堂太子,便是娶妻納妃,也不能折了我的威嚴不是?
儲副最該談論的是政事。
「此番冒昧打擾,是孤的過錯,只是,於大人,您在朝堂這麼些年,虎狼環飼,是家仇重,還是國恨更重?」
他眼角的褶皺動了動,「殿下,於家不過區區小門戶,頂了天也只是我一人支應門庭,何來家仇,至於國恨,臣一介文臣,做到俯仰無愧便是了。」
「小門戶?大人過謙了。」我看了看這間屋舍,裝飾很是質樸,但其中的門道可一點也不少。
「這斗笠青瓷盞似是前朝開國十年間官窯產的第一批賀朝貢品。」站起身踱步至窗前高腳桌架,「若是孤眼不拙,這折枝芙蓉銀盤乃是前朝末年哀帝御用之物,前個月,探月閣出手了一件與此甚是相似的石竹銀盤,得了三千金。於氏世代爲官,簪纓百年,何爲小門戶啊?」
他立在我身後,我知道他在探我的虛實,有些時候這些微末伎倆可比狠話要奏效得多。
這些擺件我一向不上心,若是擱一個大金磚,我大抵還能知道他的金貴。若干年後才恍然,或許自己喜歡那個矯揉造作滿口敷衍的精怪,許是因爲我們都不知道御書房那些舊兮兮的古董哪裏好看,值當礙了我看奏摺的大眼。
這是胡伴伴三個月前一件一件梳理的奏報。
「殿下,臣之家仇在國恨之前,何足掛齒?」
「孤懸在北漠,常常缺衣斷糧,爲了維持北軍軍力,什麼缺德事都幹過,但那些莽漢子他們用命去守的國,廟堂之高的人卻用他們守住的安寧來爭鬥!」
我這話衝得肺腑顫了顫,遲相爲了排除異己,更爲了北漠軍權,挾制厲家,糧草剋扣得令人髮指。
我這人不是君子,靠着幾番殺伐北漠世族削弱了不少,父皇又給了稅權,才堪堪能養活北漠軍力。
父皇派我去北漠絕不是無的放矢,那裏爛透了!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其上沾的鮮血和陰謀早不知多少。
世族最難對付,也最好對付,他們之間的利益牽扯不清,利益爭奪更是如火如荼。
「臣惶恐!」
這老狐狸着實不好對付,我緩了緩,「於氏在北漠,也是好大的家業呀!」
我雙手托起他作揖的手,畢竟要娶人家的女兒,禮儀是要有幾分的。
「殿下,臣約束部族一向嚴謹,北漠一支早分了族!」
「是,是分了族,在於老太公辭世之時,不是嗎?」
我手上用了力,這老頭子總歸是書生,硬是被我拉了起來,看他額上早是細密的汗珠。
「殿下,臣忠於陛下之心……」
「孤知道,可大人忠於的是陛下,可不是孤啊!」
「你的大女兒,孤即便是娶了,也不過是和符氏的聯姻,你的小女兒奉上,孤纔信你的忠心。」
「殿下,臣之長女是我嫡生女!」
我坐了下來,看着他笑了笑,「你心裏明白,又何苦呢?符氏一門孫輩無女,於大小姐自幼被符太夫人帶着四處結交,從那時候起,她就算半個符家女了。僅僅她入東宮,沒人會看到於家的投誠,這搖擺的人可就不敢落子,孤這媳婦娶得虧啊!」
我端着茶杯喝茶,抬眼看着於大人,他眉頭緊鎖,閉着眼沉吟一會兒,緩緩道,「臣之幺女,不入宮!」
話畢,這老頭居然甩袖走了!
哼,孤的顏面何存?
我敲了敲桌面,李織溶便從窗外翻了進來,鋪面的塵土味,嗆得孤咳了咳。
「殿下!」
「把東西給他!」
她低頭便出去了。尋常士大夫,聽了我剛纔似是而非的威脅,早該屈服,畢竟不過一個庶女,父皇的公主尚且爲國遠嫁。
可於老頭子偏愛沈氏,更偏愛她所出的女兒。
於氏家大業大,族人自不能全都聚集京都,北漠和川渝皆有族衆。
於老大人當年爲國不懼死敵,被遲家暗中動了手腳,死守城池,城在人亡。是以陛下多年信任。
可是北漠那些人仗着於老大人功德,在北漠幹起了軍需勾當,在於老大人去後不久,於氏分族。這事可大可小,可一旦證據確鑿,於氏傷筋動骨。
如今,於氏倚仗的不過是陛下信任。
一旦,火燒遲氏長子的欺君之罪捅破,陛下的信任必將不復存在。這位老狐狸在於老大人去後,那可是爲了社稷朝堂,作了一副隱忍求和的大義模樣。
我說得似是而非,可他心裏清清楚楚,不過是探探我的底牌罷了。
孤再煮一壺茶便是,心急哪能抱得美人歸呢?
但我泡了一壺茶,於大人沒來。
第二壺茶,仍舊沒來。
到第三壺,李織溶送來了一封彩絹,絹裏細細包裹着她的生辰八字。
我看得心熱,一行短短的字,它那樣可愛漂亮,充滿着生機。她出生在豔陽高照的春日,明媚的陽光下,不帶有那些陰暗,那些冷冽,只有溫暖和美好。
「他有說什麼嗎?」
李織溶面上有些躊躇,我便知道話不好聽。
「直言。」
「他說,於家祖輩以義立在朝堂,祖父如是,父親如是,吾亦然。無論於昭樺還是於照椿,殿下得到了於家的女兒,卻不一定能得到於氏。若殿下不配,她們改嫁便是。」
我聽了這話,有些想笑。
虧他爲官多年,還是少年心性,皇家的女人,哪個能活着走出宮門?
又一想,於氏兩代家主,雖隱晦而不爲人知,但大抵都死於非命。我手有些僵,朝堂之上,親情珍貴,但若真的觸及根本,於家也不會手軟。
怕是我落敗之時,便是於家二姊妹香消玉殞之日。
我收起剛纔有些得意而挑起的嘴角,聲音冷冽,「走吧,孤還有話和於大人講呢。」
我換了一副禮賢下士的仁君面孔,後面跟着李織溶手裏握着於氏流失在北漠多年的玉劍。
「琮剛剛多有冒犯之處,只因晚輩年少冒失,又傾慕於家女兒,還請大人海涵!」
「殿下,微臣不敢。」
我雙手撐着他行禮的雙臂,這次溫柔且真誠。
「大人,琮自幼爲太子,卻無一日真爲儲君。其間艱難,不宜宣諸於口。」我這時候的眼睛當是泛着猩紅的,這些話,輕易能與誰言?
「殿下?」
「且聽晚輩說完。自安閒太子事後,主少國疑,陛下夙興夜寐,可遲家掌握朝綱,黨同伐異,以家國爲注,用國器以肥傢俬。倘他當真是當世之能臣,便也罷了,這李氏江山便是讓與遲又何如?可他偏偏以權謀私,用術至深而全無道法,江州水患,朝廷賑濟銀兩竟有五成去了遲系黨羽。於家世代忠良,獻身朝堂死國無數,又如何能聽之,任之,由之?」
我一番話下來,於老頭總算動了動眉頭。
「殿下方纔問臣,國恨家仇,孰重孰輕。臣之家仇,何能與國恨相提並論?當年遲家長子有必須軟禁的緣由。遲氏子嗣不豐,那時候他的權力已達巔峯,但膝下僅有二子,次子有疾。那年大旱,眼見各地動亂,若我不綁了他的兒子,改朝換代便在眼前。」
「可陛下讓你軟禁,你卻動了殺心!」
「殿下怎知……」
「怎知這件事本是陛下旨意嗎?」
我高深莫測地笑了笑,父皇是心軟,可再心軟,他也是能將這個舉步維艱的朝堂維持幾十年的明君。遲家得了我那皇祖父輔佐幼主的遺旨,在朝堂根基深厚,安閒太子的餘黨卻是被清理殆盡,父皇做了多年閒散度日的無權王爺,朝堂運轉不得不託付遲家,可他也明白,遲家野心昭彰。
但以父皇對遲貴妃多年如一日的寵愛,不可能取了遲家長子的性命,那麼餘下的自然是於大人自作主張。
挑着喫了一顆點心,飲了飲茶。
這於大人太不懂待客之道,即便我這個女婿他不太喜歡,也不至於餓我一整日吧。
腹中有食,心纔不慌嘛。
「殿下,陛下栽培之心從無動搖,當今朝堂,但凡是忠於陛下,定當忠於儲副!」
「大人所言甚是。」
接下來,便是我的主控場了。有些缺口一旦打開,接下來的便也順理成章。
半夜之時,我總算告別了於大人,朝堂那點事,於老狐狸鑽研一輩子了,門道摸得比自家院子都清。
我實是受益匪淺。
甩了甩一腦子陰謀算計,我抬腳翻牆入了她的院落。
院落並不大,但佈置十分可愛,不見名貴花木,可每一處草植都顯得渾然而靈動。
我輕手輕腳地蹲在窗外,這更深露重的,孤還在院子裏聽牆角,也是不容易啊!
是的,她還沒睡。
「唉!」
「小姐,你怎麼了,爲何嘆氣?」
「小司,父親今日不對勁。」她聲音慵懶還帶着鼻音,顯是困得久了。
「小姐,快睡吧,就算明日裝病也不能真傷了身子呀!」
「不行,憔悴這二字可是有門道的,眼裏的睏倦和病態,畫是畫不出的。若是騙騙母親倒還好,這次騙得是姨娘!」
「小姐,姨娘精着呢,您若想真騙過去,還得修煉十年八載的。」小司在旁邊毫不留情地道出真相,「爲什麼你不想嫁給譚探花呢,他才高貌美,無可挑剔啊。」
我腳有些麻,堂堂太子聽牆角,傳出去,哦,傳出去估計沒人信吧。
是啊,爲什麼不願呢?
屋裏默了默,良久她開口,「小司,你看舅父,他不也沒有婚娶嗎?」
「我是庶出女兒,自懂事起,便能感覺到這世上諸般不易。姨娘的身份讓我自幼被兄姐嘲諷,父親周旋在官場,和自己的妻子鬥法多年,姨娘斷情絕愛,其實揹負血海深仇。一個人活得太明白,就不再會相信和希冀。小司,你信嗎,我不論嫁與誰,都能過得舒心自在。可我想去看看山水看看人情世態,走遍這大好河山,寫一本遊志,若有可能獻給朝廷,也是功德。唯獨不想,活得似個物件。」
「小姐?」
「不是嗎,似個物件兒,將自己託給誰,哪怕那個人從不相識,生子管家,孝親敬長,克己復禮。若是成爲家族的棋子,便在各方之間作棋子,生死皆由他人。我若是家養的金絲雀也倒是罷了,可我不是,小司,我不是啊!」
她絮絮叨叨的,剛開始還是正經話,可後來就正經不下去了,話題迅速成了夜晚吹牛大會,再過一刻鐘,就要成爲蓋世英豪開疆拓土裂土封疆了,還好,她睡着了。
我爬上屋頂,帶了一壺酒,還沒來得及喝,就睡着了。
孤本以爲自己算無遺策,可第二日就遇到了於大小姐。
「殿下,臣女有禮。」
呃,這拜見的彆彆扭扭的,語氣冰寒,眼睛轉得滴溜溜的,父女三人的眼睛一樣的狡黠。
「於小姐何事?」
「我可以嫁給你,於氏一族嫡女做你的太子妃,助益良多。父親雖說不一定肯爲我用闔族之力,但若有選擇餘地,他會願意保全我。」
我詫異地看着她,於家的女兒都成了精不成,本該做夢的年紀,十幾歲的人偏偏活得比幾十歲的人還通透。
「所以,小姐有什麼指教?」
「我要你娶於照椿。」這倒是讓我有些驚訝。
「哦?爲何?」我有意試探,倒想看看她的反應,「她不過是庶女,比不得大小姐尊貴。」
「我姓於沒錯,但算半個符家的女兒,我那幺妹纔是真真正正的於家女兒,是父親放在心尖上的女兒,更是父親的態度。宵小之輩躲在暗處窺探,於氏的抉擇會被許多非遲氏黨羽的的大臣效仿,這毋庸置疑。」
我定神看了看她,「於小姐如何篤定我非你不可呢?」
「就憑殿下沒有一個穩固的母家,如果不順水推舟,怕是婚姻艱難。」
於家的飯果然不同,養出的女兒這般奇巧。
但她的城府且還沒到能脅迫一國太子。
「於小姐多思了,世族女子養德養性,莫要急纔是。」我的語氣陡然轉厲,「便是再落魄,孤也還是齊國儲副,再言,於氏家主嫡女不多,可族中也不乏貴重的女子。」
果然,我從她的臉上看到了裂紋,她慌了。
她,遠不如那隻精怪的功底。
那隻精怪已然爐火純青,便是三年前,在別院我也不乏試探,可她沒有絲毫破綻。深入虎穴龍潭還能收放自如的,我只見過一個。
「但,我們可以合作,不是嗎?」我探過了深淺就絕不戀戰,「只要,譚大人對小姐你,不全是攀附。」
她的臉色瞬時便百般變幻,我知道這位小姐,不是我的對手,但也不是庸碌之才,可以爲臣。
就像李織溶,她武藝超羣又理智刻板,但心直性快,可爲心腹;而於昭樺,稍有心機謀略,卻還不至有欺上瞞下的修爲,亦可用之。
「爲保萬無一失,這件事,還勞煩小姐說服令慈,想必小姐也不願於氏百年積澱卻要屈居在符氏淫威之下,不是嗎?」
事實證明,她的確得用,三日後我便得到密報,於夫人親手爲我的精怪打點好了嫁妝。
而我和於大小姐的合作也開始了。
胡伴伴
我是東宮人人敬着的胡伴伴,殿下身邊最受信賴的掌事大太監。
我是皇后指給殿下的人,他幼小時不知事,常常喚我阿爹。
我第一次聽到駭得一整夜都沒有睡。
但陛下仁厚,除了笑了笑說,「胡大監對琮兒甚好。」便再無其他責問。
我給陛下連連磕頭,「奴才萬死,求陛下責罰。」
陛下只是撫着殿下的頭髮,眼裏是複雜的情緒,「替朕照看好他,不必想得太多。」
我看向皇后,她只是衝我點頭,不言其他。
我這等皇家家奴,早沒了做男人的快活,更沒了做父親的可能,爹孃早早把我送了進來,讓我爲人僕婢,仰人鼻息,生死也不過是貴人的一念之差。也就靠着陛下仁心,皇后殿下賢德,宮中的奴僕不至於朝不保夕。也不知哪裏來的運氣活到如今,竟然讓太子喚我阿爹。
自那日後,我把他當成了自己的親子來呵護。哪怕,他後來愈發知事,再沒喊過阿爹,只叫我伴伴。
殿下從前一派的風流倜儻,哪怕身處詭譎的博弈之間,也只是被皇后教養得純粹狂傲:他的課業向來怠慢,偶爾寫幾樣文章策論來博得太傅連連稱許,偶爾看幾頁書本還要嘲諷一番儒生迂腐,此外便是和皇后殿下看着話本子,看着後宮百花爭豔。
後來,他北上從戎,我才知道,皇太子不是脂粉堆裏的如玉公子,而是心有溝壑的大丈夫。
是啊,皇后那樣的女子教養的孩子,怎會只是一個狂悖之徒。
殿下或許不知道,我最初並不是侍奉皇后的大監,而是陛下潛邸王府裏的舊人,而我的舊主,便是遲貴妃。
那時的遲大小姐,是陛下的王妃,我見證了二人情真意切的少年時光,他們那時候恩愛得像是一個人,連去恭房都要一前一後,做什麼都要相依相隨,王府裏的人對此津津樂道,陛下那時候只是逍遙王爺,許了遲家女兒一生一世,相守相依。
我直至今日也還記得初春的陽光很明媚,王妃脣角一顆紅痣在笑顏裏若影若現,紅潤的雙脣輕抿丈夫親自喂來的葡萄酒,春衫上的輕紗盪漾在清風中,兩人在滿是花香的院子裏相依相偎,屋檐上的燕子窩又一次搭建好了。
兩人仿若就要這樣過千年萬年,眼中只有彼此。
但一朝賜婚,王妃卻成了側妃,而太子妃之位卻給了滿門清正的林氏嫡女。
王妃白綾便搭上了房梁,就在陛下娶太子妃的那一日。那日的王妃塗着鮮紅的脣脂,慘白的面上掛着冷清的單行淚珠,被遲家家主救下時,她脖頸上的血瘀就像盤亙着的毒蛇一般,觸目驚心。
那一夜燭火暗淡,冷風刺骨,我忙碌一夜整頓宮闈,訓斥奴僕不許傳出一個字,否則即刻拔舌!
遲家家主涕泗橫流,質問斜躺在他懷中的王妃,「你是要我遲氏一族與你同死不成?」
太子大婚,原配自縊,對於那時候瘋狂獵殺的先帝而言,必會遷怒遲家。
自那之後,王妃變了一個人,她陰晴不定,愈發狠辣,做了貴妃不久就把我送給了當時根基尚淺的皇后做眼線,做隨時射向皇后的暗箭。
皇后的親子胎死腹中,是貴妃的計謀,她做的毫無忌憚,甚至毫無遮掩,我便是那層層相攜的連環毒計中的其中一環。我這一環,是要皇后的命!
是啊,失去孩子算什麼,她要殺掉這個讓她貶妻爲妾,給她百般羞辱的女人。即便毫無遮掩又如何,她知道陛下一定會護着她,會原諒她。
只不過我臨陣倒戈了。
我無法傷一個那樣的女子,她的美和善,能融數九寒冰。
皇后是那樣一個女子,明媚而自得其樂,柔婉卻不怯懦,對我們這些生如螻蟻的人也能真心呵護,哪怕是最低賤的灑掃庭除的宮人,也能收到皇后殿下的年節紅封。
她與貴妃的不同在於,貴妃需要愛來滋養,而她自己就能珍愛自己,也珍愛旁人。
即便我曾是貴妃的暗探,是她爲皇后埋下的毒瘤,最後我臨陣倒戈,她也願意護下我的性命。
後來啊,我陪太子北上疆場,在北漠那些根基深厚的世族之間周旋,他爲了得到情報不惜討好春樓老鴇。
我心疼得咬牙,淚珠子不爭氣得從老眼裏頭泵,卻不見他有絲毫不忿。
那是我從小一點一點呵護着長大的孩兒,我殫精竭慮地爲他擋去宮中暗箭冷槍,小心翼翼地爲他掃清前路地坎坷算計。可在宮中我尚且能左右逢源,在這荒涼冷清地北漠,我再擋不住那些層出不窮的刺客,那些世家大族的傾軋。
在北漠他殺了不少人,沾了不少血,早就在那風流浪子的皮囊下藏了厚重的陰暗和恐怖,在他安靜時,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身影,太靜了,靜得讓人生懼。
但見到那隻精怪時他好像又變成了那個溫潤如玉的少年,喊着旁邊的大小姐姐,眼裏盡是溫柔。
但娶她並不容易,那是官家小姐,出自京都於氏,不是他一個處處危機的儲副能輕易拿捏的。
世人眼裏於大人愛權愛勢,這是殿下最會拿捏的一部分人,我本來並不十分放在心頭,只要那女孩子能常伴左右,讓殿下有片刻安耽也好啊!
可我錯估了於大人的心,他騙了整個朝堂的人,人人盡知他是慕權愛榮的人,卻不知他也能硬氣得很。
我在宮裏並不十分扎眼,默默無聞纔是宮中保命之法,但我想爲我的殿下搏一搏。殿下登了於家門庭數次,無功而返,他眼裏落寞,讓我心裏針扎似的疼。
我便在於大人早朝回府必經之路上等待,守了三天才見着人。
「胡大人安好。」
他看見我也是禮數周到,言語客氣,絲毫沒有那一幫讀書人一口一個「閹奴」的蔑視,相反,平靜而尊重,既沒有趨炎附勢之意,也無輕視之感。
我不由也還了一禮,「於尚書,咱家這番冒昧見您,是有一言。」
於大人令後面的僕衆退了一射之地,「胡大人請講。」
我慣常是不會借勢凌人,面對這樣一個以禮相待的人,也裝不出官腔來,這時候才知道殿下那一手八面玲瓏黑臉紅臉白臉輪番上陣是多大的天賦。
「咱家伺候殿下多年,他對於令愛是真誠心意,緣何大人不肯嫁與?」
於大人看着我,眸子裏冷然,殺氣騰騰。我在北漠,最常見到的就是武將殺氣。
這番,我第一次見到了文官的殺氣。
「胡大人,實不是某怠慢儲君,只是我那小女兒自幼嬌慣,心思不定又多逆反,若入了宮必是後宮不平禍亂橫生。某忠君體國且不多談,單是怕她禍及家族便絕不敢送她入宮。」
我沒有接話,只是沉了沉嗓子,用宮中內官人特有的尖細嗓音道,「大人可知,自古紅顏多禍,令愛嫁與誰,都爭不過將來的陛下!屆時又怎知不會禍及家族?再言,令愛那般容貌,等閒誰人沒有貪慾,又有幾人能護得住她!」
這話說完,額角就有細汗,爲了殿下,做個壞人又如何?
於大人卻不多話,只是給我作了個揖,便轉身走了。
第二日,於家就籌備起了訂婚宴。
我甩了自己兩個巴掌,我對不起殿下。
殿下親自給我敷了藥,「伴伴綿柔了一輩子,笑臉迎人,此番倒是爲我做了回惡人。」
他說的時候眼裏還帶着笑,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志在必得。
幾番波折,側妃終究入了宮門。
那日,殿下就在側殿門外,看着那小丫頭一個人走完了所有流程,連合巹酒都像模像樣地自導自演。
殿下的手握得緊緊的,指甲嵌入手掌,血順着指縫流下。
那美得有些攝人心魂的小姑娘站在窗前低低地抽泣,輕輕地嘆,「山有木兮木有枝,我念君兮君不知。」她聲音很小,但殿下耳目聰穎,怎會聽不到?
「漂亮公子,我這一生想要的無非堂堂正正,自由自在,如今你爲君,我爲臣,你爲夫,我作妾,東昇朝陽西落去,你我至此陌路人。」
我本十分慶幸,她愛着殿下,但沒想到一個涉世不深的姑娘能做到滴水不漏,冷清寡情至此。
她表現得仿若從未見過殿下,疏離得令人心碎,眼裏對殿下的恐懼和防備更是層層疊疊。
殿下那段時日常常看着朝陽發呆,在臨到夜幕時舞劍,我端着茶水,看着他舞動的殘影后血紅的夕陽。
某次宮中宴飲,殿下喝的有點多,握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說,「我對不住她,她本該是無拘無束的精怪,可我自私地困她於方寸之地!」
早在殿下大婚之前,北疆就有異動,禍不單行,南邊的探子也送來了密報,南地多處兵庫異常。
那是殿下大婚幾個月前,李織溶自請查探,但殿下搖了搖頭,「若是你能兼具於照椿的腦子和李織溶的身手,孤便派你去。」
我的殿下啊,說話也太直了些。虧得李副將不在意,不然易失人心啊!
我進了一言,「殿下,老奴斗膽說一句,若是有道理您就聽聽,若是莽撞,您就當老奴多舌。」
殿下看向我,眼睛溫和安靜,「伴伴,您的話,我聽。」
「殿下,您的人手多數在北漠,如今京都有公主鎮着,此外別無可用。就連着這東宮一個開門的內官您也差使不動,此等狀況實在無人能派。老奴斗膽薦一人,沈知義。」
殿下默了默,「此人不好掌握,用得不好,反噬其身。」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道,「殿下,您若是想娶於家小姐,這位大人留在京都必是阻礙。」
殿下站起身來,看着遠處,「伴伴,此去多艱,在我露出鋒芒那一刻,遲相就早有防備,而且可以看出,他對臨江府十分放心,必是防備周全,萬無一失。」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