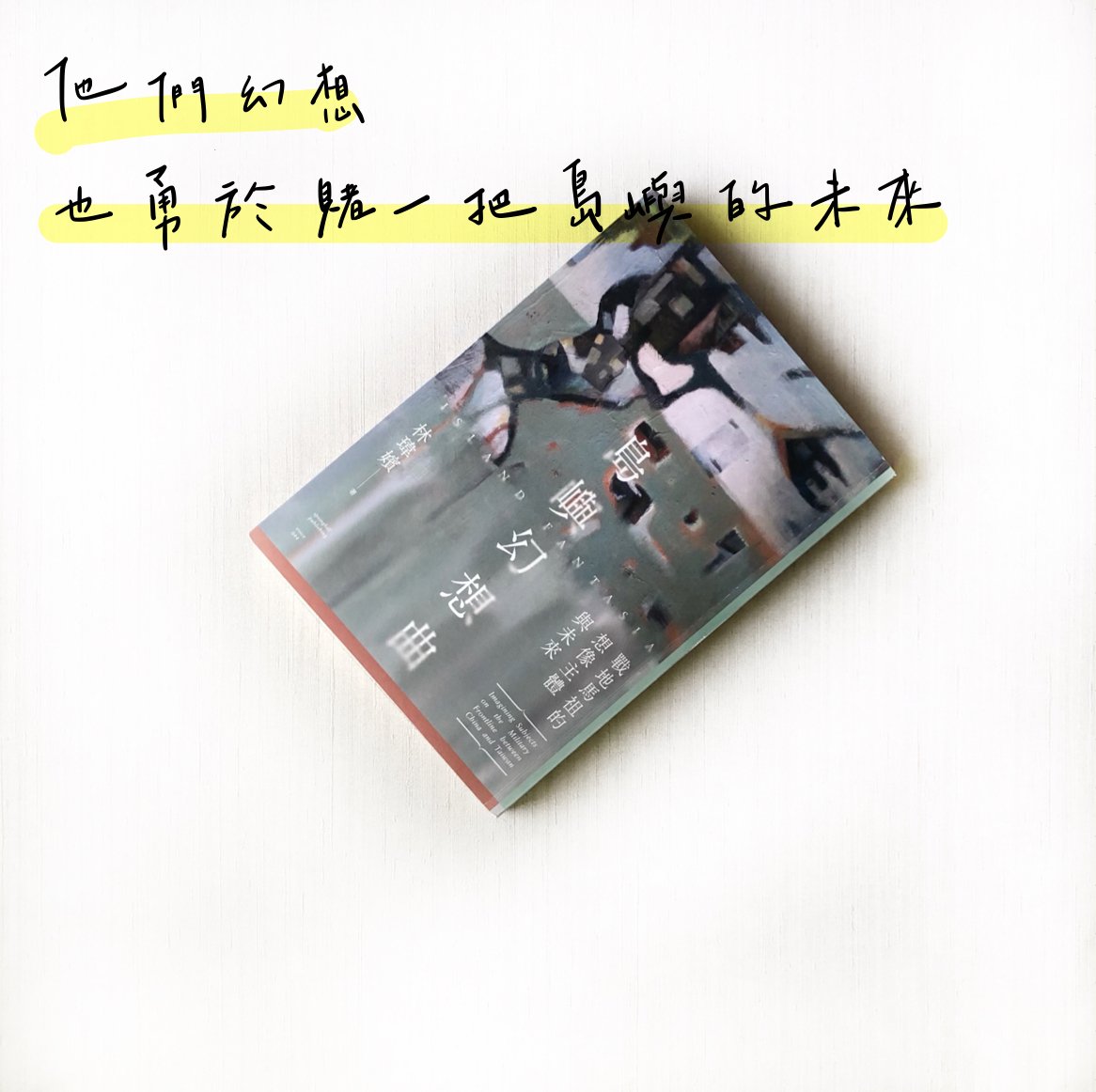馬祖的故事
強勁海風不停銷蝕容顏,不過上島幾個小時,她覺得自己被吹乾了好幾歲。眼前似曾相似,卻又有物換星移之感,多年經緯度不變,卻恍如隔世,認也認不出。她極力在枯石蒼海間搜索回憶,幸好地貌雖有些相異,曲折海岸倒與從前一樣。
不認得的建築一棟棟興起,那時候還未如斯繁華,說繁榮是和往日記憶相比,否則這片風土怎麼能跟她現居的城市比擬。那時候連機場都沒有,出去還得搭船,她吹海風長大,海浪風波就像搖床,風浪大一點也不影響安睡,但她不會忘記身旁的男人吐得面黃肌瘦,仍然撐著顏面談笑自若。
其實何必呢,誰是倚海而居一看自明,可她不忍心戳破他的尊嚴,總是要留些好看的,日子才能長長久久。爾後她也謹記這一點,不能講的當作不知道,這樣一來風平浪靜,倒也和樂融融好多年。他細心問起這裡一草一木,似要從她塵封的回憶庫挖掘寶藏,那些都是不值錢的古董,提也罷不提也罷的老化石。他們又不是來考古,只是恰好來看心肝兒子。
雖然小兒子抽到金馬獎,但時光變異,讓人淚斷腸的都演在戲裡,他們反說小兒子可以渡假一段時光。她在家裡算日子,算小兒子何時抵達部隊,電話一頭則說一切平安無事,島上風景優美,要兩老有空也來玩一趟。她在意小兒子有否暈船,小兒子繼承海的基因,一路順利抵達港口。
玩一趟啊。她若有所思,反覆吟唸,直到聽見話筒裡傳來吆喝,小兒子匆忙結束通話。他在一旁,溫柔抱住她,說去玩一趟也無妨。她搖搖頭,小兒子已非三歲小孩,何必讓父母跟著,孩子要放飛才會成長。但她不停想著小兒子口中美麗的風景,然後不曉被誰下了蠱,迷迷糊糊訂了兩張機票。
這當然是他的作為,當他亮出兩張機票得意邀功時,她疑惑地拿著機票查看,覺得好奇怪,那地方什麼時候有機場了。她沒說想不想去,他已默默請好假,排定行程,聯絡好小兒子。兩人玩一趟的事變成家族出遊,大兒子跟兩個女兒也來了,兩張機票變五張,她看著他跟兒子女兒忙裡忙外,自己則像失了魂。
她甚至忘了出發日期,平時早起的她居然賴床,還是他死命催,一家人才趕上飛機。這麼多年坐過無數次飛機,她卻害怕起來,前幾年飛往離島航班的墜落事件讓她耿耿於懷。他說生死有命,遇上了躲不掉。她還是被勸上飛機,心神不寧望著窗,看雲蒸霞蔚的大都會變成盆地,然後縮成小小一點,進入一望無際的藍天。從飛機上俯瞰的島很小,連個人都無立錐之地,她瞇了一會,等到他搖著她的身驅,已經平安落在機場。沒事了。兒女輕輕握著她的手說。
可是還有回程。她在心裡忖,但就只放在心裡,沒有對他們說。一家人租車,興奮地指點未曾見過的景色。小兒子明天才休假,不過北竿不大,黃昏前就能繞完一圈。下榻地在航空站附近,他們寄放好行李,到熱鬧的街市用午餐。她不禁嘆這裡變得如此喧囂,當然是與從前相比,那時還沒幾家店鋪。四人點了魚麵,一雙兒女大讚是沒吃過的好滋味,她卻喃喃說這家魚麵不好,嚼勁不夠。
聽見她的嘀咕,大兒子說她似乎對這東西很熟,他們餐桌上可從來沒出現過魚麵。她瞥著人來人往的店鋪,曾在朋友那裡品嚐當地人自己做的,夠味夠勁,吃過一次就忘不了。還有蘿蔔絲餅,她又囔囔冬日的蘿蔔最好了,沒有冷冷海風曬過就少了滋味。女兒笑她說話的方式簡直像是個老馬祖。
午餐完免不了四處兜晃,北竿不大,駕車一下子就繞完,小兒子明天才休假,於是他們便在附近走走,去塘後道看海,到大沃山也是看海。無論海灘山峰,最後都離不開海,她坐在草地上,望著延入海的陡峭岸壁,他悄悄到她身旁,指著海中某個方向,那裡是無名島,旁邊是峭頭。他們不像初來乍到的觀光客,對附近小島的位置如數家珍,熟得不像剛從地圖上背下來,而是真的親眼就過,曾經爬上去探險似的。
面對兒女的調笑,她說可能跟馬祖有緣,所以小兒子才能坐船不暈。或許夢裡來過,所以對這裡一草一木並不陌生,夢很模糊,記憶卻逐漸清晰。吹了一下午海風,氣溫遽降,彷彿要下雪。她拉緊厚重的羽絨大衣,望著冉冉昏黃的天空,這裡會下雪的,只是沒有國外那樣漫天狂雪,不過冬季的海風已經夠冷夠寒,再添雪可能凍得掉鼻子。
太誇張了。他說那年大寒,冷氣團拚了命像要結凍整座島,也不見她喊冷。說完他趕緊摀住嘴,一旁兒女識相的離去,吃晚飯時她要三人別假裝,一家人不該藏著秘密,再說她從來沒有藏住什麼,就只是不提而已。她是馬祖人,生於北竿,並非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但也沒什麼好隱瞞,翻開身分證英文開頭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事實上她的兒女前幾日才知道原來她來自馬祖,她不提也不藏,就這樣過了二十多年。這些日子改變的不少,在她眼裡就是物換星移,就拿那座航空站來說,她記憶裡的馬祖可沒有這個建築。但人變老,建築變舊,這山這海依然如那年。家人沉默望著她,反而讓她無措,不就是來玩一趟,別搞得觸景傷情。
孩子們從沒踏過她的娘家,永遠無法跟別人談論初二的話題。她不講,被問了也不答,只輕描淡寫帶過,反正人都出來了,還有什麼好說。她脾氣很倔,一旦決定封口能一直假裝沒這回事,他明白,也遵守兩人之間的默契。他非馬祖人,畢業後抽到金馬獎,還大哭了一個晚上,不曉得吐了幾次總算靠岸。
當兵的事不多提,他只說在這裡遇見了她。她起身回房,房間面向海岸,夜裡海岸起霧十里霧茫。不禁想這霧原來這麼濃,還是老花眼又加重了。鏡裡初生白髮,家裡的老人現在又該是何模樣?他輕輕推開房門進來,向她道歉,不消猜也知道是誰洩漏往事給兒女知道。她沒生氣,何必氣呢,倒是她嘆著分辨不出會不會下雨,倚海而生最擅長判斷天氣了,濕氣很重,幾乎再加一丁點水蒸氣就要淹沒南竿。離去這麼多年,對於海已經斷了某種聯繫,她也成了聽天由命的陌生異鄉客。
他坐在床沿,輕摟著她,一如二十多年前兩人在大霧的海堤上相擁。她年華老去,他也不年輕,那會當兵體格精實,理著平頭也散發青春朝氣,當初的大男孩戴上老花眼鏡,不起霧也看得糊里糊塗,年輪深深刻在臉上,像是乾瘠草原。她走時以為這座小島成為絕唱,卻堅持不往回看,爾後要看只能到夢裡尋。最近她常在電視上看見老兵落葉歸根的故事,八十九十歲的老芋頭漂洋過海一甲子,臨死仍懷念家鄉的土壤。她一個人看會忍不住鼻酸,指甲緊掐著肉,警告自己別像甩著水袖哭得淚漣漣的花旦。她不唱戲,只過人生,人生沒有戲本。
這些年她跟他換了好些住所,以前住得地方早忘記地址,唯獨家鄉的忘不掉。畢竟夜夢裡還會盤桓在花崗石造的樓房前,躊躇不敢敲門進去,當時父親已經撂下狠話,離了這裡永生不見。她的倔強肯定遺傳至父親,因此夢裡她也不見。
翌日他們去了軍營,見了小兒子,他那時也在這兒服役,回憶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去。她總會提些涼水熱食來賣,幾番往來跟他有了交集,外島日子漫漫,數不完的饅頭足夠讓兩人生情。一開始誰也不知道,但彈丸小島海風一吹很快誰都知道了,街上人瞥見幾次,就傳回她家。她父親不支持,畢竟役期一到人就回台灣,他說放就放,但女兒還在島上,小小地方傳得人盡皆知,敗壞顏面。
父親越不讓,她愛得越深,他破冬後她也懷了三個月的孕,這件事差點沒讓她父親上軍營理論。家裡無時無刻鬧騰,她只能在軍營外盤桓,期望他的海誓山盟成真。家人逼著打胎,她硬是要保孩子,面對街坊鄰居指指點點,她堅忍挺過那年代對未嫁女人的抨擊。
他領了退伍令準備回家,在海岸用一束花當作戒指套住她的一生。大海茫茫,誰知道他去後還來不來。幸好她的母親可憐孫子,撐到大兒子生下來,只是他回鄉後竟杳無音訊。父親揚言要把大兒子送人,街頭巷尾的流言蜚語讓父親老面子掛不住,索性也不接濟她,她也不放心上,一邊養背著大兒子,一邊撿粗活做。家人不諒解也好,他薄情寡義也好,村人罵她淫蕩也好,她始終吞忍一切,自己做得事自己承擔。
轉眼隆冬降臨,他在冷颼颼的冷雨裡返回港口,她才知道他在家鄉出車禍,因為地遠通訊不發達,因而音訊阻隔。這次他帶著許多禮品,要向她家提親,她父親拿著掃帚把他轟出去,她則堅決要跟著他。那次是她生平第一次被父親狠狠刮了一巴掌,要她踏出回就斷絕父女之情,她想也沒想,不哭不鬧,不管母親淚斷腸,提著小行李跟他坐船去了台灣。她背對北竿再不回頭。
直到小兒子喚了她幾次,她方從那些回憶回來。一路上兒女話少了,他也不怎麼說話,一家人靜靜馳著公路開往花崗石樓。她以為今生再也不會見到芹壁,那黯淡的石堆牆勾起她曩昔點點滴滴,想起有一年她跟他去了希臘,覺得那裡的海岸跟馬祖好像,但是人家白牆藍頂漂亮多了。車子緩緩經過她夢裡頻頻出現的屋子。
坐在車上她想起初隨他到台灣也經歷多重苦難,他的雙親不待見她,沒多少好臉色。說她未婚懷孕勾引他,絕不是好女人,要不是有大兒子在,恐怕更沒好臉色看。她又倔了,反正不怕吃苦,寧願帶著兒子出去討生活也不仰人鼻息。她不願自己命苦,既然做了就得承擔,怨天尤人哪稱得上刻苦耐勞的馬祖人。他決定同進退,兩人攜手北上,白天做工晚上做家庭代工,辛勤度日。直到大兒子四歲她跟公公婆婆的關係才好轉,那時又多了一個女兒,頭次祖孫三代吃年夜飯。
北上第十年,他因幫朋友作保欠債,好不容易經營的事業一夕潰敗,她依然不怨,將積來的首飾全部典當,笑著說一家人都平安就好,這個家又讓她撐下來。回過神,已經二十多歲的大兒子拍了拍她的肩,大家提著大袋小袋下車,一向堅決的她突然躊躇,那道崁跨不過去。幾個人站在外頭吹冷風,冷得直發抖,最後是被她的大哥發現。那一年她大哥身材魁梧脾氣暴躁,為了妹妹狠揍他一頓,如今大哥腆著啤酒肚,圓潤的臉看起來和善許多。
她還沒哭,大哥竟先搶著唱哭腔,親血骨肉不必話語點明,大哥連忙邀她一家人進屋,大聲喊著讓大夥全出來。裡頭老邁的聲音罵問什麼天大的事,一出來全凝成三尺凍寒,下一秒白髮蒼蒼的老母親老淚縱橫,九千個日子的思念一時半會哭不完。
母親看見她身後已經成年的孫兒,趕緊拉上前一個個認,除了抱過大孫,其他都是突然迸出來的。她的外甥也從小鬼頭長得又高又大,一把辛酸道不盡。母親以為今生無緣見到女兒,高興地以為是白日夢,緊緊牽著女兒的手到公媽桌點香,感謝列祖列宗保佑她平安。她看見母親三千青絲成灰,兩滴淚珠眼角打轉,始終下不來,不知這場面該哭該笑。
遠遠看見一道騎著機車的老邁身影,幾乎瞥上一眼就曉得是誰,她僵住微笑靜靜看身影騎進門前,颼颼海風頓時平地起風雷,哼著歌的老父親大變臉色,仙是驚愕,然後一句回來幹什麼,沉著臉往屋內走。要是換做以前的脾氣,她立刻甩門離去,可是這門一甩好多年,這把年紀也沒必要,再說她只是答應他來玩一趟。
母親要她別理老頭子,要大夥上市場買菜,辦遲到多年的歸寧宴。她心裡有疙瘩,其他人也是,臉上嘴上說說笑笑,時間劃開的鴻溝卻不易填滿,但家人終歸是家人,看見那些熟悉的老地方,當時情緒全湧上來,指著一堵牆一條路都聊出感情。夜裡她和母親協力煮了一大桌家鄉菜,母親還背著偷偷地哭,她忖菜肯定不用加鹽,那些淌出來的憋在心裡頭的已經足夠重鹹。
老父親窩在房裡不出,不見女婿不見孫兒,任誰喊都沒用,年過甲子性子越活越倔。芹壁點了燈,不像以前入夜後黑燈瞎火,還是有些事情不一樣了。晚飯母親跟大哥帶著她一家子逛著燈火通明的村子,綴上冬日輕霧頗有一番滋味。
母親悄悄說自從她走後,父親沒事就會到港口觀望,航空站蓋好後更是三番兩頭去,就是怕有一天她待不下去,跑回北竿會沒人接,她的房間除了定時打掃從沒動過擺設。
她當然知道父親還是疼她,正因為他們都有一副臭脾氣,明白父親擺不下臉。想到父親駝去的背,眼眶止不住濕潤,被海風逼出了幾顆,誰也沒多說話,只是靜靜走回屋裡喝熱茶。母親說隔不久就要過年,問初二來不來,到時候正經八百擺個大宴,她笑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又說過年要來接小兒子回去。家裡的擺設格局沒太大變動,她憑著記憶走到自己的房間,門開著,裡邊看見父親消瘦的背影,父親冷冷地說東西沒人碰過,她同樣冷淡哼了一聲當作回答。
暌違二十多年的交流如寒風刮過,已足夠讓她流滿一鍋熱淚,她沒哭,仍然驕傲的昂首轉身。彼此都知道過得好就好,多說無益。後兩日母親跟大哥也加入他們遊馬祖的陣容,返程的日子彈指而至,一伙人十八相送終須一別,她在機上緊盯北竿,那些被蓋住的思念一旦溢出止也止不住,倉促幾日遠遠不夠發洩,他安慰等到過年就來,馬祖也不遠,又非天涯海角,之後想念了坐個飛機就到了。
在機場時母親拿出一盞小燈給她,這是缺席的父親塞給母親轉交的。習俗有元宵時要為出嫁女兒送喜燈,她卻還了回去,要元宵時再讓父親親手交給她。一來一往,兩人無形盡棄前嫌,誰也沒真的把當年那番惡話往骨子裡聽,說到底還是血溶於水的親父女。哪怕真是天涯海角,也斬不斷這份親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