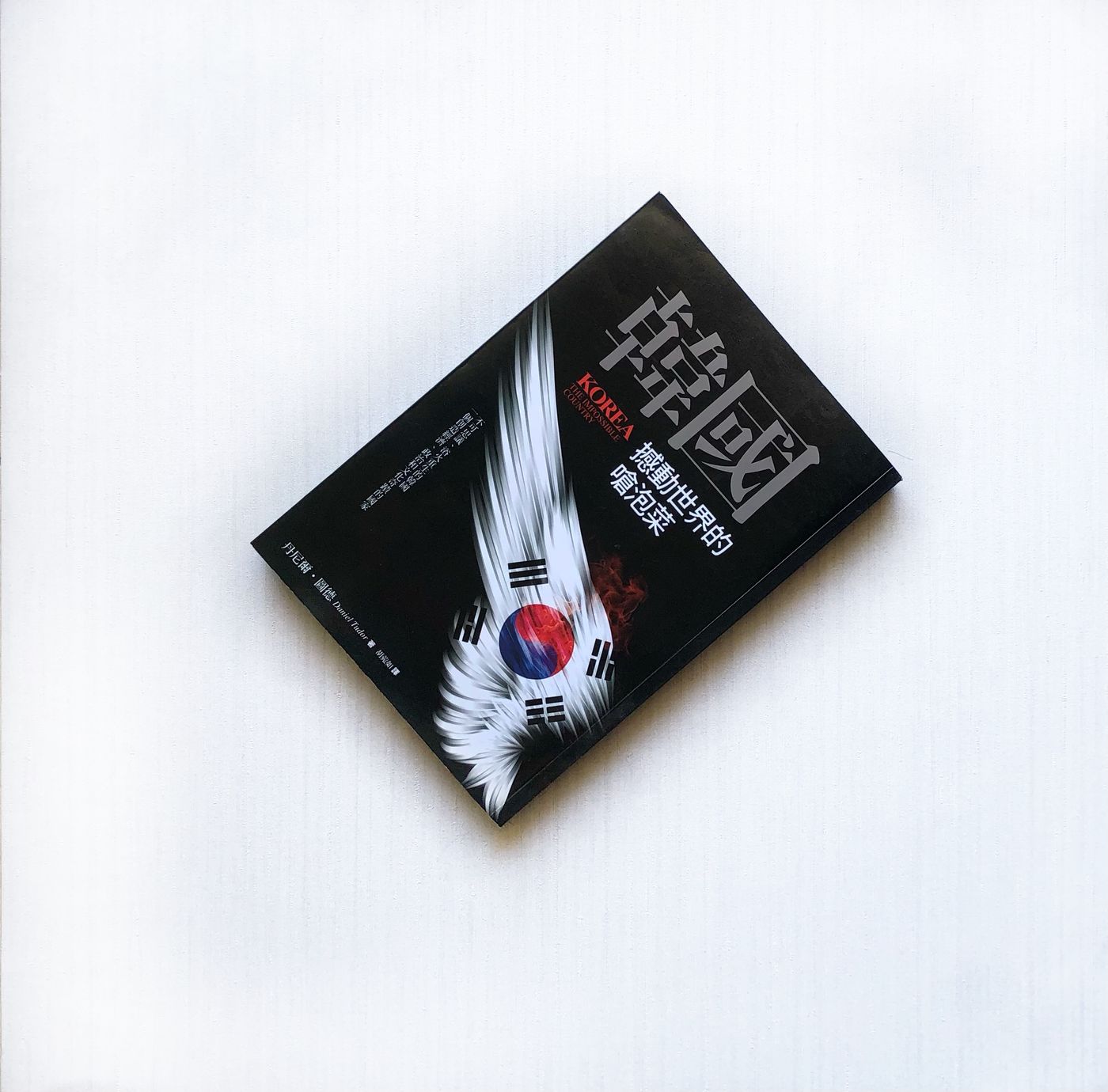「韓國華僑」可能是台灣人最陌生、也最不了解的「同胞」了。
現在韓國人口中的「華僑」,大部分是民國初年軍閥割據,以及國共內戰期間為躲避戰亂而逃往朝鮮半島的華人,遷移的背景和台灣的「外省人」類似,只是由於地利之便,多半是走半島陸橋、或乘船跨過黃海的東北/山東一帶居民,和世界各地華人移民多為擅長航海之閩、粵等南方族群的組成不太相同。
他們為了躲避戰亂來到朝鮮,卻沒想到國共內戰剛落幕,韓戰又興起,硬生生地用北緯38度線將朝鮮半島分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與大韓民國(南韓);爾後當兩方政府安頓好,想起這些流亡的華人時,便將38度以北的歸至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南的歸給中華民國。於是,在歷史的偶然之下,南韓便出現一群既沒有祖先來自台灣、也沒在台灣居住過、甚至連台灣本島的土地都沒踏上過,卻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遺失的國民們」。
不過,若說成「國民」也不太精確,因為沒有在台灣居住置產,也沒有親族的韓華們,拿的護照雖然與我們外觀相同,卻是無戶籍護照,俗稱「空殼護照」--意即他們法定意義上是中國民國籍,卻仍被視為外國人,需要每三個月出境一次,就算在沒有疫情阻礙國際交通的過往,也甚為麻煩不友善。
我們這邊政府的對待方式或許還算合乎邏輯,畢竟韓華說穿了和台灣沒有任何實際的淵源,他們的身分乃是一連串陰錯陽差與不得已造成的;然而,讓我匪夷所思的是韓國那邊的處置,即使我接觸韓國流行影視文化十幾年、學習韓文、真正認識韓國人甚至韓國華僑後,仍然難以理解--到底是什麼樣強烈的民族性與血統主義,能夠視已經落地生根三、四代的居民為外國人、次等公民,明裡暗裡施予差別待遇和歧視,並且整個社會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
因此,我個人面臨韓華議題時,很難不感到忿忿不平,除了親耳聽聞韓華朋友闡述當地的隔離生活和壓迫之外,也在於同樣做為「戰爭難民」後代,雖然很幸運沒經歷類似的排斥,但仍非常能夠想像與同理。

以至於當我聽聞《醬狗》這部由韓華導演與主演的電影問世時,立刻產生了頗高的期待,畢竟在Kpop、韓劇與韓影風靡全球的當今,我們對韓國本地文化與歷史了解的程度,可能都遠勝於對「韓華」這個與台灣若近若遠的群體;且在百花齊放、類型多樣的韓國影視作品中,幾乎不曾出現有深度、有份量、做為陪襯搞笑的中餐館員工之外的韓華形象,更別提以探討韓華身分認同為主軸的電影了。
《醬狗》以韓華第三代光龍的視角切入,用「青春成長陣痛」這種較好入口的劇種包裝,講的依舊是「醬狗們」(註:韓國人對華僑的貶稱,取自於中華料理的代表-炸醬麵)在社會大環境中遭遇的不公義,以及無處為家、難以定義自身的漂泊感。
韓國被喻為「世界上唯一華人移民難以發展的國家」,除了人們排他性高的民族思維之外,朴正熙專制時代明令的差別政策也是將歧視推波助瀾的原因--對置產、經商種種限制,稅收比別人高、待遇卻比別人差,甚至規定與華僑通婚之韓國人須放棄國籍,藉此阻斷韓華以「血脈」真正融入韓國社會的可能性--這使得現今在韓華人的數量,銳減成戰後的五分之一。
因此可以同理,要他們平靜、不帶批判地訴說自己在韓國的生長故事,是十分困難的,《醬狗》也不例外,雖然有著青春鮮豔的主視覺設計,電影畫面色調也大多使用高明度,但它幾乎是以不加修飾的憤怒口吻,指控光龍在學校遭受的霸凌、路邊警察對疑似「非法居留者」輕易行使的暴力,以及行政體制對「無戶籍之他國人士」的不通融,並且更回過頭來讓光龍把對外界的埋怨向內投射至對自我存在的遲疑--若不是生在這難以憑藉努力翻身、永遠弱勢又疏離的複雜歷史脈絡下的家庭,該肆意揮灑青春的年紀又何來如此沉重且龐然的煩惱?
所以當父親老是用中文對他說:「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時,他壓根兒不知道該認同的到底是哪條根?畢竟在體驗到文化所帶來的薰陶與涵養之前,他已被生活中因做為「異文化」代表而遭受之攻訐,傷得鼻青臉腫、渾身瘀痕。

關於光龍,電影的設定頗為微妙--他的父親是韓華二代,母親則是韓國人,因此不像「純種」韓華們被逼得毫無退路,光龍是擁有歸化為韓國籍這道選擇的。劇情中他已經進展到印出歸化申請書、只待父母同意的階段了,然而在一陣親情攻防之後,導演仍未給出明確答案。既然對「華人的根」沒有情感基礎,為何不果斷地變成韓國人呢?
電影安排母親以「成為韓國人,就要接受連他們都抱怨連連的大學聯考和服兵役」來勸退光龍,未仔細思考其話術背後意義的觀眾,可能會覺得這理由很瞎,而我認為讓光龍猶豫的原因有二:
- 光龍韓華與韓國混血的身分,使得他在韓華社群中又被切割出來,「擁有選擇權」看似優勢,卻會成為在爭取權益時難以站住腳的把柄。片中有一幕是他經過一群正在舉旗抗議的韓華們,只看了一眼、便戴上耳機快步離開,這並不意味著他對韓華的福利保障漠不關心,而是他不夠「純」、不夠資格代表「最被壓迫的個體」挺身而出。
(這也讓我想到《靜寂的鼓手》中,融入聾人社群的唯一方法便是讓自己「真的聽不見」,因此當聽力漸失的聽人男主角不放棄聲音、裝上人工耳蝸時,便注定從群體中被驅離。) - 當你長久遭受強勢群體欺凌時,要委身並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是有心理上的障礙的。這便是為何主流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或移民需要聚集、凝結群體力量,理性地想,多多接觸不同族群,應較能達到交流與和平共存的目標,但問題就在於成見實在太難放下,在追求安全生活的前提下,同類聚攏是更迫切的需求,當族群愈加壁壘分明,彼此隔閡對立的惡性循環便愈加深厚。
對此,光龍父親的作法是將他拋出舒適圈,由華僑學校轉至一般高中,提前讓他適應「真正的」韓國社會對待華僑的方式;而孤立無援的光龍,只好顧好成績、擔任老師親信,以抓耙子的方式暗中以暴制暴,回擊霸凌者,卻也反向加成了霸凌者對他的憎恨與惡言相向。

做為新導演張智瑋的首部長片,能感受到其急欲在韓國電影/台灣電影(本片獲選文化部106年度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獲選)中,補齊韓華身分認同論述的拼圖,造成一些情節安排和角色設定上會稍微顯得議題先行,但也因為韓華在歷史處境下的定位實在太過複雜,100分鐘的片長無法讓各個戲劇事件都獲得完美收束,不過仍能看到導演揉合深刻的親身經歷,誠懇地交出了一部情感豐沛的作品。
期待《醬狗》能勾起觀者關注、接近韓華的好奇心(無論原本了解與否),並反饋到票房上,讓張智瑋或其他韓華導演有餘裕創作相關議題的作品,好呈現更多關於韓華的不同面向--可能不僅有青少年、不只有壓迫和痛苦,因為這群人的存在是真的很獨特、很有故事性,也值得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