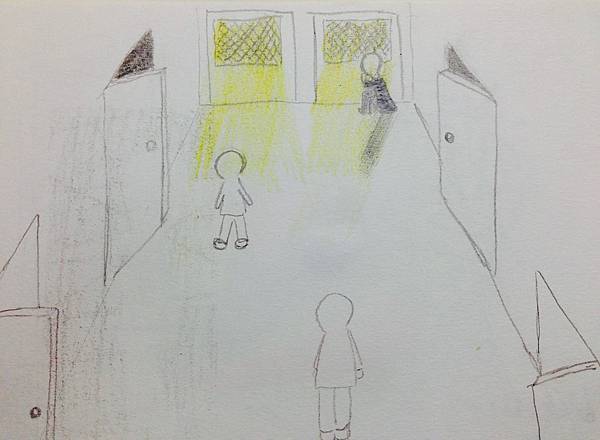講者:徐志雲 醫師
記錄:專線志工 山椒魚
大家好,我是一位精神科醫師,今天會從我自己的從業經驗來談談在醫療中看到的視野。當然有些專業者已經寫成書,但有些細微的內容在成書之後容易不見。
我先介紹我的背景,住院醫師階段一開始是在桃園療養院,整棟都是精神科,全部加起來大約有一千床,是西半部最大的精神科。後來轉到了台大醫院,這是綜合醫院,狀況又不太一樣。我除了一般精神科之外,也有受兒童青少年次專科的訓練。因為我是金門公費生,現在工作的地方在金門醫院,已經在這裡大約一年多。但因為我自己對「性別」格外有興趣,所以在台大醫院時有開了一個同志諮詢門診,直到現在也繼續在台北兼診。
我先讀我之前在小燈泡事件時投書到風傳媒的文章〈這就我們家的病人啊〉,這會連結到我今天為什麼會這樣談。今天活泉給我的講綱包括四個主題,我要強調的是其中有很多異質性,這些話在精神科醫師、病友、和家屬聽起來都不一樣:
(一)為什麼進入精神醫療
精神科是醫師當中的一個科別,社會最常把我們誤植為「心理醫師」,但台灣是沒有這個職業的;台灣是分成醫師跟心理師,後者還有分諮商和臨床,他們至少碩士畢業才能考照。精神科醫師是從醫療體系養成,在醫學院的七年期間,每一科都要學習,考取醫師執照再進行專科訓練。事實上,大部分人在考上醫學系時,都不知道醫療生態和各科在做什麼;最終影響選哪一科的因素也未必是專業知識和收入,而是生活型態。比如有些人選外科是希望有立竿見影的成就感,他們就很受不了走精神科或復健科,覺得同一個病人看了好幾年都沒有變化,就是「沒有進展」;有些人就能接受陪伴病人很多年。
剛入學的前面幾年都在修基礎學科,不會對特定科別有感覺,直到大四左右才有臨床課程,大五才進入醫院見習(每家醫學院略有差異),這時看到學長姊的經驗才會有一點感覺。我自己大五時在學校修精神醫學,開始覺得感興趣、能比較深入理解,還會自己在課外時間找資料。大學七年級是實習,當時覺得醫院工作真是太可怕了,導致畢業後的第一個想法是不要再當醫師;但因為我是公費生,所以當完兵後還是乖乖回到醫院,並且選擇了比較有興趣的精神科。
大部分醫學生對精神科是愛恨分明,通常是對「心理」抱著興趣才進來,所以其實一開始都會想像自己成為常做心理治療的醫師。但當住院醫師的第一年才發現:「媽呀,怎麼長這樣!」因為第一年都是在急性病房待著,而多數醫院都不會把精神病(和現實已經脫離)與精神官能症(有情緒困擾但溝通沒問題)的病人分開,所以我們常常要面對幻覺和妄想時的激動狀況,要學習的是如何安撫病人、約束病人。這是大部分人都經歷過的,理想與現實差距的衝擊;我猜想每個人在經歷這整個過程後,都產生了很多人格上的質變,所以有些人第一年就不幹了。但多數人還是會撐下來,因為仍舊有些喜歡的東西可以作為支撐;雖然心理治療的「豪華版本」在住院醫師期間並不存在,但我們也會盡力在繁忙的過程中,跟病人和家屬談相處與照顧中的衝擊,做比較簡短的心理治療,而這些都只能做中學。
另外,隨著時間過去,處理急性狀況的比例會越來越低,其他訓練則會增加,包括兒童青少年、司法精神醫學、老人、成癮、社區復健等等,每種次專科都要訓練三個月。漸漸熟悉後,才會開始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我自己是性別。我後來發現這樣安排是有道理的,因為急性病房其實最簡單,有一整個團隊可以作為支援;但其他都是醫師要單打獨鬥的,包括門診。
在精神科時時刻刻都被迫進行自我反思,但我反思的比較不是為什麼走精神科、而是現實的限制,我們常得與現實拔河,如果太耽溺於理想中反而會幫不了人,所以很多時候沒有辦法改變現狀,但可以改變個案的心境,讓他有希望。如果我們自己都不相信,要如何說服來看診的人,即使在客觀環境的限制下,還是可以有一個比較自在的生活方式?「人到底有沒有權力自殺」,我覺得這是一個最終極的問題。在形而上我覺得是的,也不得不承認有些人是我們無論如何都救不回來。但我也得為自己設定某個界線,因為我既然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就要盡可能發揮自己。
(二)醫院中其他科如何看待精神科
這個問題很少被討論,但我們很有感觸。其他科常把精神科當成隔離狀態,第一種是知識上的隔閡,大部分醫師覺得自己不了解也不想懂,所以我們要讓他們知道在內外科會遇到的精神現象,如譫妄,這時重要的不是把他們當成精神科病人,而是在內外科就能處理。
第二種是情緒上的覺得病人難搞,我覺得這也是反映社會現象,例如幻覺和妄想時對他講什麼沒用,或者常常割腕,就像個情緒的黑洞,這時就會失去耐性。精神科會訓練我們怎麼處理自己的情緒,但其他醫療人員沒有這樣的訓練可以調適心態,認知到每個人都是可憐、可愛、又可惡的綜合體,所以和其他科醫師溝通過程是很重要的。同時也要同理他們,有時候他們只想知道要開什麼藥,才能馬上解決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只當個好人,整天只有高尚理想也不是好事。
(三)精神科從業人員彼此如何看待
精神科從業人員包括護理師,有些醫院是各科輪調,有些是資深的專科護理師。日前瘋靡貼一篇病友分享自己經驗的文章裡有寫到,護理師是病房團隊裡最有機會接觸病友、和家屬會談的,但要看各家醫院的護病比,是否能讓護理師在處理其他雜事之外,有時間做心理治療,這是我覺得比較理想的狀況。
另一種職類是社工師,就我自己的觀察,其能力和熱忱和他有沒有執照未必成正比。社工是非常重要的,但醫師也不能把所有社會因素都推給社工處理,比較理想的情況是醫師也要具備社會工作的知識和能力。
一般而言,醫院裡的心理師大多是臨床心理師、少數是諮商心理師。心理師跟很多醫師一樣最初是有各種興趣的,但最終在很多醫院中,他們花最多時間在心理衡鑑(如墨漬測驗、智力測驗等等)和寫報告。因為衡鑑比較容易被客觀化與量化,其健保給付也比心理治療高很多,如果他們花時間多做心理治療,可能就會被醫院關切。但用慈善機構的標準來看待醫院也不盡公平,畢竟很多事情要被體制化才能有永續的發展。目前健保的心理治療只能給付八次,超過這個次數就要轉成自費,或者等半年後再重新開案,所以醫院的心理治療都要排很久,但要一下子讓社會認識到心理治療的重要性並不容易。
職能治療師讓我們比較不會覺得心虛,因為在醫院裡很多慢性病友需要復健,而負責這項業務的主要是職治師。急性病房有侷限是,由於大部分病友是比較低功能,因此通常只能帶基本功能的活動,但這無法符合高功能個案的需求。如果職能治療能做到讓功能分流,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有些醫院還會有其他職類,如社區關懷訪視員,這就需要額外寫方案去申請;社區醫療是很重要的,但「去機構化」在台灣做的還不夠好。
很現實地說,整個精神科團隊還是以醫師為首,所以如何下決定取決於他自己的民主素養,能不能聽取其他人的意見。其他專業人員之間則是還滿彼此尊重,他們都知道各自的辛苦,比較沒有階級差異(但也許只是我自己剛好幸運遇到平等的團隊)。我回到金門,在那裡醫師的社會階級依然非常高,這也反映在醫院當中的階級氛圍。
(四)精神科人員如何看待病人與家屬
聽眾提問一:聽到很多門診病人反映,由於人滿為患,導致醫生只能開藥而很難多談一些,你如何面對這樣的困境?
我自己的經驗沒辦法反映所有人的,我還算幸運。第一是因為我回到金門,人口相對少,每一節門診大概二十多人,雖然還是不少但相對其他人已經很幸運了。我的老師他們是看上百人,一次看十二小時。另外,每個醫師選擇的方式也不同,比如我遇到要花很多時間的個案,就會跟他約其他時間治療,雖然獲得的健保給付是一樣的。
還有要看醫院能不能支持,像我在台大只看同志,這個同志諮詢門診盡量以心理治療和家庭諮商為主,畢竟同志不是疾病。我的同志門診一個診有十幾人,但要花上一整天,這種診很不賺錢,所以就需要醫院支持,反正我就跟醫院說,不用給我額外的人力,盡量減低成本。很現實的是,有些醫院可以承受而有些不能,比如台大醫院是醫學中心,大家會期待他們有所創新,而不只是營利;且醫學中心被健保核刪的比例最低,診所反而最高,這會讓被核刪愈多的層級愈不敢做賠錢事業。
至於其他醫師怎麼做?有些人會因此妥協於業績;但我也知道有些醫師會分流,把多一點時間留給需要談比較久的個案;或者乾脆一走了之,自己出來開診所只做心理治療。
聽眾提問二:有照顧者打來專線問,自己和家人有需求,但看診時卻不知道如何表達?所以想問,如何讓醫師覺得要花比較久時間在這個人身上?
我覺得這就是臨床上的直覺,不應該要求個案會表達,而是醫師要訓練自己的敏感度,即使面對沉默的病友,也必須幫他找出方法,比如讓他跟家人分開、單獨看診,或者在幾次門診彼此熟悉後慢慢談。又比如兒童青少年,家長狀況愈多就需要看愈久;反過來說,憂鬱症到極度嚴重反而較輕型的難以談久。
但回到專線,接線時可以問問個案的語言功能如何。第一種是語言功能不好的,就建議家屬在診間幫忙說明。第二種是語言功能還可以,但受限於情緒上的困難,如社交畏懼和過度焦慮,這時可以鼓勵他們用其他方式表達,如先寫成文字,或者畫圖。第三種是已經努力試著表達,但醫師無法理解,也許就代表雙方不是那麼投緣,這時也可以考慮找其他醫師尋求第二意見。